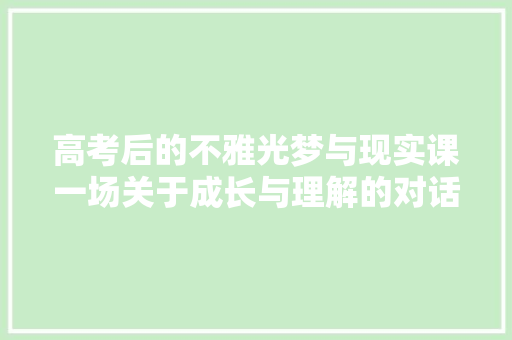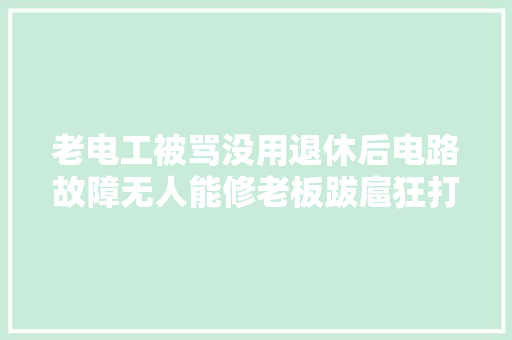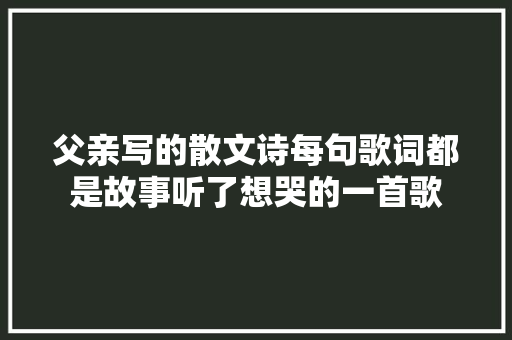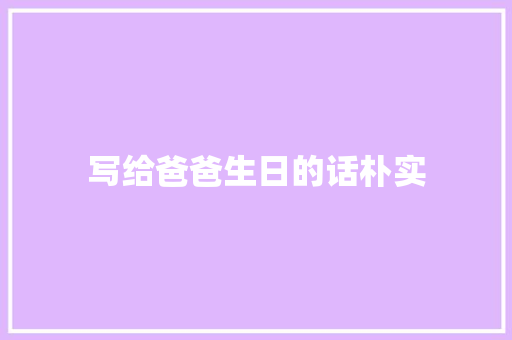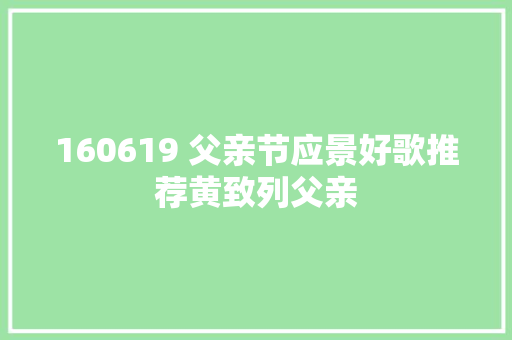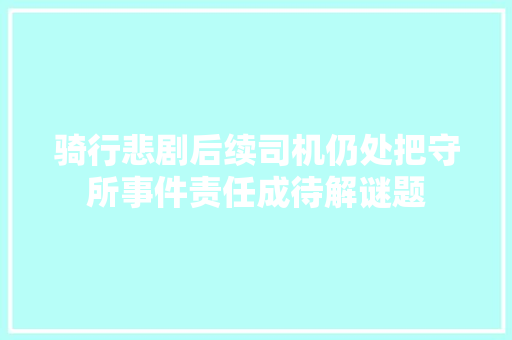◎王韵
我至今也没买车,唯一的代步工具始终是一辆半旧的单车。大概是性情、大概是身体的缘故原由,从个人便是一个特殊内向、不善言辞的孩子,喜好一个人默默地、悄无声息地生活。喜好安静的我,对付内心的感想熏染,相对付措辞,原来就更侧重于笔墨的表达。纵然是本日,有了手机和电脑这些便捷的通讯办法,不但没有增加我与外界的打仗,反而让我为这种习气找到了最好的情由。日常能打电话就不见面,能发微信就不通话,有事能简短留言就不谈天。乃至连手机和微信铃声都一贯设在静音,总是怕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会冲破多年习气的安谧无声,这已经成了我生活的办法。习气独自沉浸在笔墨中,过大略干净的生活,悄悄享受无声的天下。除了必需的会媾和活动,我基本不参加饭局和社交场合。绝大多数韶光都喜好呆在家里,安静地读书,沉默地写作,算是一个范例的宅女,偶尔去趟邮局。因此我的活动半径基本在家和邮局之间。我所在的城市不大,有事了推出单车,或者步辇儿出门,十分方便快捷。

从开始学单车至今,我骑过或骑坏的单车有五六辆之多,但影象最深,也最有感情的却是父亲的这辆。
父亲一辈子只骑了一辆自行车。而今,父亲腿脚不便,走路都已经拄动手杖,步履蹒跚,那辆单车而今也已经如他的主人一样,朽迈沧桑,锈迹斑斑,悄悄地呆在地下室里,默默地望着窗外的道路寂然不语。父亲的单车是一辆凤凰牌的大梁车,瞧上去坚固结实,不但后座能够载人,前面的那根长长的梁也可以坐人。在过去许多如黑白相片似的日子里,父亲骑着这车子,前梁小椅子上坐着我,后车座上坐着母亲,一起欢笑着小心地驰过,前后锃亮的车圈滚滚反射着阳光一贯向前。
父亲的单车是我刚刚记事时买的。记得当初它是杂乱无章地来到我们家的,它被拆散了,表面分头包裹了麻袋片,用绳子牢牢地扎上,不见天日。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弄得如此神秘。直到有一天,父亲请了邻居一位工厂师傅到家,用剪刀拆开包装。我才知道原来是一件件坚硬冰冷的零件。师傅操着扳手,开始组装那些零件。从车头开始,逐渐有了雏形。末了,一辆崭新大方的单车特立在了我们逼仄的家中。大概由于这是我们家当时最值钱的家什,父亲一贯守在师傅身边,他请师傅在每一个须要的地方都垫上了防止摩擦的胶皮。我和哥哥姐姐也在阁下不错眼珠地盯着,此刻好一阵雀跃欢呼,我们家终于也有单车了!
父亲特殊保重他的这辆单车,闲时常常会到路边的修理自行车师傅那里,要一点润滑油,在自行车链条上精心地涂抹一遍,车把手上的铃铛更是擦得铮亮。每当父亲骑着自行车,走到狭窄逼仄的小胡同,父亲就会按响铃铛。我最早坐在父亲的单车前梁,后来父亲在自行车后座安装了专门的小椅子后,那就成了我的专座。每次出门,父亲都骑车载着我,自行车铃铛的清脆铃声伴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
童年的我是多么幸福啊!
偶有一点点不舒畅,父母亲就会紧张起来,赶紧送我去医院检讨,而一贯对医院怀有深深恐怖的我,常常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后座上,一听说要去医院,就溘然觉得肚子不疼了。我央求着父亲:“爸爸,我肚子不疼了,咱们回家吧,不去医院了。”父亲转过分看着我,微微笑着,一脸宠溺地问:“怎么还没检讨就好了,真的不疼了吗?”我冒死点头:“爸爸我真的不疼了,咱们快回家吧,你和妈妈还没用饭呢。”父亲调转车头向家的方向骑去,母亲骑着新买的“蝴蝶”牌绿色小坤车紧跟在后面,她像识破了我的苦处一样打趣道:“韵儿怎么还没到医院就不疼了,是听说要去医院,吓得肚肚不疼了吧?”我坐在父亲自行车后座上,牢牢地搂着父亲的腰。后座上是母亲特意为我做的棉垫子,软软的、暖暖的,特殊舒畅。我转头对着紧随而来的母亲扮了一个鬼脸,说:“妈妈我真的不疼了,一说要到医院,肚肚就不疼了。”就这样,一家三口伴着谈笑,一下子又返回家了。而今,这些曾经温暖的回顾,成为我本日倔强面对所有噩运的源泉与力量。我始终相信,心中有爱的人,就会希望长存。
因着父母事情的缘故原由,我们常常搬家。步我们后尘,这辆单车也被捆绑了手脚钉进木箱子,一次次坐上大卡车,一起颠簸地追随我们,来与我们团圆。父亲一有空儿,就骑着它载着我上街,吃早点、看电影、上学、放学。父亲端坐在前,稳稳地双手攥把,像极了在惊涛骇浪中掌舵的大副,他偶尔捏一下车闸,或摁一下铃铛,清脆短匆匆的铃声在我听来是世上最悦耳的音乐。儿时父亲的肩头是我们温暖的依赖,如今这肩头延伸到了单车上。车轮滚滚,一起撒下的都是欢快与喜悦。父亲并不宽阔的脊背像一堵挺立的墙,为我们遮挡风霜雨雪,护佑我们快乐发展。
父母事情的地方间隔奶奶家90里地,那时还没有摩托车,更没有私家车。每个周末,父亲都要带着我回老家看爷爷奶奶。自行车前面叮叮当当挂满了给爷爷奶奶的东西,我坐在后面的车座上。我两手捉住父亲特意为我安装的小椅子的扶手,一起唱着歌,间或给父亲讲刚看的小人书里的故事。90华里,要骑上大半个上午。父女一起走着,说着,我像一个清脆的小铃铛,带给父亲一起欢声笑语。那时候,路上极少有汽车,更很少见到小汽车。偶尔父亲也会搭乘大卡车带我一起回老家。记得一个暖春的周日,父亲骑着自行车,后车座上照例载着年幼的我,一起谈笑着往奶奶家赶。忽然,一辆吉普车从后面飞驰而过。我指着奔跑的吉普车,仰起小脸,撒娇地对父亲说:“爸爸,我想坐小汽车。”父亲听了,居然停下车子,在路边东张西望起来。那时候,全体县级市也很难见到小型汽车,吉普车也是百里挑一。父亲站在路旁,边用手扶着车把,边看着路上偶尔驶过的车辆。这时,一辆半新的吉普车从后面驶来,逐步在我们面前停下。车上一位伯伯探出头跟父亲打呼唤,一向不肯求人的父亲见到熟人,竟破天荒推着自行车走到车子前,打听车子的去向。可能是巧合吧,吉普车正去往奶奶家方向。父亲解释意思,车上的伯伯下了车,把我抱了起来,激情亲切地呼唤我跟他们一起上车。就这样,那位慈爱的伯伯一起与我说着话,把我送回了奶奶家。父亲则一贯骑着自行车,牢牢跟在后面。到了奶奶家村落外的道班房,伯伯按照跟爸爸约好的,把我放在道班房里,叮嘱室内值班的叔叔照看,等着爸爸骑自行车赶来。不知过了多久,飞蹬自行车一头大汗的父亲凌驾来了,我一下钻到了父亲怀里,再也不肯离开父亲坐小车了。唯有父亲的大梁自行车,才能带给幼年的我温暖和安全感。
我就读的初中离家很近,走几分钟就到了,父母没让我学骑单车。初中毕业的暑假,想到立时要到30里外去读高中,父亲开始教我学自行车了。在村落庄小路上,我紧张地骑在车上,父亲抓着后座,车子歪七扭八,栽晃欲倒,就像我蹒跚学步时。父亲在后面仔细地扶着,身体随着我旁边摆动,很快便满头大汗了。过了不知多久,他便撒手让我自己骑了,等我扭头恍然发觉时,已经骑出了十几步远。在学了两天,摔了几次跤后,我终于学会了骑车。
眨眼间,我已成了一名高中住校女生。高中三年,父亲每学期开学和放假,都要骑着这辆单车去送我,为我送行李,送学习用品。每周都要两次骑他的凤凰单车跑30里地去学校看我,给我送刚刚出锅的饺子、包子,用饭盒装着还有一点温度的米饭和菜。无论刮风下雨,酷暑寒冷,每周二和周五上午的课间操韶光,都会定时涌现父亲高大的身影。那时候,由于我的身体一贯不是很好,也没有现在医院煎制好的中药,爸爸每个周末都要带我去看中医,回家用药罐子煎制出一个周的中药,然后将汤药耐心地分成七份,分别装在七个玻璃瓶中,在玻璃瓶身上标注上第一天、第二天……第七天,叮嘱我每天早晚按照瓶子的标注各倒出一半,用开水烫热冲服。高中三年,父亲为我煎制了三年中药。每周两次骑车子去看我,父亲都没有太多的言语。那种沉默的爱,却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心里。那一年的那一天,校园的天空高而深远,它的绿树就那么站着,眺望着迢遥的白云。教室门前,我安静地站在那里,看绿树,又看云的游移。在我把脖子看得酸痛的时候,同班的女生在喊,她的声音真清脆,就像小鸟在浓荫里叽叽喳喳:阿韵,你爸爸在校门口!
许多年后,每当回顾这声音,不知怎的,耳边总响起那个校园的鸟鸣。
初中毕业那年的暑假,我溘然萌生了给杂志投稿的动机。于是,人生中的第一篇稿件,载着我的梦想和希望,随着八分钱的邮票一起寄走了。高中开学两个月,翘首企盼的我逐渐淡忘,以为早已杳无音信。然而就在那个飘着秋雨的下午,刚下课,身着单衣的我正准备跑回宿舍添衣,一举头却看到一个穿着雨衣推着单车的熟习身影向这边走来,雨下得这么大,而且父亲刚来了不到两天,难道又来了?正犹豫间,父亲已经急匆匆又愉快地喊起我的名字来。然后躲在一间教室房檐下,激动地打开用塑料袋仔细包裹的手提包,从里面拿出一本刊物。原来是我的文章揭橥并且获奖了,父亲居然冒雨送来。那一刻我有点恍惚,有点激动,乃至有点小小的埋怨和心疼:一向沉稳镇静的父亲,本日怎么像一个孩子,下着雨,骑单车跑这么远,便是为了来送样刊。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和手机,通讯也非常未便利。由于一篇文章的揭橥和获奖,我收成了来自四面八方同龄人的来信和明信片,那一页页存心做成一枚枚八分钱邮票的信笺,像雪花一样纷纭飘到我的桌前。起初我还逐一回答,来的信太多了,逐渐地,紧张的学习生活已经让我无暇复信,又怕辜负了那么多同龄文友那一双双诚挚期待的眼睛,那些等待心灵呼唤的覆信。于是,父母代我做起了信使。母亲卖力替我收信、登记、填写信封,我写好复书,再由父亲骑着他的那辆单车一次次来回邮局为我邮寄复书。
快乐的光阴总是走得太匆忙。我的学生生活就这样很快度过去了。它载着父母的期望和顾虑,还有永久在路上的影象。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距家不远的一所学校当老师,拿到第一笔人为的我,在校门口的市场买了水果点心回家。记得那天下班后,我将用第一笔人为买来的水果点心,像儿时爸爸每周自行车把手上叮叮当当挂满食品去看爷爷奶奶一样,我也把食品盛放在塑料袋里,挂在单车把上,满怀喜悦地蹬着车子往家赶。塑料袋前后晃荡,乃至飘扬了起来。当我气喘吁吁地进家将食品递给母亲时,一家人围着方桌正准备开饭,父亲看到我买的水果眼睛一亮,笑着说道:“倒酒,喝一盅,尝尝韵儿的劳动果实。”果喷鼻香和酒喷鼻香搅和到一起,萦绕在屋内,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红光。我以为很骄傲,仿佛挣了钱买了食品拿回家,不仅意味着我经济上的独立,而且是我步入成人的仪式,这或许是我许久以来内心一贯默默渴望的。
我的学生生涯一贯非常顺利,成绩精良,懂事乖巧,是父母和老师眼中的宠儿。然而,大概苍天是公正的,总要在一个人的生平中增加一些磨难。我毕业参加事情不久,母亲自患绝症匆匆离世。尚未从失落去母亲的痛楚中规复过来,刚刚调动事情的我又遭遇单位改制。仿佛一夜之间,母亲去世,自己失落业,命运在一个不谙世事的纯挚姑娘面前露出了狰狞的面孔,昔日的家庭温馨再也找寻不到了,我险些被击垮了。为了生存,我给人打过工,又自己创业,在城南开预制件厂。住在市区、已经退休的爸爸常常骑着那辆陪伴了他生平的单车,跑来回近三十里路去看我。
父亲很快朽迈下来,步履蹒跚,踉踉跄跄,昔日高大的身影佝偻瘦小了许多,头发全白了。望着日渐朽迈的父亲,不由地想起他骑单车载着我的欢愉光阴,禁不住泪水盈眶。而今垂老的爸爸再也骑不动乃至坐不了单车了,这辆单车孤苦伶仃地搁置在地下室里,落满了灰尘,结上了蛛网,逐渐被我们遗忘了。但它仍旧那么坚固结实,漫漫岁月带给它的统统,丝毫没能压垮它,它就像一头任劳任怨的老牛,专一沐浴着风雨穿梭兼程,咬紧牙关默默无语地承受与负载着……
现在,它终于像岁月牙床里一颗彻底松动的牙齿,浑身高下生了锈,散了架,终极进入岁月的回收站了。
单车有着父亲的体温与脉搏,也储满了父亲与我那些重合的影象。它以自己生生不息的坚韧与温暖,覆盖和漫漶了我生命的一半多光阴,有条有理地陪伴了我蝉蜕般的发展,载我一起走过了许多成熟所必经的坎坷、欢快与无奈。
(编辑:高一平)
(本文图片由作者供应,如有侵权请奉告删除。)
作者简介
王韵,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作协签约作家,山东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山东省委文艺专委会委员,烟台签约文艺家,烟台散文学会副会长。山东首届齐鲁书喷鼻香之家、齐鲁文化之星。作品散见《公民文学》《文艺报》《美文》《莽原》等多家报刊。多篇作品被《散文选刊》《散文.外洋版》《外洋文摘》等转载,入选中国作协创研部等编选的几十个年度选本。作品入选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山东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山东作协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等。出版散文集四部,获奖多个。
壹点号烟台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