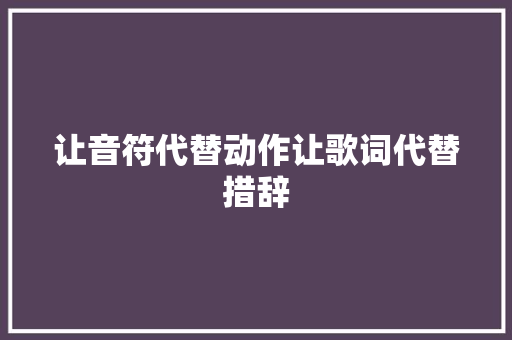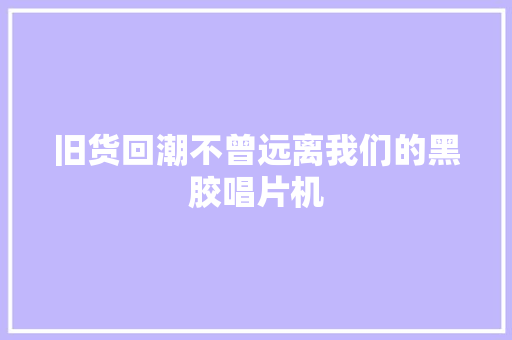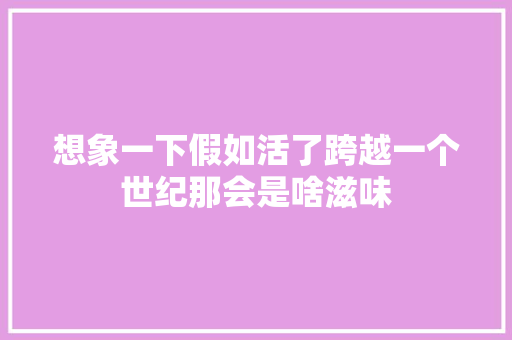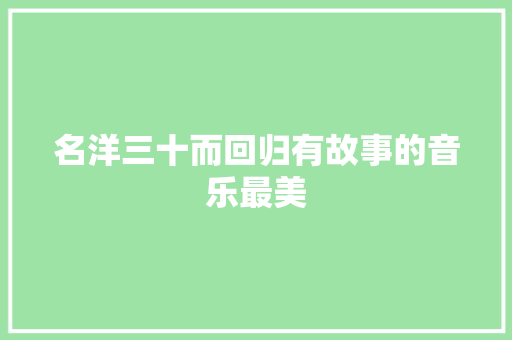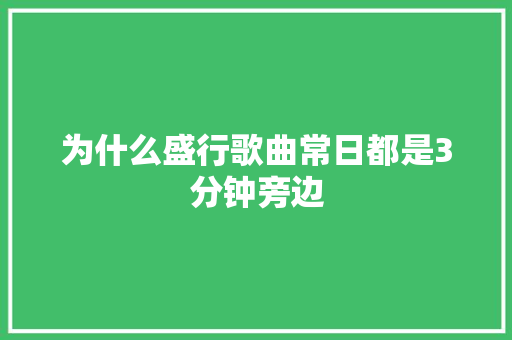有的人活在时期前面,那是我们常日理解的时尚、潮人、先锋,有些人选择活在时期后面,他们不管韶光,只管留在自己的钟意里,他们也很酷。
十多年以前,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由于补课的缘故原由,周末常在安乐一带晃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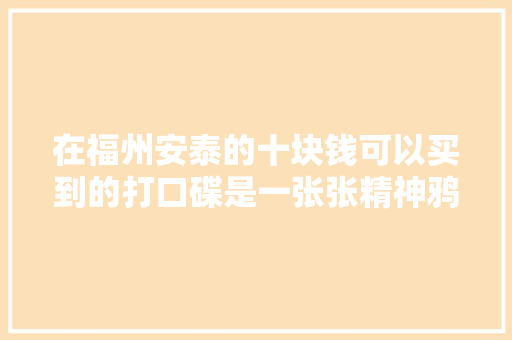
那是一个还有唱片行的年代,安乐图书城的斜对面有“你我音乐天”CD店,书店里也有很大面积的音像发卖区,如果你再往前走一些,还有更大的“音乐皇庭”。
当时的安乐十分繁华,不到七点夜市就会摆出来,窄窄的小道上流淌着熙熙攘攘的人流。
随着夜市涌现的,还有一群神秘的团体。
他们常驻于安乐图书城一楼的门口阁下,拉着好几箱的碟,带个鸭舌帽,坐在夜市摊位与书店门口之间不到五米的过道间,箱子里的碟险些都是国外的,鲜少见到华语碟的身影。
当时出于好奇,我就走近看了看,老板闇练地搬了张塑料椅子让我坐下逐步挑,然后问我:“小妹,喜好听什么?摇滚、古典、盛行、爵士、还是其他?”
当时只听过华语盛行的我被问懵了,然后我故作沉着地说:“随便,老板你推举几张吧。”
老板姓陈,熟客都叫他老陈。
老陈在箱子里闇练了翻了几下,给我递了张Miles Davis的专辑,说:“新到的,好货。”
《The BIrrth Of The Cool》,Miles Davis,1989
我清楚地记得,那张专辑的价格是15元,比唱片店的任何一张都便宜。
当时的我没有任何上网工具,听音乐的紧张媒介便是收音机和电视。回家后来我把碟放进家里的CD机,从此打开了新天下的大门,原来除了华语盛行外的音乐,居然也这么好听。
碟上的缺口
从那往后,我就常常去安乐买碟。
除了老板推举的一些,我还会挑一些封面好看的碟来听,不过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有缺口,只是长短不一。
缺口长一些的,老板就会算便宜些或者干脆送给你,由于这样的碟每每后面几首歌都不能听。
良久往后我才知道,这类碟叫「打口碟」。
《Part Lies, Part Heart, Part Truth, Part Garbage 1982–2011》,R.E.M,2011
打口碟是国外唱片公司保护自身利益的一种办法,唱片公司与艺人在签订唱片合约时,会有一条,公司担保卖出多少张唱片,然后根据卖出的唱片来支付版税。
但是,不会有人能把市场算得那么准,唱片公司在唱片加工时只能估摸出一个大概数字,比如U2的唱片估计能卖出1000万张,但实际上只卖出了990万张。
唱片公司只能根据实际发卖数字与艺人结算版税,剩下的10万张就不能结算。这些滞销的唱片,公司不能贬价或偷偷销往其他国家和地区,以规避向艺人支付版税。
于是,公司会当众销毁这部分滞销产品,这些被销毁的部分不再给艺人提取版税。
《Chicago Blues Masters》,Muddy Wates&Memphis Slim ,1995
打口,便是销毁办法的一种。
麦田守望者、左小祖咒、崔健和李志也都曾卖过打口,崔健、唐朝之后的一代北京摇滚乐手,险些没有不听打口的。
专辑内页
当时国外的专辑设计的都很有趣,专辑的内页很多都是由音乐人亲自设计的。
90年代末21世纪初,是打口碟最繁荣的时期。在安乐和师大附近,都可以很轻易地找到十几个打口碟卖家。
老陈也是个中之一。
老陈并不是最早在安乐卖碟的,最早在安乐卖碟的是几个四川人,后来他也随着卖,最初就在本地进货,但是销量都不是太好,后来买卖做的久了有些履历了,便自己去广东那边进货,从一堆又一堆的打口碟里选出自己满意的,再用箱子拉回来。
老陈的仓库就在安乐后面的一间斗室子里,顾客要的碟外边假如没有,老陈就会回仓库找,资源相对来说比较丰富。
贩卖打口的老板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品味,这直接关系到了碟的品质的好坏,只要说出几个喜好的歌手的名字,老板就能迅速而准确地给你推举好碟。
也正因如此,老陈积累了许多的转头客,当年在安乐卖打口的,没有人不知道老陈。
《Rocket Ride》,Kiss
打口的天下,是一种不用走出国门也能实现的精神冒险,它成长于规则与制度的缝隙之间,它们和那个年代顽强成长的摇滚乐一样,是地下的、是非法的、是主流之外的。
在每一个贩卖打口盘的地方,你都能从某个角落里抽出几只大纸盒,里面整整洁齐码放着数以百计种类不同的打口盘。
在夜色渐深,陌生人潮拥挤的街头上,有个这样彼此互不理解的人和你心照不宣,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
《Achtung Baby》,U2,1991
有人说打口碟的进入便是一场文化扶贫。
当海内唱片工业还处在在一个自欺欺人的期间时,打口一代学会了向它嗤之以鼻,而打口碟便是那个信息不对称、影音资源贫瘠的特定时代里这一小拨群体的光荣。
《Please Please Me》,The Beatles,1963
几年之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智好手机、数字音乐浪潮的兴起,人们开始利用更加便捷的手机来听歌,唱片行一波又一波的倒闭,面对数字音乐新天下,打口碟这个分外的行业链被排斥在外。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期,被称为打口碟闭幕的时期。
高三往后,由于学业繁忙,买碟这事儿也就搁浅了。高考往后去了外地读大学,打口碟这三个字基本就完备消逝在了我的生活中。
回到福州后的某一天,无意中翻得手机通讯录里老陈的电话,心血来潮便打了过去。
“喂,老陈吗?想问下你现在还有没有在卖碟?”
\"大众有,还是老位置,在一个卖鸡爪的摊位这边,随时可以过来。”
得知老陈还在卖碟,我感到很惊异,在这个正版唱片都不赢利的年代,更别提打口了。
自从东街口商圈逐渐没落之后,我大概已经有五年的韶光没有来安乐了。
安乐
如今的安乐和从前比较没落了许多,街道上的行人也很稀少,在这个从前寸土寸金的地方,乃至还建上了花圃,令人不免有些感慨。
在两辆电动车停放间隙的台阶上,有一个不起眼的小箱子,这便是如今老陈卖碟的地方。
从前,卖碟是老陈的主业,而在唱片业冷落之后,老陈不得不卖一些其他的生活用品来坚持生存。
我问老陈:“还有其他的碟吗?”
“有,刚刚进了两批货。”
说完,老陈便把我领到了过道摊位旁的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小仓库里。
老陈的摊位
仓库里堆满了老陈刚从广州拉回来的新货,按照音乐的类型分箱装好,老陈现在紧张做熟客买卖,都是当年累积下来的一些老客户。
“喜好买碟的人还是会常来买碟,有的人良久来一次,一挑便是一两千。现在的碟都不打口了,有的人的播放设备都很高端,打口的碟放进去对机器也不是太好,以是现在卖的险些都是原盘(没有打过口的碟)。”
老陈和他的仓库
“唱片业实在是不景气,中间有停卖过三年,后来做了些小买卖,以为还是放不下,这才又开始卖碟。现在福州在卖的该当只有我一家了,以前最多的时候这里有二十多家卖碟的。”
老陈对自己所挑回来的每一盘CD都如数家珍,现如今依然还是有很多人迷恋淘碟时与自己喜好的音乐人不期而遇的欣喜,常有人搬上一张塑料椅子,往那儿一坐,一挑便是一下午。
打口碟的时期已经由去了,而这个故事自始至终一贯沾满了街角的尘土和躁动的雄性荷尔蒙,它的参与者和讲述者们也一贯分享着一种来自地下的默契。
在一定意义上,打口向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城市青年洞开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梦幻情境,一顿没有发达成本主义唱片工业供销管控的发达成本主义唱片工业产品的盛宴,一座密匙在探索者自己手中的感官迷宫。
在打口市场最壮盛的十年里,来自穷山恶水的一支支地下摇滚乐队终于前赴后继地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壤,这绝不只是一次巧合。
看着碟上的缺口,忽然想起Cohen的在《Anthem》里的一句歌词:
“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万物皆有缝隙,那是光进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