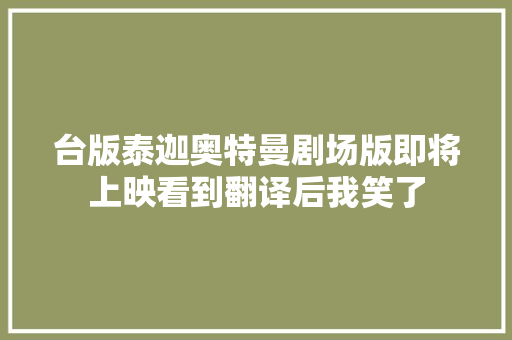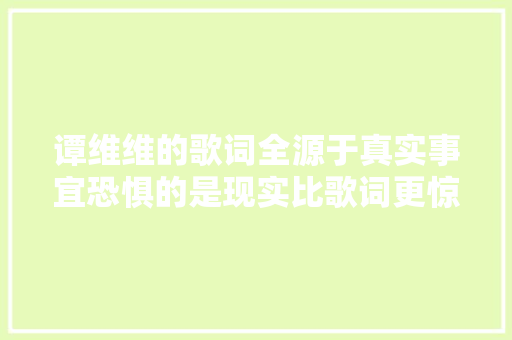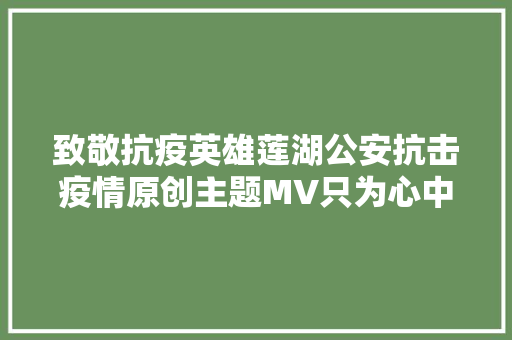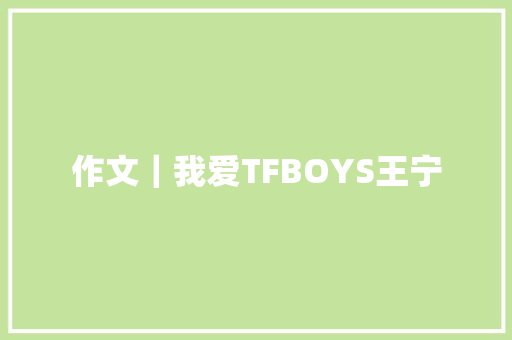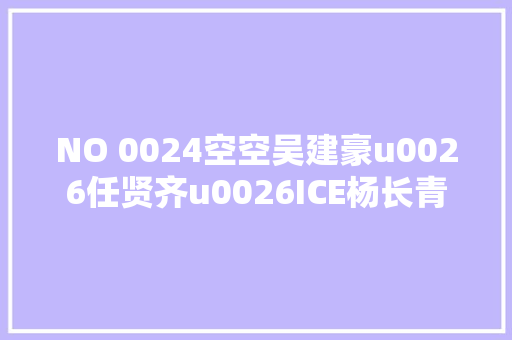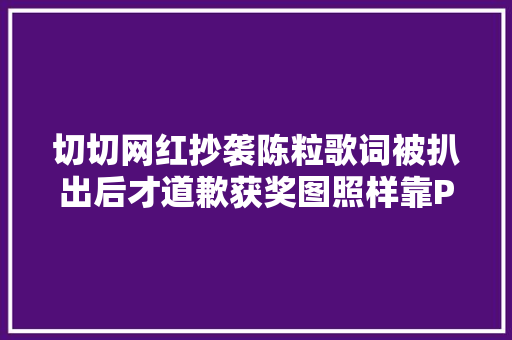1792年4月25昼夜晚,法国大革命时斯特拉斯堡市市长迪特里希忽然向坐在他身边的要塞部队年轻上尉鲁热望过去,问他是否能给来日诰日就要奔赴前敌的莱茵军写一支战歌。鲁热是个谦善的普通男子,他从不把自己看作一个大作曲家。他的诗从来未曾刊印过,他的几部歌剧均遭谢绝,他只知道自己即兴创作的诗歌写得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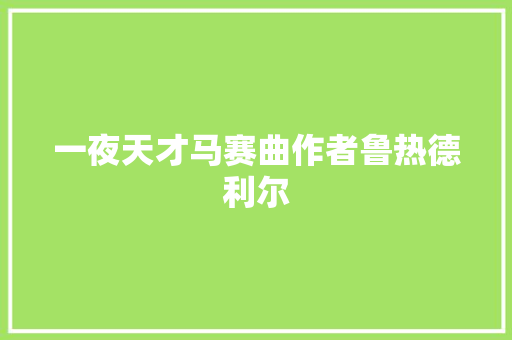
在革命的气氛中,人们的感情愈来愈狂热,客人们离开市长宅第的时候,午夜已过了良久了。就在这一夜之间,他用自己的全部激情亲切,恐怕也是上天的意志,让他写出这曲天纵之音,当他写完时,他乃至激动的倒在了地上手舞足蹈。他所不知道的是,在这往后,再也未写过一首值得令人称道的作品,这一夜也究竟成为他自己生平的绝唱。
4月25日,令斯特拉斯堡如此激动的宣战日已经结束,实在,4月26日已经开始了。夜幕笼罩着千家万户;然而黑夜只是幻象,由于城市仍旧激动万分。但《马赛曲》写完后的首演,市长和市长夫人都觉得一样平常,其评价仅仅是“社交界很满意。”
我们本日会以为这话惊人地冷淡,仅仅表示友好的印象、不冷不热的赞许是可以理解的,由于马赛曲的首演还未能真正宣示出它的力量。马赛曲不是一支供某一位嗓音悦耳的男高音歌手演唱的歌曲,不是为穿插在小资产阶级沙龙里浪漫曲和意大利咏叹调之间而写的独唱曲。这是一支感情冲动大方、节拍强烈、富有战斗力的歌曲,“公民们,武装起来,”这是向一大群人,向群众的呼唤,这支歌真正的乐队伴奏是铿锵作响的武器、劲吹的号音、齐步辇儿进的团队。它不是为漠然坐待舒适享受的听众,而是为共同行动者、为共同战斗者而创作的。它不适于单独一个女高音、单独一个男高音歌唱,而适于成千上万群众引吭高歌,这是一支堪称典范的进行曲,一支凯歌,悼亡之歌,祖国的颂歌。全体公民的国歌。鲁热的这支歌在激情中出身,也只有激情才能授予它以鼓舞民气的力量。这支歌还没有激起反响,它的歌词、它的旋律还没有深入民族的灵魂引起神奇的共鸣,军队还不熟习他们的凯旋进行曲,革命还不熟习她的永恒的赞歌。
即便一夜之间创造了这一奇迹的他本人,鲁热造诣彷佛不过是短暂的成功,这首歌也只是巴黎外发生的一件事,随后就将被人遗忘。然而,一件作品固有的力量是不会长期深藏不露或被禁锢的。一件艺术晶可以被韶光遗忘,可以被撤消,被埋葬,但富有生命力的事物总是要降服只能短暂存在的事物。
6月22日,在法国的另一端,马赛,宪法之友俱乐部举行宴会送别志愿者。长桌旁坐着500名血气方刚、身穿崭新的国民卫队制服的年轻人高唱着这首歌;此刻,他们的感情和4月25日的斯特拉斯堡一样冲动大方,只是由于马赛人的南方气质而更炽热、更冲动、更激情,并且不像刚刚宣战后那么盲目地充满必胜的信心,由于革命的法国军队正处于危险中。
7月30日,马赛营以军旗和这支歌为前导穿过市郊进入巴黎。成千上万人伫立道旁,隆重欢迎他们,这五百男子仿佛一个人似的高唱着这支歌,几次再三高唱着这支歌,步伐整洁地提高,所有的人全都屏息谛听。马赛人唱的是一首什么圣歌?这么美妙动听,鼓舞民气!
这伴随焦急骤的鼓点的号音,这“公民们,武装起来”的歌声,多么震荡民气!
两三小时往后,巴黎所有大街小巷都能听见这支歌。
于是这支歌如雪崩似地迅猛传播,胜利的进程势不可挡。宴会上唱这支歌,剧院和俱乐部里唱这支歌,后来乃至在教堂,唱完戴德赞颂诗后也唱这支歌,它很快就取代了戴德赞颂诗。一两个月后,马赛曲成了公民的歌,成了全军的歌。法兰西共和国第一任军事部长赛尔旺以其慧眼看出了这一支世无其匹的民族战歌所具有的振奋民气的雄浑力量。他紧急命令印制十万张歌篇分发全军。两三夜之间,默默无闻者的歌传播之广竟超过莫里哀、拉辛、和伏尔泰的所有著作。没有一个盛会不以高唱马赛曲结束,没有一次会战之前团队不高唱这首自由的战歌投入战斗。在热马普和内尔万,团队齐唱这支歌列队进行决定性的冲锋,只靠用给士兵发双份烧酒的老办法来鼓舞士气的敌军将领,瞥见成千上万人同时高唱战歌,着着疲弱的革命军高唱着战歌不平不挠的进攻,犹如铿锵鸣响的波涛冲击自己的军队,他们为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以同这首“恐怖的圣歌”反抗而大惊失落色,末了全线溃败。
其时,默默无闻的工程部队上尉鲁热正在许宁根的一个小驻防地郑重其事地画防御工事的草图。大概他已经忘却了他在1792年4月26日那夜已逝去的夜间创作的《莱茵军战歌》。在报上读到一首颂歌,一首战歌如狂飙一样平常征服巴黎的时,他压根儿不敢想这充满必胜信心的《马赛曲》的每一字、每一拍无一而非那一夜在贰心中、在他身上发生的奇迹。这真是命运无情的讽刺,《马赛曲》响彻云霄,却没有使这样一个人,即创作它的那个人出人头地。全体法国没有一个人关心鲁热·德·利尔上尉,一支歌曲所能获致的最巨大的名誉只属于这支歌,丝毫未曾惠及它的作者。歌词上没印上他的名字,在那些辉煌的时候他自己完备不被重视,也并不因此愤懑。
只有历史才能发明这种天才的革命圣歌,但历史最无情的是,作者现在已不是一个革命者;相反,没有任何人曾经像他那样,以其不朽的歌曲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现在他却不遗余力企图阻挡革命。当马赛人和巴黎的群众高唱他那首歌曲猛攻杜伊勒里宫,推翻国王的时候,鲁热对革命感到厌烦了。他谢绝宣誓效忠革命,宁肯辞职,也不愿为雅各宾党人效劳。他那首歌里唱的“宝贵的自由”,对付这位耿直的男子倒不是一句空话:他痛恨国界那边头顶王冠的暴君,也同样厌恶国民会议里的新独裁者、新暴君。
当他的朋友《马赛曲》的教父、市长迪特里希和吕克内将军(当初《马赛曲》便是献给他的),以及那天晚上作为马赛曲最初的听众的军官、贵族统统被拖上断头台时,他公然对福利委员会发泄不满,不久便发生了把革命的墨客作为反革命分子逮捕监禁的怪事,审讯他,给他加上背叛祖国的罪名。只是由于热月政变,随着罗伯斯比尔被推翻,打开了监狱的大门,法国革命才得以免除把不朽的革命歌曲的作者送交给“国民的剃刀”的耻辱。
倘若鲁热当时果真被处去世,倒还去世得壮烈,而不致像后来那么潦倒。由于不幸的鲁热在人间40多年,度过成千上万个日子,生平中却只有一天的那一个夜晚真正有着不属于他的天才创造性。他被赶出军队,被取消退休金;他写的诗、歌剧、文章不能揭橥,不能演出。命运不宽恕这位擅自闯入不朽者的行列的业余作者。这个小人物干过各种各样并不总是干净的小营生,困难地度过微小的余生。
那一次残酷的有时机缘使鲁热有三小时之久成为神和天才,随后又歧视地把他再度掷回原来的卑微,这无可救药地毒化了他的性情,使他变得脾气狠恶。他同所有的权势者都吵遍了,冲他们发牢骚,给要帮助他的波拿巴写了几封措词激烈的无礼信件,公然自满地流传宣传自己在全民公决时曾投票反对他。他的买卖使他卷入不体面的事务,乃至为一张未付清的汇票而被关进圣佩拉尔热债务监狱。他哪儿都不受欢迎,债主们追着他逼债,警察不断在暗中监视他,他终于在省里某个地方躲了起来,从那里,像从一个与世隔绝、被人遗忘的宅兆里似的,聆听有关他的不朽歌曲的命运的。
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听到马赛曲和战无不胜的军队一道攻进欧洲各国,后来又听说拿破仑一当上天子,认为它太革命,敕令把它从统统节目单中删除,甚至波旁王朝的后裔完备禁止这支歌曲。过了一代人的韶光,待到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他的诗、他的旋律在巴黎的街垒中又规复了往昔的活力,国王路易·菲力浦因他是墨客付与他一小笔养老金,使他不胜惊异。人们还记得他,这个偃旗息鼓的人,被人遗忘的人,以为这像是一场梦但这只不过是淡淡的影象而已。
1836年他终于以76岁高龄在舒瓦齐勒罗瓦去世,这时已经没有人知道他是何许人,没有人能说出他的名字。又过了一代人的韶光,直至天下大战中其时马赛曲已是国歌,法国各条战线又再度响起这支战歌,这位小小的上尉的尸体才被移葬在法国巴黎第七区的荣军院,和另一个小小少尉拿破仑的尸首放在同一个地方,这样,一支不朽名曲的极不出名的作者终于长眠在他感到失落望的祖国的名誉墓地,虽然只是作为独一无二的一夜的墨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