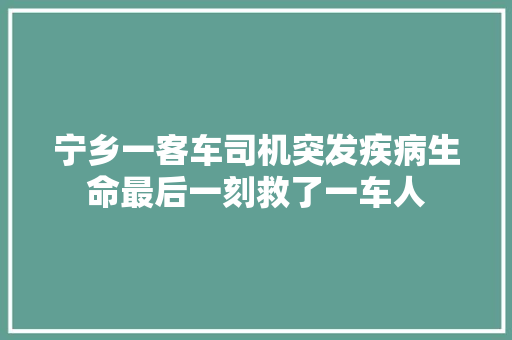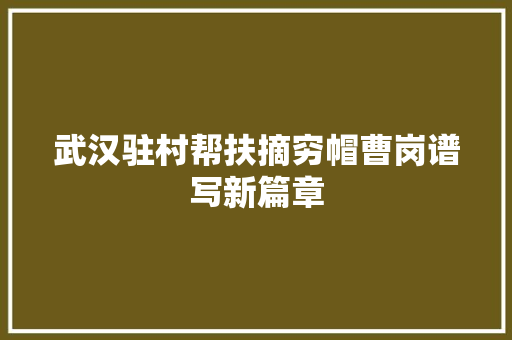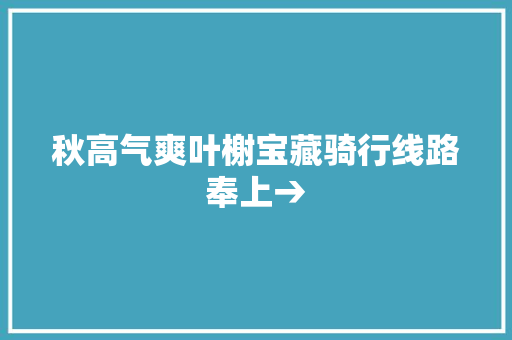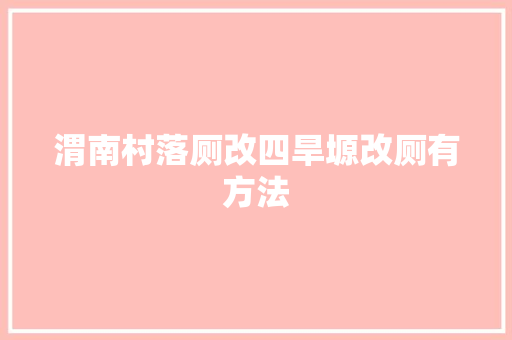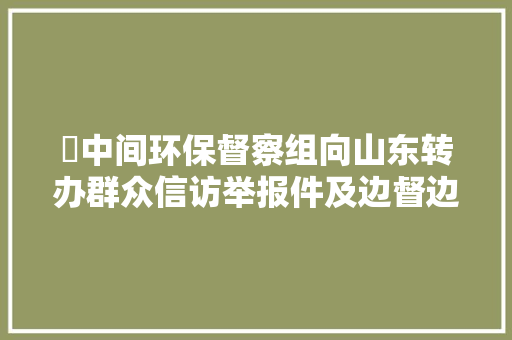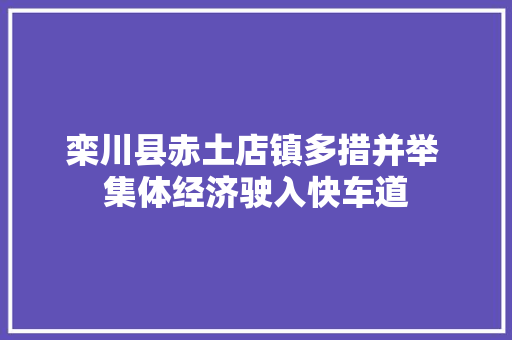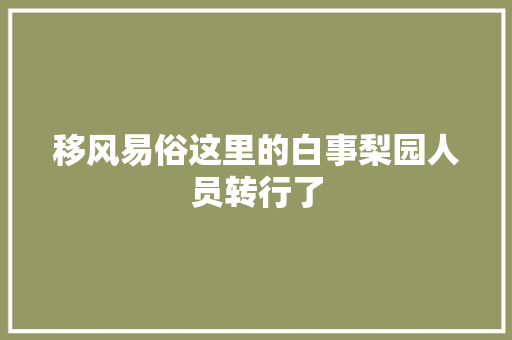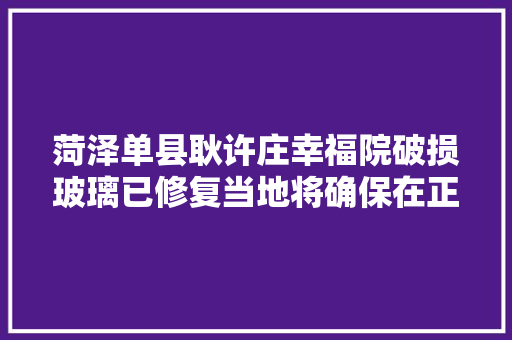石柴里
文/徐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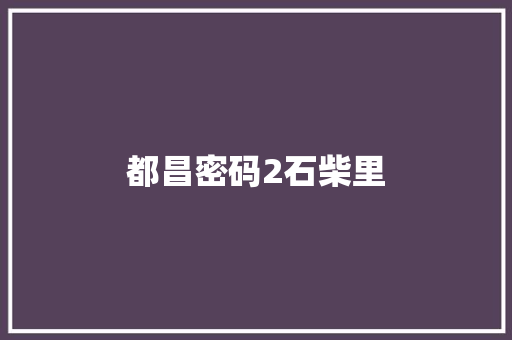
历史上,都昌县的徐埠镇曾风光一时。
古镇徐家埠,当地人简称“埠下”,历史上因水陆交通方便成水运要地,以繁荣的商贸成为都昌中北部的紧张商品集散地和全县的要埠名镇。《都昌名胜古迹》一书写到:这个地方是唐朝时位于蔡岭洞门的旧都昌县城的水运码头,商业非常繁荣。有旧时流传下来的《十字歌》唱到这里是:“十个大当铺,十个大作坊,船满十里港,街有十里长。”抗日战役爆发后,这里的买卖越做越大,客商越来越多,享有“小南京”的美称,有“买不尽的埠下,装不尽的吴城”之说。那时的徐家埠,棉花行有五家,南北杂货一百三十多家,能歇客百人以上的旅店一十三家,歇五十人以上的旅店有三十多家。
一个小镇,旅店总床位数达到2000以上,这是流动人口规模的直接证据。住店的都是买卖人,解放前的的一个县城,未必有这么大的商业规模。
旧时的徐家埠能成为一个商业繁荣的古镇,肯定与滨临鄱阳湖的一个大湖汊——北庙湖这一地理位置有关,另一个缘故原由,便是与唐代的都昌县治所在——洞门王市相邻。
本日蔡岭镇的洞门王市,之以是在唐时成为都昌县城所在地,该当是由于当时那片区域人烟密集。本日尚在的最古老的原住民石姓人,其先祖曾居住于此。
据《石氏家谱》记载,都昌石姓人的先祖最早的落户地点,是本日的蔡岭镇洞门村落委会辖地,又于几十年后迁到一公里外的,本日徐埠镇马矶村落委会的石柴自然村落。
石柴村落的历史有多少年?我们来看看都昌石姓的宗谱。
都昌石姓继承《忠纯世家》,尊石蜡二十六世孙石仲先(?—30年)为一世祖。仲先父石祎(前21—?年),字端饰,曾任桂阳令。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秩满回故里河南芑田,赁舟行鄱阳湖中,遇武陵蛮单、程二寇拦船劫财,仲先公为上保父母,下护兄弟及妻儿,挺身而出迎战水匪,与二寇奋力拼搏,终因寡不敌众,中箭溺水而亡。而家人却免遭其害,逃脱虎口,急奔吴后港。藏入九庙深林。越日祎公携妻家小,望山而行四十里,偶雨入庙,见有韩田二字。雨止,一老人揖问:“公家何往?此去三十里寸步难行。”“我张纯之字克铭,祖籍河南阳武,迁此地已三世,子因服徭役渺无音讯,后获信息亡。遗业老不能耕。”祎曰:“同命,同乡也。”“欲返故里,途经鄱阳湖遇寇,次子仲先中箭身亡,苦也。”“尔乡里可允我居否?”张公即允,二人即挽手相泪前行。乃寓居其家而获全焉,即今蔡岭镇洞门村落委会辖地。后仲先遗孤益仁聘克铭孙女张秀兰为妻。十五年后仲先弟季先携父端饰回祖籍河南,仲先母甄氏,妻崔氏,儿益仁(26—?)及儿媳张氏在韩田相依为命,经由近2000年的繁衍,石氏在都昌已形成王谢。
仲先孙石振,于东汉章和丁亥(公元87年),由韩田徙居三角塘枣木墩(白水塘),后人以其三十五世孙石楫字柴,号时具的字名冠于村落名,即今徐埠白池村落委会石柴村落。白池村落委会后并入马矶村落委会。
振公二十世孙石孜生两子,长石铎,幼石钟。铎公十世孙石蒿(公元941——1025年),字中岳,于宋太祖开宝年间由三角塘枣木墩移居旧宅场……
从公元30年年夜公元2019年,开始,石姓人在都昌已经繁衍了一千九百九十年。从公元87年年夜公元2019年,徐埠镇的石柴村落已经存在了一千九百三十三年。
一个村落落具有近200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若何的古村落!
我们来比较一下众所周知的那些古村落。
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落,建于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至今不超过一千三百年,享誉环球华人圈,其后裔总数有人统计近一千万,约占环球陈氏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抚州市乐安县流坑村落,始建于五代南唐升元年间(公元937年-942年),至今只有一千余年的历史,是中国村落庄旅游的著名目的地之一。
都昌的鹤舍古村落,于明嘉靖年间建村落,至今不超过五百年,2012年鹤舍村落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落。2015年被国家住建部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但是,除徐埠镇的人之外,即便是都昌县也险些无人知道石柴村落居然悄无声息地,一根藤瓜瓞绵绵地存在了近2000年!
不知道这个石柴里,算不算得上全中国最古老的村落落?
不是真有这可能,而是险些可以肯定。
由于历史上的多次大规模战乱,特殊是五胡乱华等外来民族入侵,使得中原人曾遭遇多次人口剧减。听说,五胡乱华时中原汉人遭屠杀百分之九十以上。历史上多次战乱造成的频繁迁徙,中原地区保留了很多古城,但古村落真不会太多。
网络查询古村落,极少有超过两千年的。而一姓传下来的近两千年的古村落,根本就查不到。
都昌的大姓村落落,差不多都有这样一副或者几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许可后人变动的对联。石柴村落不算大,但也有一副对联:孝谨传家,居卜鄡阳迁白水;忠纯受姓,远宗陵里近韩田。
石柴村落的石双喜师长西席说,都昌石姓第二代,即鄱阳湖遇盗身亡的石仲先之子益仁公,最早落户于韩田,益仁公之孙石振率家人从韩田迁到本日石柴村落。石振因喜好当地的源泉池,拆“泉”字,自号白水翁,源泉池因此改称“白水塘”。这是对联中“居卜鄡阳迁白水”的来由。“远宗陵里近韩田”指的是都昌石姓先祖益仁公及其祖母甄氏,母亲崔氏三人均葬于韩田。三人的墓至今保护无缺。
《都昌名胜古迹》先容,白水塘为都昌县最大一口古池塘,分高下二塘,两塘相连。上塘方广百余亩,中有一小土山,为塘中之岛,树木繁茂,时有禽鸣驻其上;下塘面积亦近百亩。清同治版《都昌县志》载:“每春夏之交雨多水涨,泛滥汪洋,望无际涯,故名白水塘。”关于白水塘名称的来由,书载与口传有异。
韩田与白水塘或者石柴村落的间隔很近,开车走村落道,弯弯曲曲的也就两三公里的路。石柴村落村落长说,如果抄近路不到一公里。
石柴村落先祖从韩田迁至本日的三角塘,说是“居卜鄡阳迁白水”,证明洞门的韩田便是鄡阳。并进一步证明:古鄡阳不仅限于本日靠近周溪泗山的,那片沉入鄱阳湖的地皮,至少,本日都昌县的周溪镇到三汊港镇到土塘镇到蔡岭镇洞门还包括徐埠镇的一大片区域,都是曾经的古鄡阳。
解读石柴村落这串密码,我们还能读出古鄡阳的什么信息呢?
本日的石柴村落是都昌县徐埠镇的新屯子培植示范村落。村落落不大,四十多户人家,房屋算不上奢华,有钢筋混凝土的小楼,也有传统的青砖瓦屋,但全都整治得错落有致,看过去让人舒适。村落内的道路和小巷都硬化了,下雨天不会泥泞。村落里的空地,没有一块杂草丛生的地方,都种上了绿化灌木或者草皮,路旁还像城里的花圃,设有低低的隔离栅栏。
随便走走,险些感想熏染不出千年古村落的气息。
和都昌所有村落落一样,石柴村落大堂庼门外有一口池塘。池塘面积不大,三角形,塘边也没有特殊大的古树,只有一棵碗口大的爬满了薜荔藤显樟树。
对一个村落落来说,门口塘既是风水的须要——依山傍水;更是生活的须要——洗衣洗菜。村落落门前的池塘在大部分村落落没有特殊的名称,就叫“门口塘”,但石柴村落的这口塘有不同于大多数的一样平常,叫“三角塘”。在新屯子培植中,石柴村落人特意在塘的东南岸边立有一块,上书“三角塘”。
三角塘写进了家谱,是石柴村落人的骄傲。
三角塘是从石柴村落迁徙到远方的石姓人的故乡的地标。从石柴村落走出去的石姓人,会一代一代见告他们的子孙,先人的故乡有一口“三角塘”。其后代回石柴里祭祖时,必须先找到“三角塘”,以确定是真正的先祖福地。。
石柴村落的三角塘,相称于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相称于鄱阳湖里的瓦屑坝。
还有枣木墩。石柴村落在祖宗堂庼边的一块空地上立了一块石碑,又请人写了一首诗刻在碑基上。只是,传说中的“枣树墩”完备不见踪影,石碑下是用矮栅栏围着的一块空地,空地上种了些花草。石柴村落人说,树碑的地方便是枣树墩原址。
实在,由一堆土突出来的那种墩,可能原来就未必存在过。这个枣树墩,是另一种观点的墩。
都昌人把户头叫“烟头”,把村落落叫“墩头”。究其缘故原由,第一种可能是鄱阳湖多水,墩因阵势高不易被淹,故用来建房居住,以是把村落落叫“墩头”;第二种可能是引申于瓜类的栽种。春天来临之前,有人在田边山脚锹出直径几十厘米的小圆地,用于逢春和栽种冬瓜南瓜或者瓠子,这块小圆地就叫“墩”。在墩上栽下两三棵瓜苗,瓜苗成长后开枝散叶霸占很大一片地方。有共同先祖的人,谓之“一根藤高下来的”。
枣树墩上开枝散叶繁衍出来的,从石柴里迁出去了多少人?没有人统计过。石双喜说,一代生两子,十代一千烟。石柴里人在这里住了一千九百多年,均匀三十年一代,一共繁衍了六十多代。他还说,村落里老人说以前曾搞过一次祭祖,不知道是明朝还是清朝,当时参加祭祖的人来自五省四十九县。
石柴里的村落名石碑,是迁到湖北大冶后裔赠的。湖北大冶后裔每年都派人到石柴里祭祖。湖北阳新,每年也有人来这里祭祖。
石柴人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财主石崇,其祖籍是都昌石柴里。
石柴村落的村落长说,石崇的爷爷一辈从都昌迁到鄱阳,然后石崇的父亲石苞成了晋朝的大将军。后来,石崇回到都昌修了个玳瑁阁,还留下一个金街岭的传说。村落长还说,石崇是上天封的“财王”,他上楼的木梯两边各有一口大稣缸,左边一缸金,右边一缸银。这两口缸里的金银便是传说中的聚宝盆,拿走多少里面又长出多少,永久也拿不完。
石柴里不仅有“财王”石崇,还有“力王”石辉德,“法王”石仕凯。石柴里的祖堂庼别号“凯玉堂”,取名于石仕凯和石仕玉两兄弟。现在的石柴里人,都是这两兄弟的后裔。
细读石氏家谱你能创造很多问题。自石碏起第二十五世石祎到都昌,二十七世石益仁在都昌结婚生子,二十八世石振即白水翁于公元87年从韩田迁到石柴里,年夜公元941年之后,才有后裔迁出都昌县的第二个石姓村落落。其间的八百年所繁衍的人都住在这个村落落吗?显然不是,从这里一定迁出了很多很多人。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不愿就近迁徙,就住在都昌县的其他地方,而要迁到那些本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远方呢?是由于那时的都昌不适宜人居住吗?如果真的不适宜居住,那么,当年51岁的做过桂阳令的石祎,为什么领着一家人在此住了十五年后再回到河南老家?又为什么把没有父亲的孙子石益仁留下呢?
最不可思议的是,石祎和三子季先回河南老家时,不仅留下了石仲先的儿子石益仁,石仲先的妻子崔氏,还把自己的妻子甄氏给留下了。留下甄氏很没有情由!
如果说甄氏病重不能远行,其三子石季先难道不应该尽为子之孝,待母亲去世后再走吗?
一定有情由,而且是非常充足的情由。
石双喜说,石柴里人有一个非常分外的葬俗:村落里的过世老人出殡时,无须抛洒黄表纸,也便是给孤魂野鬼的买路钱。石双喜阐明说,这一块地方是他们的先祖最先到来,相称于“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他们的后裔到了阴间,走的都是自家的路,自然用不着丢什么买路钱。
是石姓人来得最早吗?石益仁妻子的祖父,那个名纯之字克铭的张姓人呢?
由于取了人家孙女,张纯之又无其他后人,张纯之也能算是石家先人。
那么,那座写有“韩田”二字的庙是谁修的?有庙,肯定不但一两户人家,而该当是相对较大的一个群体。石氏先祖为什么直接忽略了这一个人群呢?
如果那些人都是番人!
蛮人!
就能阐明了。
拿本日的话来说,那些人都是少数民族。石祎之妻,石仲先母甄氏的留下与此有关。作为官宦妻的甄氏,其见识与处于蛮荒文明的少数民族女性比较,上风不言而喻。如果说当时的少数民族还处于母系时期,甄氏、崔氏极可能会成为氏族核心人物。石祎和石季先父子的离开也是必须,由于他们都是读书人。包括石益仁的后代,同样不愿意一贯生活在蛮荒文明里的古鄡阳,差不多都迁走了。因此,经历八百多年后才有了都昌的第二个石姓村落落。这已经是宋朝了,此时,从各地迁入都昌的中原人已经很多了。
石柴里过年的习俗,或者能证明这个猜想。
按过年的那些怪兽什么的传说,过年只在除夕,也便是尾月三十晚上。但赣北人常日过两个年。一为过年,一为辞年。辞年是统一的除夕夜,过年的韶光则不尽相同。有人说,过了尾月二十四,日日有人过年。
石柴里也过两个年,尾月三十除夕夜叫过年,尾月二十八叫过姑姐年。石柴里过姑姐年时,出嫁的女儿必须都回来过年。
女儿回家过年,在本日基本是天经地义的存在。但在上个世纪的很村落落,是绝对不许可的。有的村落落在新中国成立前有过年“赶野人”的习俗。那便是过年那天,安排一个后生领着一群半大的少年,手拿施肥的尿杓,站在进村落的路口,任何外村落人进入,包括本村落嫁出去的女儿,都用尿杓冚头。尿杓冚头是非常不吉利的,特殊是过年的时节,自然就不会有嫁出去的女儿回外家过年。
如果都昌石姓先祖来都昌时,当地原住民真的是处于母系氏族的少数民族,石柴里的姑姐年就非常好阐明了。
石仲先父子在鄱阳湖里遭遇的“武陵蛮”,石双喜说是王莽的败兵,我以为,也可能是当地的少数民族人。或者干脆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写到的“以捕鱼为业”的武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