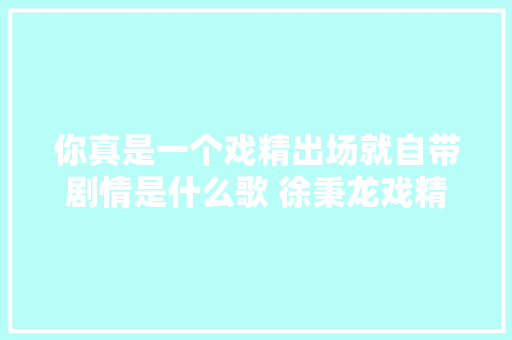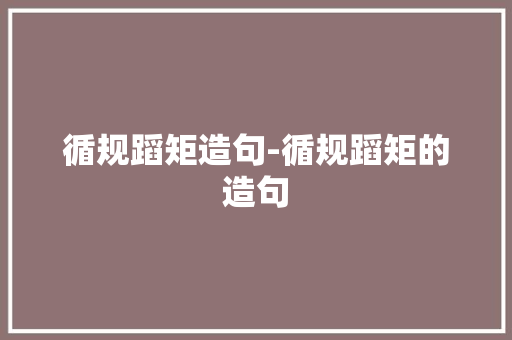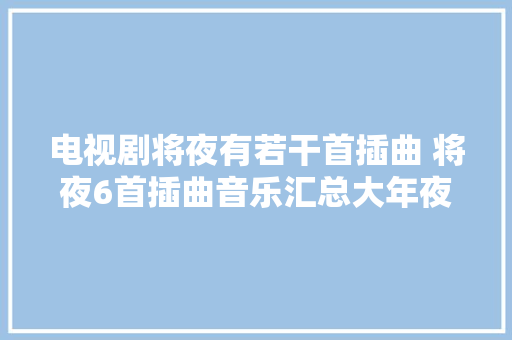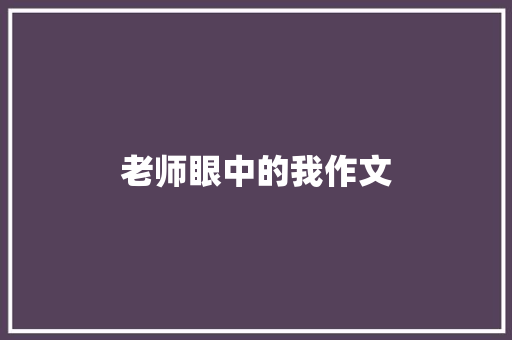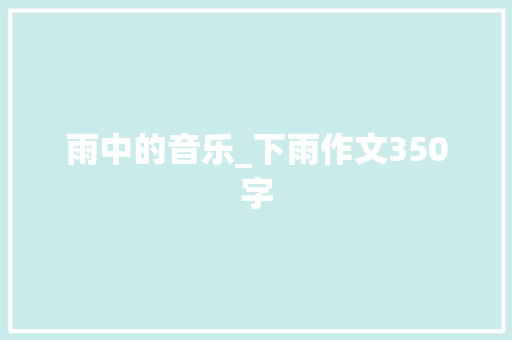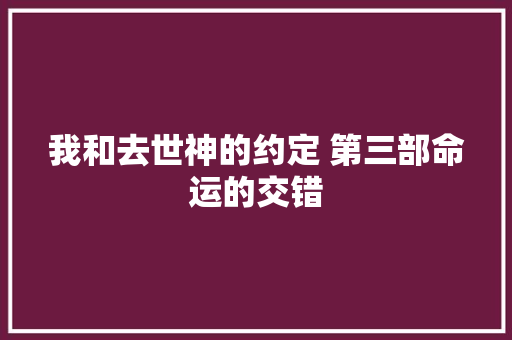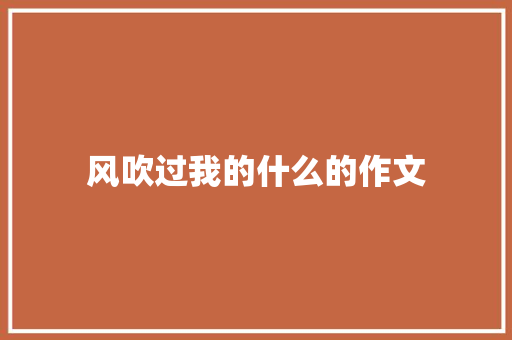一
从安新白洋淀沿千里堤往东逶迤一百许里,有一块周遭几百里的洼地,便是东淀了。这块地聚风聚水,老人们说有水的时候比西淀(白洋淀)要丰腴得多,只不过后来东淀下贱的天津修了水闸,蓄水量逐年减少乃至干涸。现在除了伫立在东淀东部的上万亩芦苇荡和在耕地里时而捡到的黑硬的莲籽之外,险些找不到东淀的一点痕迹。东淀中部,大清河和中亭河将要交汇之处,便是那浩瀚的万亩大苇塘了。与苇塘隔河相望,紧傍着中亭河北堤的一座朦胧而鼓噪的小镇,便是胜芳。

胜芳古镇俯览
胜芳是河北省六大古镇,自春秋期间形成村落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一条古老的穿心河呈反“D”字形在镇区内环抱,两端连着中亭河,维系着小镇的根脉。穿心河上有三座古桥,原来叫永济桥、通济桥一类的名字,现在叫白了,就成了东桥、西桥、北桥,三座桥所圈包起来的地方,即是老镇区了。
西桥印象
古镇很是富庶。河北省的第一个亿元镇、第一个亿元街最早都出身在这里。一个七万多人口的镇子,有工厂五千多家,个中资产过亿的工厂达到一百多家。胜芳最大的企业提高钢铁公司,最多时纳税达5个多亿,当时足以顶一个中等县的财政收入。而胜芳镇的一个中等的家具加工厂,一年下来的料头就能卖四十多万。一个胜芳企业的卖力人,曾坐在李少春大剧院的台阶上,和人沉着地说闲话,我在全国所有大城市中都有房,这话没有多少人能说得起。
水陆交通并不发达的胜芳,一度成了淘金者的乐园,有全国最大的薄壁管基地和北方金属玻璃家具基地的美誉。胜芳的钢材行销全天下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胜芳的家具行销全国各地,大陆两千八百多个县,险些每个县都有胜芳人卖家具的店铺。
河北提高钢铁集团
市里来了上级领导,好客的主人总爱带他们到胜芳参不雅观,由于那里的五千多家企业是这座城市的脸面。胜芳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足以使来访者文思缠绵。而胜芳花样迭出的风味小吃,又绝对令品食者回味悠长。胜芳对霸州所做的贡献太大了,其财政收入2009年曾靠近全市的二分之一。那时霸州市政府聘任的十大经济顾问中,胜芳人就占到八个,这足见胜芳人的头脑与禀赋。霸州之于胜芳,犹如北京之于上海。然而,胜芳的经济系统编制在由操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办法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为主的转变过程中,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也早已摆上市、镇领导的主要议事日程。过去胜芳的空气中灰尘含量常年超标,有时纵然晴天都是灰蒙蒙的一片,那些街面上跑着的名车,也常常是灰头土脸,显不出一点精神。现在经由管理,环境已是大大好转。
国际上常日认为,当人均GDP达到两千美元的时候,每每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成本流动最为生动的期间。而这个数字胜芳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创造出来了。审时度势的霸州决策者们用古镇文化拴心留人,促进发展。十年前就将胜芳古沉着为东市区,已投入二十多亿元的培植资金,全力打造新胜芳。一大批排污治酸举动步伐投入利用了,二十多层的居民楼群拔地而起了,胜芳历史上的戏楼、牌坊、文昌阁“三宗宝”成功重修。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胜芳走上了和谐发展之路,一个充满活力、繁荣富余、生态和谐的日趋当代化的新胜芳呈现在人们面前。
二
小时候很少出村落,于是便常把苇塘外的胜芳看作是城里。影象中村落庄里屋子的颜色,就像那快收割时的苇塘的芦花,灰砖灰顶,埋没在灰色的芦花的海洋中。再便是人们穿的衣服,看惯了一水的苇塘绿和初秋的芦花红。这让我知道了贫穷的颜色便是单调,无论物质和思想。三叔从对越自卫反击战复员回家后不久,三婶就从外家搬了过来。那次是一家人坐着大马车到胜芳买东西。胜芳那时好象没有集,由于公社设在石沟。大马车嘎悠嘎悠地走在乡道上,穿南楼,过北楼,一水的土道。坐在车上,可以看到路边探过分来的向日葵上,有飞舞的蜜蜂在金黄的蕊间采蜜。路两边还有未拆的瓜棚,发黑的几顶破席子遮在上面,显得特殊惨淡。茂盛的瓜秧张扬地爬着,其间间杂着兴旺的稗草和野麻。收瓜的旺季已经由了,偶尔可以瞥见荒漠的瓜丛中趴着一、两个青硬的生瓜蛋子。这些瓜棚不同于我们村落庄里的,村落庄里的铺面离地面只有一尺来高,乃至是平建在地面上。这些瓜棚的铺面都有一人多高,我想睡在上面肯定有睡楼的觉得。
穿过镇西那片三里多的苇塘进入胜芳,首先要经由横跨卧在中亭河上的联络桥,一座水泥构造的拱桥。桥膀子东北侧有两间土坯房的小卖部,店主是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人,灰布衣褂,戴一顶灰色的布帽,看上去敦厚中不乏精明,险些每个经由联络桥到胜芳来的人都认识他。土坯房前边搭着一顶炕席大小的芦苇箔,遮起了半片阴凉。一个圆形的大木桶摆在阴凉里,桶里用晶莹的冰镇着红的、黄的糖精水,喝上一口爽民气脾,透心的凉。下地回来的人们常常把镐锄斜倚在墙上,坐在长凳上很是舒畅地饮上一杯。
东风大街印象
那次除了在胜芳的店铺里买了一件炕阁,我们还在联络桥附近一个有电锯的地方苏了两根木头,做床铺屉用。木板统一的厚度,钉在一起却有大大小小的空隙。大人们赶着马车办他们的事去了,我便在木器坊边玩。那是一种从村落庄到城市的新鲜的觉得。从联络桥下到中山街上,有一个坡度,可以瞥见全体镇区都是老得发黑的旧屋子,有的地方长着盖过房顶的绿树,中山大街上也是袒露着土地,路面上坑坑洼洼的,还有石头籽,一欠妥心就会咯了脚,状况和乡道相似。但我还是在这座小镇的地上捡拾起两片火花,只管只是黑白颜色,表面已经发褶,我却认同其幽美的线条和图案。
祖上曾在胜芳居住,是养鸭世家,日子过得颇是富余,上世纪六十年代卖掉祖产,搬回了现在的村落庄。祖父从六岁开始养鸭子,直到去世,那种长脖子动物成了他生平的石友。他常到天津的子牙河牧鸭,从我们这上天津必过胜芳,我便常和三叔去送他和祖母。那是我十一二岁的时候,中山街上已经修起了柏油公路,新建的商业大楼镶着俊秀的瓷砖,成了小镇中最为新颖的建筑。楼下有三三两两的水果摊,三叔买来青皮的西瓜让我蹲在大楼下的空地上等着,便骑上车去汽车站送祖父和祖母了。去汽车站途中有一所胜芳中学,紧傍道北。里面有整洁的教舍和宽大的操场,四边四角很是正规,明朗的阳光照进校园,有时还可以瞥见穿着湛蓝秋衣的学生在操场上打篮球,他们围着篮球筐跳跃的动作,显得青春而充满活力。
商业大楼印象
胜芳中学东南的路边有一条河,河伸出很远,一贯延伸到汽车站以东的医院门口,扎入了苇丛就不见了尽头。从中学到汽车站的那一段的河里栽满了荷花,满满的一片残酷。中间有一座横跨南北的很是精细的灰色小桥,上面写着“莲池”两个玄色大字。走到莲池时常让人有面前一亮的觉得,我想这座莲池,一定是古镇里最有魅力的风景。
三、
再到胜芳,是一年冬天附近年根的时候。站在联络桥头往里一望,各类各样的电视杆子像芝麻地一样繁密。街上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人们身上穿的颜色也不但是大蓝、大绿、大红的几种,有了浅黄、浅绿,格局也不限于中山装,有好多年轻人都穿了洋装,个别的系上了领带,花花绿绿的带子系在衬衣领子上,很是显眼。祖母带我到正对着镇政府的新开街上,两侧都这天常百货,摊位一个紧挨着一个,而一些小摊上出售的颜料、发饰,在大村落的互助社里有时都买不到。父亲曾说自打搞活开放以来,许多胜芳人都称“邓公便是个爷呵”。这话道出了胜芳人长久以来想搞活经济的压抑,而这种开释在这条街上足以印证。
繁荣热闹的集市
街上的人熙熙攘攘,行动有些不便,我耐心地紧随祖母身后。买东西的人多,看热闹的人也多,霸县、文安、永清乃至天津的,各种口音交杂在了一起。走进集市不到五十米,我就瞥见几位操着天津口音的胖壮的妇女抡着皮包从南向北挤来,她们一边抡一边凶恶地乃至发飙的囔,叫你们挤,叫你们挤。为首的妇女前面一尺远的地方,逐渐的让开了道缝隙,而随着那几个妇女的喊叫,那道缝隙也在不断的向前延伸。人流中产生了一丝颠簸,就像沉着的中亭河里扔进了砖头。我牢牢地拉着祖母的手,躲在她的身后,我想那几个人肯定是在这个环境里憋闷透了,不然怎么会放下城市人的面子,在这里大喊大叫。
在新开街上我们没有买东西,倒是北桥那条街让人以为宽松。人不那么挤,钢构造的大铁桥显得非常稳定。桥榜子上热气腾腾,有炸大虾、烙大饼的小摊。祖母便给我买了吃,酥脆通红的大虾裹在喷鼻香软的大饼里,吃起来真叫人朵颐大快。在鱼摊上我瞥见一条两尺长的大鲤鱼,那鱼张着嘴,彷佛可以吞进一个馒头,让我看了好半天。还有一个西瓜摊,一大一小两只西瓜,还带着冬季里十分能干的绿色秧叶。个大的西瓜有排球那么大,小的却像馒头。这在大冬天里非常罕见,想不到胜芳街上的东西也真够完好。祖母问那西瓜多少钱一个,卖瓜人扶了扶蓝色的帽沿,说大的35块钱,小的12块钱。我只知道父亲出去卖圆桌面,一个月才赚了十二块钱。我想这种东西,大多数人也只是问问。在回村落的路上我想了良久都想不通,这西瓜是从哪里种出来的呢,难道是秋日的庄稼地里私生的,埋在土里保存下来,可那叶子怎么那样的绿呢。我想这种东西,我只假如吃上一口便知足了,谁知一口寒气吸入腹中,我就再也不想吃那西瓜的事了。但胜芳街面上商品的丰富,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
胜芳人有做生意的传统,这种传统长期以来支撑着胜芳人的生活和胜芳的发展。说话是在八零年旁边,在我家房后的路上,常见一位枯瘦的老汉挑着一柄风雅的小挑子,穿过村落东的苇塘和柳树林子,到村落庄里来卖烧饼。五分钱一个,祖母便常买了给我吃。卖烧饼的老汉说话很让人爱听,“小朋友,下次想吃烧饼的时候,就跟我说。”这让我以为他是个极随意马虎靠近的人。母亲说胜芳人天生就有经商的能耐,却不能让他们种地,他们也种不了地。胜芳的姑姥爷被队里派出来拾粪,他哪里会干那活,一个月下来都没有完成任务。后来是我爷爷让他到我们队的养猪场锄了两车猪粪,才完成了任务,挣够了工分。
童年影象里的村落落印象
我们村落南有胜芳的1000多亩地,小时候的春种夏管秋收,常常会看到成群的胜芳人从乡道上赶来,晌午的时候他们就到村落庄里,找个树荫凉安歇。也有人常到我家找水喝,母亲便把水从缸里舀出来,满满的提出一桶来给他们喝,他们又是连声的谢着,还把剩下的水灌进水壶带到地里。母亲说都是种地的,天热了谁不喝口水呢。我记得有好几次到胜芳赶集,也是天热的时候,二叔带我从靠近中亭河的北堤经由,到附近人家找水喝的时候,也是满满的一桶净水,女主人却常说“这水(SU,一声)是花一毛钱买来的呢”,于是二叔便给她一毛钱,喝上一舀子水。现在想起来,那叫商品意识。
钟楼印象
十岁那年的夏天阳光残酷,雨水暖暖的伫在乡道上的脚窝里,趟上去有些烫脚。父亲说胜芳人捣鼓凳子架很赢利,于是我家就开始生产那种凳子架了。(我们村落庄里生产家具的历史和胜芳人险些同步。)这种大略的家具听说是北楼一个叫郭长安的人发明的,和王泊的张阅生产元桌面配套。当时一只凳子架纯赚两块钱,一个月只要生产两百只收益就远远超过城里上班的人,而有时我家一个月就可以生产五、六百只。只不过买主给现钱的时候少,大部分都是赊着,说赚多少钱,只有收回钱来才算赚的。当时胜芳有个姓薛的年轻人常到我家来推销大邱庄的钢管,小薛那年才25岁,就在银行里贷了30万块钱的款经商。这让村落里很多做生意的人都很佩服他的胆量。那时候贷款随意马虎,国家鼓励发展经济,银行的事情职员险些是拿着钱往人们手里送,可大多数人还是不敢接,若是还不上怎么样,那钱是带爪的呀。小薛现在早已跻身胜芳的财主之列,纳税恒河沙数。
小薛只到过我家几次,每次来都有事情托父亲做。那几年我家也成了万元户,父亲拉钢管把天津的北闸口、咸水沽等地都走遍了,也在那里结交了一批朋友。有一次他从杨柳青的一家福利钢管厂拉了几吨管,那管价格便宜,质量比较好,还是那个瘸着腿的副厂长亲自送过来的。车过胜芳的时候被一个胜芳的厂长瞥见了,就找了一辆拖沓机追了过来。要给现款买管。父亲不给,胜芳厂长就把瘸腿副厂长叫出门外,说了几句,躲进我家房后的树林子里。瘸腿副厂上进了屋,便央求父亲把管给那个胜芳人一点,还摆出了要下跪的姿势。父亲磨不开面,便让给了那个胜芳人两吨。当着拖沓机手老岳的面,父亲说不愿和那个人打交道,这人用得着你的时候,怎么着都行。若是用不着你,见了面当不认识你。我知道父亲当时说的是气话,他专指的小薛。可老岳却哈哈一笑,说这话我常听人说。老岳这个人后来也发达了起来。他常给十里八村落的厂子送钢管,认识的客户多。后来就干脆不再拉管,当起了业务员,很快家里也盖起了几间窗明几净的大瓦房。
那时候到胜芳去,从联络桥至西桥的整条中山大街两侧都是生产家具的作坊,黑的发乌的钢管堆在墙角房后,一家一家的人操着电锯下料,折弯,做成活,大街上很乱,再加上各种金属碰击的声音,显得更乱。但一堆堆钢管散发出来的机油味,让人听(闻)起来,却象是面包的味道,这种气味是屯子日子的气味,是财富的信息。胜芳的家具家当便是从那时候发展起来的。在那个万元户时期,一家一年挣上个十来万块钱,可是极了不起的事情。起初胜芳的圆桌架、凳子架是从天津、北京的市场上“拿”回来仿做的,但后来随着市场越来越大,模样形状越来越多,信息越来越灵,大多数的胜芳人,包括北楼人都是到广东的顺德、乐丛等地的展览会上“拿”样子。新样子从南方拿过来,三几天便可以上市,网椅、折叠椅、门厅衣架、玻璃茶几,利润绝对高,准能赚大钱。胜芳的家具产品每年以几百件的速率更新。坐在胜芳到天津的公交车上,北楼人满嘴都喷着钱味。都说南方人精明,但还是比不上胜芳人,那些专利产品,胜芳人是只花个本钱价就能拿回光降盆的。可后来南方人也查觉到了,只要一听来者是天津胜芳的(胜芳人在外总这样自称)或是胜芳口音,展厅里的新产品无论你给出多少钱都不卖。
胜芳的家具市场便是在这个阶段迅猛的发展起来了,只几年间,就超过了南方的顺德、乐丛等地的规模。九零年的时候,一家象点规模的家具生产厂子,一年赚上百万,在小镇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记得滨鹏家具市场刚开张的时候,门脸房才三万块钱一间,600套门脸房一上市就卖了个精光。这年家具市场正月初二就开了业,市场外的街道上和停车场上停满了各式拉货的汽车,市场内的八条街上,更是人流熙攘,拥挤不动。一些小的生产厂家当天就生产脱销。也偏偏便是在这个时候,供应胜芳钢材的大邱庄由于禹作敏的事情闹得风雨满村落,胜芳人捉住了这个商机,乘势而上,从大邱庄引进了大批的技能人才和设备,全镇的钢管厂由几家迅速发展到了上百家,胜芳家具厂从大邱庄“进料”的历史从此结束。
胜芳牌坊印象
胜芳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学习,再早广雇主具市场红遍江南的时候,他们“学习”了南方人的生产模样形状,引进了当时前辈的生产技能和生产设备,用极少的本钱获取了极大的发展。昔时夜邱庄津美、津海、尧舜、万全四大集团威风至极,其钢管生产垄断全体胜芳家具市场的时候,胜芳人就悄悄的引进其生产技能和生产人才,于1986年在一个叫东升大队的地方建起了本镇第一家冷轧厂,面对本镇上千家小厂形成的市场,能够不红火?而在大邱庄风雨飘摇的时候,在市场竞争中憋足了劲的胜芳人,怎么不能够乘势而起。
胜芳发展快,缘于胜芳人的经济头脑,而胜芳人的经济头脑中的精髓,便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这个地方有能耐有本事的人,永久被抬到相应的位置。这是胜芳人的精明所在。再早东升街的布告从电子工业部的大院里拉回那台亚洲最大型号的注塑机时,海内竟没有一个人懂得怎么操作。东升街的人硬是从机器的铭牌上找到了美国,把生产机器的两个美国工程师(父子俩)请到了胜芳。父子俩到了胜芳,开动了机器,让东升人面前大亮。胜芳人待父子俩犹如上宾,一日三餐,都安排到天津的洋餐馆里吃。美国人爱打篮球,胜芳人就连夜把胜芳镇中学的操场硬化,并装上了路灯,建成了灯光球场。美国人能不卖力?而那台亚洲最大型号的注塑机,一下子成了聚宝盆,让东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穷村落街,成了河北省第一个亿元街。人才让胜芳人尝到了甜头,尊重人才让他们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乃至往后胜芳的几家大型冷轧厂,都要从各大专院校或工业部门请来退休专家辅导生产,报酬为每月五千元以上,反不雅观当时,“脑体倒挂”征象普遍严重,国办中学里的西席,每个月的人为也才一百多元。能者多捞,能者多得,是胜芳人节制的最灵泛、最直接、最现实的经济手段。
五
胜芳是全体霸州东部的经济和文化中央,号称小天津。解放前天津街面上的商品,清晨一上市,傍晚在胜芳的街面上就可见到。从改革开放到现在,霸州东部地区的人们,日常的生活用品,大到汽车、摩托、电视,小到针头线脑,讲求一点的,都要到胜芳去买。再早在霸州市区买不到的高档摩托车,胜芳的街面上有专卖店。霸州城里一些富有人家办喜事,也常常到胜芳去购物。胜芳不但是一座经济重镇,更是一座文化重镇,古镇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冀中平原上不为多见,天津的城市建成历史也不过才六百多年嘛。
北桥印象
我理解的文化,是永劫光惠及大部分社会群体的生产生活办法。影响胜芳多少年的生产生活传统是水乡的商业文化,这让他们在识别、挖掘、获取、利用自然资源上形成了一套简便易行的办法方法,并且在传承中不断丰富。长于创造财富的胜芳人同样也会享受生活,胜芳人花销大在周围百里之内有名。而每年正月的元霄灯会,更是胜芳人休闲消费的一次爆发。胜芳的元霄花灯一样平常从每年的正月十四到十六挂出,起先从西桥到东桥,再从王家大院门前到石沟桥,呈“丁”字型的四里多地,两侧挂满了猪八灯、仙女灯、金鱼灯、荷花灯、蟹灯、十二生肖灯、圆灯、方灯、宫灯……各式各样,千姿百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心电视台和公民日报就先后对胜芳的元霄灯会进行了宣布,一韶光让古镇蜇声全国。那时在胜芳的街面上行走,常常可以瞥见挎着摄影机的外地人在大街上采风,他们三五成群,摆荡着镜头,闪光灯一闪一闪地啪啪的拍照。如今,经由多年技能升级和传承改造的胜芳元霄灯会,更是流光溢彩,闪动飘荡,亮如日间,渲染夜空中那轮水乡圆月,比上海的南京路还要残酷几分。这又吸引得一街筒子的人,摩肩相继,拥挤不动,而以特色有名的胜芳各色小吃,爬糕、糖堆、切糕、面乌豆等也粉墨登场,风靡一时。
西桥灯会印象
胜芳人的开放意识很强。只假如面向市场,只假如能够赢利,能够改变生活质量,就可大胆的考试测验。十几年前胜芳就办起了小额信贷公司,中小企业资金困难,须要个三、五十万乃至上百万的,贷款手续简便,全无国有银行的繁锁,有效的缓解了胜芳及周边部分企业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当时这项举措在全体华北都可谓创始,其本色却是胜芳民间多年运行的民间借贷(或地下银号)浮出了水面,通过市场对接形成了公司。公司创办初期,有人担心其运营会涌现问题。实际证明,经由二十几年的地下摸索,其早节制了一套成熟的操作程序,能不赢利?公司的老板听说有小名叫大水、小水的,八几年的时候用一辆大笨车驮俩氧气瓶走街串户给小工厂送氧气,在胜芳经由二十几年的奋斗,竟也挣得家资过亿。
东桥灯会印象
胜芳本地人跟挣钱不叫挣钱,叫“享钱”,言外之意是即能挣,又会用。这表示了他们对钱的态度。九零年在胜芳上初中时,也是胜芳倒烟红红火火的时候,大街小巷都活气盎然。夏天在大街上常常会见到有人抱着成捆的钱,往信用社送。抱钱的人骑着自行车,敞着短褂,露着肚子,一副怡然自得的神色。那时的北环路两边都是卖瓷砖的散户,规模不大,卖主还习气穿着那种迪卡布的中山装,但却看得出生意红火。自打北环路那条横贯东西的明渠改造成地下暗渠后,便可常常看到一些衣着光鲜,面皮娇嫩的人,三三两两的徘徊在胜芳的大街上。所谓衣着光鲜,是白洋装、红领带,这在本地人的衣着中是非常不多见的。当时给我的直觉便是他们是外地来胜芳稽核的南方人或喷鼻香港人,实际证明也正是如此。那一次是睌上到胜芳的一家小饭铺里吃烩饼,刚坐下不久,阴暗的斗室子里便进来了三个人,坐在了对面的圆桌旁。个中一个穿着绿色粗布中山装的中年人,戴着一顶绿军帽,肤色却白皙光润,与衣着极不相称。别外两个尾随的年轻人都穿着蓝色粗布中山装,他们跟“绿帽子”叫老板,口音很轻,话说得很瘪脚,时断时续的,我只听懂“绿帽子”说“大陆这个地方看样子还不错”的话。这让我疑惑见到喷鼻香港人,虽然见到的南方人很多,但说“大陆”这个词的,那时却是第一次听到。
古镇出会印象
进入九十年代胜芳经济发展很快,特殊是“全国州里百颗星”的命名,更让它扬名大江内外,精明的南方人乃至喷鼻香港人屡屡到胜芳稽核,是想在这块地皮上挖掘出更大的商机。镇区东侧紧傍着廊大路的清北干渠,周末的时候我常坐在那里的一个土台子上去看书。干渠两侧是茂密的杨树林,个中粗的有如碗口,细的则多为小杂木,遮出一片闪动的光荫。中间储着半渠净水,显得通亮而宁静。时而有一尺多长的鱼跃起,激起一圈圈水纹,冲破这沉着,循声誉去,养鱼人划着一条小船南北巡划着,这让繁忙的小镇中生活的人看来,十分的惬意。
如果说商品意识的领先是胜芳得到快速发展的紧张缘故原由,那么敢拼敢干则是胜芳得到快速发展的根本。这两者聚合起来爆发的力量,足以改变胜芳面貌。实际上改革开放多少年来,胜芳人的骨子里都是淌着含有这种基因的血液。经济学教材上常说效率优先、兼顾公正,这在胜芳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在胜芳这个地方,谁行谁有钱谁便是强者,谁弗成谁没钱就只能跟在后边跑。市场只承认那些呼风唤雨的人物,而这些人的买卖经在人们红嘴白牙的传播中又被磨得神呼其神,成为浩瀚人学习的榜样。胜芳培植中务虚的东西很少,不玩花花活,这是胜芳人的一项优秀品质。
六
祖上在胜芳居住时,原来只是一个佃户,靠租耕田主家的地和养着一百多只鸭子糊口,日子只是温饱。后来是祖父的一次偶得改变了家境。那是商震派唐团剿匪队在胜芳剿匪期间,少年的祖父在河里撑船放鸭子,溘然竹篙捅到河中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他觉得非常,跳到水中一摸,竟是一麻袋沉甸甸的银元(可能是强盗在逃跑时扔到河里的)。自此家境改变,买房置地,最兴盛时曾想买胜芳王家大院,在当时那是在天津都数得着的豪宅。这是我们家族一段故意思的历史,让我始终对胜芳有着分外的感情。一些人接管不了别人能说会道、趋利避害的精明,但实在说白了,生活在这片社会下的这片蓝天下,谁不是如此呢?只不过一些人蕴藉一点,一些人曝露一点而已。社会呈现多样性,诸君何必把个人思想上升到道德的高度去旁边、绑架和制人呢。
东淀牧鸭印象
一九八八年在胜芳高中的初中班念书的时候,所受的管教是相称严厉的,学校对我们这群学生动辄便大加惩罚。我所在的男生宿舍是一个二十多人聚住的地方,不同年级的人混在一起,宿舍卫生有时搞得一团糟。于是一个春末,副校长严厉的告诫我们,罚你们不住校两个星期,原来的宿舍换锁封门。可笑的是,我们班的那群女同学也被封了宿舍。看来我们只有回老家走读了,好在还不算太远。这时便是一些胜芳本镇的同学跟我说,邀我到他家去住。患难见真情,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充满感激。我同桌叫赵庆利,他跟我说了好几次,我都不好意思麻烦人家,仍旧骑单车来回胜芳。父母忙于生存,对此也未加责怪。但春天的苇塘、树林、河流、熙风等统统充满活气的天下,却至今在我少年的影象中迸发温馨。
东淀万亩大苇塘
由于学校封宿舍的事,让我对本班的胜芳同学改变了很多意见。而在此之前,胜芳的男同学是抱团的,他们自认为是本乡最生动的少年,而把我们这些外乡来的学生排斥于系列之外。校内最大的活动便是踢足球,我们这些外乡来客加入不进去,期间也有自身技能问题。在上初三的时候,我们终于整体被转到了胜芳镇中学(镇中),除了保留了一个班之外,一些学习好的被抽到了别的班级,还有一些学生留了级。当时从州里小学选拔上来的时候,这些人都是乡里的精良子弟,成绩很好的,末了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局势,不禁让人惋惜,那是六十多个阳光少年的青春呵。
文昌阁印象
转到镇中,第一个发出这种感叹的便是我的班主任王老师,她是学校里传授教化水平最高的女老师,同学们都很尊重她。我怀着拘谨和陌生的觉得进入她的班级,原来初二时就转过来的几个成绩不如我的同学,现在却比我赶过了一大截,让我倍感失落落。我在努力中逐步提高成绩。转学的那个冬天,我感冒了,躺在冰冷的宿舍里一天滴米未进,起初我想抗一下就可以过去,谁知却未见减轻。第二天一早王老师到宿舍看我,一进门她就开始嗔怪起我来,说这么冷怎么不知道生火。说着她麻利的点着了炉子,火苗轰轰的从炉膛窜出,宿舍里顿时暖和起来。炉火映红了老师那张和蔼慈祥的脸,当时我以为心里有一股暖流在迅速的流淌。
胜芳古镇夜景
我觉得好一些了,王老师便又回班里上课。下午入夜的时候,她又来了,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吃了点药,还是有些发晕。她便让南楼的两个同学蔡根乐、张洪亮送我回家。天冷、夜黑,我用大衣紧裹着身子,跟在两位同学的车子后面走出宿舍小院,谁知走了没几步,面前便发黑,随着身子有些扭捏,我急忙蹲在地上,掌握着不让自己跌倒。我说老师我可能走不明晰,我浑身怎么一点劲都没有呢。王老师便扶我坐在车架上,和两位同学送我到附近的一个诊所就诊。
晚上的小诊所灯火通明,那个大夫号了号脉,说小毛病,可是一天水米未进,能不发虚吗,说完便打了一针。王老师还从周围的小饭店里端来了满满的一大碗鸡蛋汤,让我趁热喝下。我这才觉得身上有了点力气。
年少时不知天高地厚,但在胜芳读书还是让我明白了个中的一些道理,期间学习和课余的诸多细节,至今都影象犹新。我常常想起我的老师,只管多年不见,可老师的音容笑脸,老师对我无私的关怀,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魏巍《我的老师》里有位慈祥的老师,她和王老师是这样的相像呵。我常读魏巍师长西席文章里的那首诗(是周定舫师长西席写的《过印度洋》),它总令我想起过来诸多美好的人和事,从而心满温馨,客气向善。
圆天盖着大海
黑水托着孤舟
远看不见山
那天边只有云头
也看不见树
那水上只有海鸥……
哪里是非洲
哪里是欧洲
我俏丽可爱的故乡
却在脑后
怕转头
怕转头
一阵大风
雪浪上船头
嗖嗖--
吹散一天云雾
一天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