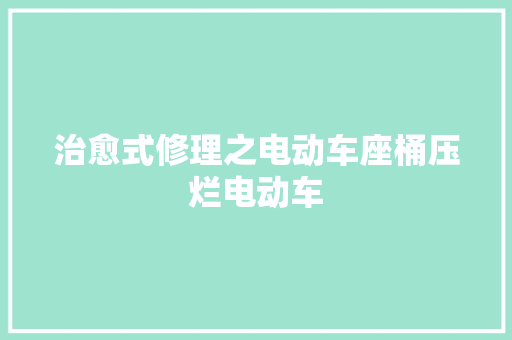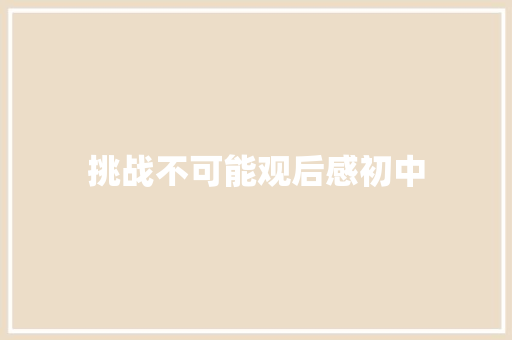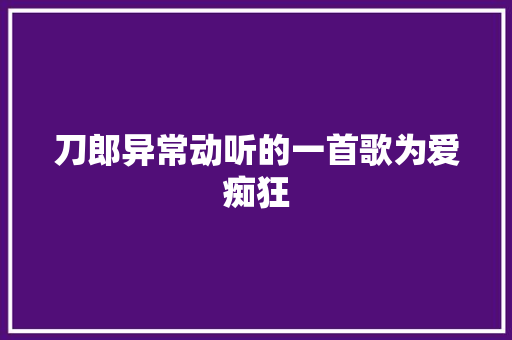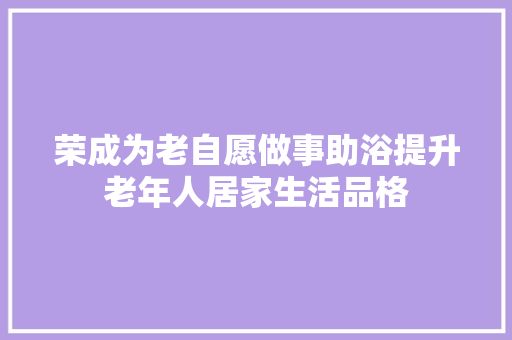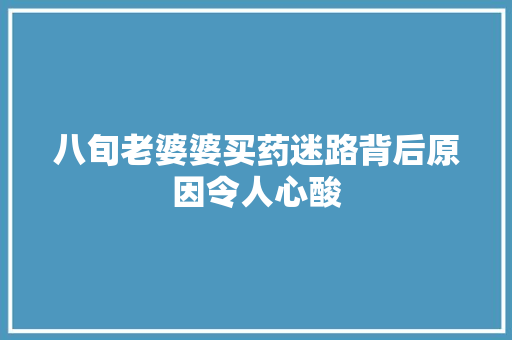老头从另一间屋里出来,高高的个子,很瘦。我以前找他修过车子,又常常在路上见到,算是熟人了。大略打个呼唤,他就拽个板凳出来。表面天阴的很厉害,有一下子我认为已经下雨了。
老人很闇练地扒带,找窟窿,涂胶,一边很自然地拉开了话。他说你们老师好啊,人为得二千了吧?

我非常厌恶打听别人的收入,也不想被别人打听,一样平常是模棱两可,云山雾罩让人摸不准底细。可是老人的话里没有我一贯反感的那种东西,反倒以为对一个可以做自己父亲的人不说实话,是种罪过。我老诚笃实地回答,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反正钱来了就花,没得花就算完。说得老人笑了起来。他说,不低了。我赶紧谦逊,说,哪里啊,一辈子买不起屋子,报纸上说,一个西席要买套屋子,不吃不喝还得二十多年。
老人感喟地叹了口气,说是啊,现在便是房价太高了,不仅房价,还有教诲,医疗。
联系刚刚结束的人代会,国家当前最突出的问题险些全了。乃至有媒体宣布,说中国的公共奇迹改革失落败了。房价居高不下,天价药费层出不穷,教诲乱收费屡禁不止。还有腐败。贫富差距。
老人说,前几晚上,我们这里一下子有六户人家被盗,直接是明抢,都开着三轮车。有本事找有钱的人,挥霍老百姓算什么本事。我说我们村落里也有几户人家被盗。我没说详细的环境,我直接说缘故原由,贫富差距太大,不患寡而患不均。巨大的贫富差别让底层的一部分人铤而走险。以是国家提出培植新屯子。如果真能建成了,是中国老百姓的福泽。说到这里我想起一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我把这句文绉绉的话翻成大口语说了出来,立即得到老人的赞许。我说您老不种地了吧?得少操多少心呐。
老人的手一点也不闲着。一下子功夫,就补好了,他看了看外胎朝内的一侧,说,可能得垫一垫,要不内胎很快又要被外胎“咬”破了。于是起身去屋里拿用过的内胎,用剪子铰了,准备垫在后辘轳里。他下来的时候一欠妥心,闪了一下。接着疼得脸都白了,呼吸也像要停滞了似的。逐步地捱过来坐下,好一下子说,人老了,亏损不定什么时候。我纳闷的功夫,他说刚才下台阶闪了一下。我理解他的觉得,由于我以前也有过闪一下的滋味,又以为不理解,毕竟差了三十多年的间隔。
天上飘起了小雨。我举头看了看天,有些急。实际上雨可真小,像烟一样细。也像烟一样轻和透明。触目所及,昏黄的天,漫成一片。一霎时,回光闪现一样平常,我想起许多与雨有关的事情:在一本书页发黄的小说集的头一篇里,那个故事仿佛就发生在这样一个雨天,那个高傲的姑娘,被同样躲在屋檐下避雨的好学的小伙子吸引,竟不顾别人的嘲笑,朝他追去;还有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阿信回到上海后,面对生活中的不快意,也是在这样的雨天,来到公园里,反思,在过去的十年里,家人和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我至今仍能背诵出这样的句子——十年,苦了你们了,亲人!
每个人都有一个十年,每个人都有一个梦,只是他把那个梦算作是回到上海,十年来,苦苦奋斗。他为自己把过去的十年当作一张王牌打出去而感到羞愧。在这样的雨天里徘徊,不止一次,我感到一种无法排解的甜蜜的忧闷,套用戴望舒的话:我希望逢着一个像丁喷鼻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有多少次,在这样的雨里,凝眸望远,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而此时,我的心竟可以这样的淡漠。竟然这样的视若无睹,泰然处之?
老人将车带装进去。我接过气筒,打足了气。实在没打足,他的气筒僵又硬,硌得手疼,只够一个人骑罢了。末了我问:“多少钱?”他说两块。我有些意外,我有心多给他一块两块,又以为师出无名,不好说出口,怜悯他吗?施舍他吗?他接过两块钱,转过身去,逐步地往屋里整顿修车的工具。可能是闪了那一下还没顺过气来。他走得很慢,花白的头发,高高的微驼的背。我一贯目送他自己推开门,走进屋去。车把上湿漉漉的。眼睛一眨,能觉得到睫毛上沁人的凉。
我在屋里看到的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出来,要往哪里走,看到地上落下的工具,就过来,拾掇起来。一边整顿,一边不知对谁说,“这老头目,整天丢三落四的。”又冲屋里说:“饭菜都凉了,还不洗洗手准备用饭?”在这样的一对老人面前,我忽然生了一种敬意,一种感慨。
我发动摩托车,往家走,老婆肯定等急了吧。路上,人们劳碌碌的,往家推草,整顿院子,急着往家赶。像极了雨前的蚂蚁,像蚂蚁那样慌乱和卑微。我忽然想起几千年前,衣袂飘飘的屈原在汨罗江边的嗟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