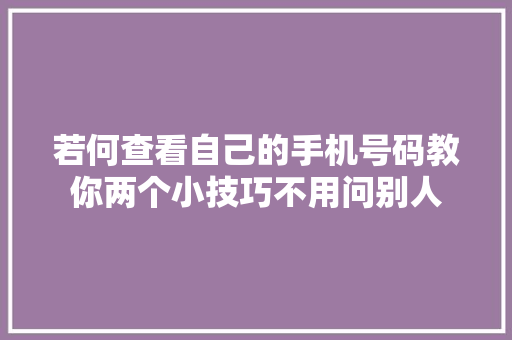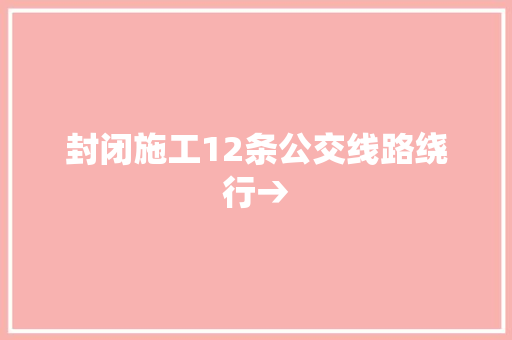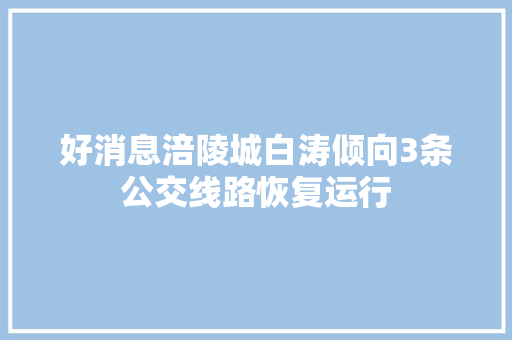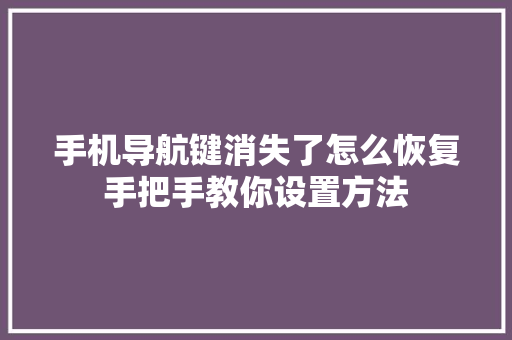我在16岁去青海之前一贯住在齐东路,每次回来探亲还是住在这里。1981年初调回青岛,又住进了齐东路的家里,直到1987年单位分了屋子才搬离齐东路。1996年母亲换房之后,才彻底和齐东路告别。算起来我们家在齐东路共住了40多年,我前后也在这里住了20年呢。
齐东路是老青岛一条范例的穿越在丘陵地形中的颇有洋味的道路。以出路径两旁在法国梧桐的的背后,是一座座各式洋楼,每个院的大门旁都配有车库(俗称汽车屋)。到我记事时,各院的小汽车已经都没有了,车库里也都住进了劳苦大众。但那时不少院还是大门紧闭,门上装有电铃。我写了博文《黄岛路影象》之后,有博友(我预测是住在莱芜二路的老同学)跟帖说,“那时走到齐东路上,常常恶作剧地去按人家大门上的电铃,等人家从楼高下来开门时,早愉快滴跑远了”。天真调皮之情跃然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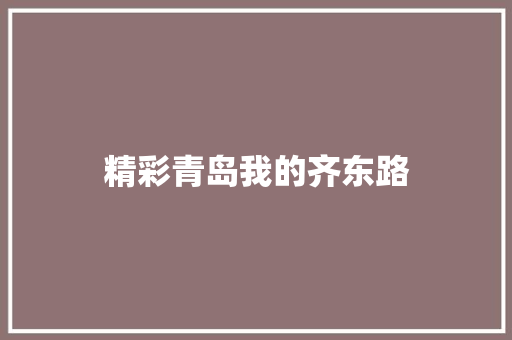
去年10月,博友杜帝发了一组有关齐东路的图片。我跟帖说“齐东路是我从小居住的地方。那里有我太多的影象,也有许多故事。小时候就知道这里有青岛的华尔街之称,住过许多名人和大亨。像小提琴教诲家董牧师,新龙源酒店曾是演员丛珊家的。”杜帝回答“你说的我确实不知,孤陋寡闻啊。大哥大概该当写点回顾散文,我们期待着”。
从此我彷佛领到了一个任务,平添了一个苦处。
我不是文史专家,更对齐东路的历史没有研究,只是在这里住的久了,道听途说地知道了些皮毛,真实性、准确性,都很难说。但是鉴于我对齐东路的感情,实在也是对过去光阴的怀念,还是想写写我所知道的齐东路——我的齐东路。
昨天开车外出时,看到景象挺好,便转道去了齐东路,用随身携带的佳能卡片机,拍了一组照片,开始动笔逐步记下有关齐东路的点点滴滴。不过要特殊声明的是,我写的大都是1966年去青海以前的齐东路,离现在快50年了,有些人和事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如果记的写的有误,恕我绝无恶意,还望敬请体谅,更欢迎批评指出。
高下图:齐东路的出发点,从龙山路北头右转开始,从旗子暗记山和伏龙山两山的山坳中,顺山势蜿蜒而上。
高下图:一贯上到顶。往右就上了旗子暗记山。齐东路则围着伏龙山的东坡,下坡向北。
上图:顺着这里一贯下到莱芜二路。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全体齐东路还是沙土路。好在那时汽车很少,只是骑自行车时不太方便。特殊我那时在上图这段路上学自行车时,由于下坡很长,沙子又滑,常常刹不住车,被摔得少皮没毛地。后来,街道上发动居民出动打石子,拉沙子,政府出了点钱给铺上了沥青,才有了现在这样子容貌。
高下图:到莱芜二路口,往斜右方,到登州路止。齐东路总长1000米旁边。
面前这条莱芜二路属市南区。从交通银行东侧往下,是丹东路(最早叫安东路),属于市北区。这里最故意思地是,每当城管来清理商贩时,市南城管来了,商贩就推着车子端起筐子迈到丹东路;市北城管来了,商贩就往南走两步,到了莱芜二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城管眼看着商贩就在眼皮底下,丝毫没有办法——你不能跨界司法。商贩在逗城管玩呢。
看到现在这里的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你大概不会想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到了入夜,我们小孩子都不敢一个人到这边的小铺买东西,由于那时路上险些没有行人。没成想,半个世纪之后变革竟如此之大。
齐东路公交车站原来就在上图工商银行门前。网上有人说,齐东路站竟然不在齐东路上。实在,这一段也是齐东路。但是由于莱芜二路隔断了齐东路,以是,在人们的意识中,后面这一段彷佛不是齐东路了。现在,齐东路由南向北是单行线,而过了莱芜二路,这一段成了反过来的单行线。一条齐东路,从中间生生地又一次被隔断了。
德国人盘踞青岛时,把市区分为青岛区和鲍岛区。青岛区是欧人区,开拓比较早。齐东路这一片不在青岛区,以是也迟迟没有开拓。到1928年,齐东路也只有6座洋楼。但是随后的发展,却让齐东路后来居上,成为原青岛区之外洋楼最集中最美的一条路。
齐东路之以是美,一个它是围着山转,起伏蜿蜒,并且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岔道——有通往山上的波螺油子,也有通往山下的石条台阶,使齐东路不单调。岂止是不单调,实在是意见意义盎然。二是那些样式互异,造型奇特的别墅洋楼。三还有曾经住在齐东路上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和故事。
齐东路上的紧张岔道有这么几条:
上图:从龙山路拐上来的第一个岔路。
这是一条很短的波螺油子路,通往旗子暗记山。这条岔路上的屋子的门牌号也是齐东路,记得是大路上编号的附加号码,如甲乙丙丁之类。
上图:路左面通往伏龙山的石阶路。
过去这里只是上山的一段很简陋的石阶,山上并没有像样的建筑。我们小的时候,上面只有贫苦百姓用石头盖的几间平房。现在,上面已经盖了不少楼房了。
上图:这是通往旗子暗记山公园的路口。左面是齐东路17号,老屋子已拆掉,现在这是新盖的。
旗子暗记山曾经是我们的乐园。上小学时,下课后我们齐东路上和旗子暗记山路的同学常常跑到这里,或者钻进德国人残留的堡垒里,或者自己动手用石头垒工事,和住在迎宾馆马号附近的学生打“游击”。双方常常背地里去把对方的工事捣毁。不过倒是从来没有大打脱手。
左边这个挂着乳业牌子的小屋,曾经是个小铺(小商店),从青海回来探亲时,常到这里买啤酒。青岛瓶装啤酒5毛8一瓶,退瓶子两毛,酒钱只有3毛8。不过和那时的收入比起来,也不便宜了。临回青海时,战友来信,说是想喝青岛啤酒了。我还在这里买了10瓶,托运了回去。说来真不合算,费半天事,还不足一顿喝的。
齐东路17号院里有我好几个同学。有一个叫赵百里的,他的哥哥叫赵万里,姐姐叫赵千里。几十年了,不知道去哪里了。同学聚会也一贯没找到他。
由于是旗子暗记山公园的入口,很多导游带着一车一车的旅游团过来。我正在拍照时,听见一位导游向大家先容说,这面是倪萍家住过的地方。倪萍比我们小好多,她出名后也没听说她小时候住在齐东路。我疑惑导游又在忽悠。回来查了一下,去年倪萍来青岛签售《姥姥语录》时,还真有她的一位女同学向先容,倪萍在39中上学时家住在齐东路。
高下图:17号阁下的这个大楼梯,叫旗子暗记山岔路支路,通往旗子暗记山路。分四级,共120蹬台阶。
有人说,倪萍曾经住不才图左边这个院里,那可能正门在齐东路,或者人们笼统地把这条路也称作齐东路了。
上图:这是齐东路中段通往旗子暗记山路的又一个大楼梯(人们都习气这样叫)。
下到底便是旗子暗记山路、西岳路和掖县路大沟。我家就和这个大楼梯正对着。顺着掖县路大沟直着走到头,便是我上幼儿园和小学的大学路小学。那时就连去上幼儿园也都是自己走,从来没有让家长接送过。当然那时街上没有那么多汽车,也没有像现在有那么多坏人和人贩子。再说,那时每家都有不少孩子,自己的还养不起呢,谁还出去拐孩子?
上小学和中学时到掖县路煤店买了煤,最打怵的便是这段大楼梯。弟兄两个抬着50斤或者100斤煤,上一段楼梯就得放下歇歇喘口气。
值得一提的是,仔细看会创造,好多照片上都有违章建筑的身影,把个原来俊秀的齐东路搞得满目疮痍。这都是从文革以来的战果。
高下图:这两个岔道都是上伏龙山的。
那时伏龙山还是个野山,有许多树,是孩子们撒欢的地方,我常常去抓蚂蚱和刀螂。伏龙山上印象最深的还有那个红砖的水塔。现在伏龙山已经开拓殆尽,只有屋子和人,没有山,没有树,更没有蚂蚱和刀螂了。
2006年5月,青岛市方案局公布了经市政府批准的182处第二批市级精良历史建筑。个中齐东路有17处洋楼入选,它们是:齐东路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10号、14号、15号、16号、18号、26号、28号、33号、39号。带符号的还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不明白为什么齐东路2号这样的建筑不是文保单位)。遗憾地是,只是公布了,并没有挂牌。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些建筑的历史和代价,也就谈不上保护了。
有些楼院不是很熟习。尤其是从1号到16号这一段,由于少有同学在这里住,知道得就更少了。可是这一段上的精良建筑就有12处,齐东路上全部的文保单位也都在这里。
上图:齐东路3号。
这个院有两个门。只记得不才面那个门里,住着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她之以是被记住,是由于她出门总是涂脂抹粉,描着眉,擦着口红。只要出门,必得路人侧目。在文革之前,已经搞了那么多运动了,所谓资产阶级生活办法早被批倒批臭了。她竟敢如此另类,我行我素,招摇过市,对她的这份胆量内心里也还真生出几分佩服呢。
后来听说,她的丈夫是国民党的军官,1949年随着老蒋去台湾了。文革起来的时候,家里来信提到齐东路破四旧抄家的情形,我首先就想到这会她肯定首当其冲倒大霉了。详细情形不得而知。
上图:齐东路4号。记得彷佛是个幼儿园?没有进去过。
上图:齐东路5号。
唯一的影象便是,当年青岛二中乒乓球队的队长赵大川住在这里。学生时期,他便是很令我们崇拜的了。后来他也由于出身不好,高考不中,先于我半年去了青海。我们成了兵团战友。
上图:齐东路5号甲。从记事起就没想着这个门打开过。
上图:齐东路7号。
前楼没去过。后院有一排很好的平房,姓戴的一家老少三口住在这里,我去玩过。这一排屋子都是他们家的,共有六七间屋子,家里还有许多传统古典家具。
高下图:大名鼎鼎的齐东路8号。
进门处原来是石阶。现在的住户为了进车方便改成了坡道,搞得不伦不类,把这幢著名建筑的风格毁坏了。在院里看到了一辆挂军牌的奥迪轿车,莫非现在的主人是军人了?
这是这一段,不,也是齐东路上最豪华壮不雅观的一处建筑了。
关于齐东路8号,我市著名的文史专家鲁海先生长西席专门考证过:
美国人詹姆斯1927年来青岛,任美孚火油公司青岛分公司经理,在齐东路8号建了住宅。1934年颐中烟草公司收购了大英烟草公司,聘他任青岛分公司经理。他的儿子詹姆斯·罗德里克1928年生在这里,以是自称是青岛人,并取了一个汉文名字“李洁明”。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役,他们百口返回美国,李洁明获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1989年李洁明任美国驻华大使,百口一起曾来访旧居。
栾宝德,曾任胶济铁路局副局长,四方机厂总工程师、厂长。他在詹姆斯一家回美国时买下了齐东路8号。后来日本人拟将淄川龙泉寺一组北魏石雕含两尊丈八石佛窃至日本,已经运到淄河店火车站了,栾宝德将它们用火车抢运到青岛,置于原四方公园内保存。这组艺术珍品现在市文博中央。
解放初期,青岛市成立“文联”,在这里办公。1955年青岛市文教局分为文化局、教诲局两个局,市文联迁旗子暗记山路,市文化局在齐东路8号办公。
以上转自鲁海师长西席的先容。
这里挂市文化局的牌子时,我曾经见过。到六十年代,栾家已经搬回了这里。楼上楼下住了好几家,都是栾家的人或亲戚。我八十年代回青后,栾家搬离了这里。开政协会时碰着栾家的半子(他以前和我住一个院),问起怎么搬家了。他见告我,8号住了好几户亲戚,厨房、卫生间都是公用,很未便利。再说,这幢屋子已经年久失落修,若要维修,用度巨大,承担不起。于是,便以住在这里的每户给一套屋子的代价转让了。此事若放在本日会让人以为不可思议,要知道按照现如今的价格来算,这幢楼最少要值上亿元,绝不是几套屋子的事。但当时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完备可以理解的。
栾宝德的儿子栾六训师长西席,改革开放后曾任过几届市政协委员,他当时彷佛是市政的总工程师。记得在政协会上,他提过有关海水利用、改进青岛市供水问题的提案。
有些屋子没有故事——该当说是我不理解它背后的故事,只能发张照片,立此存照了。也希望知道这些老屋子的历史,和个中的故事的专家和老街坊给予补充。
上图:齐东路10号。
上图:齐东路12号。
上图:齐东路9号。
这里是14岁成为天下最年轻的男子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的卜祥志的爷爷家,卜祥志的爸爸就出生和发展在这里。
上图:齐东路9号乙。
这里最早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或者六十年代初建的一个小楼,住的是部队的一位师级首长,他是《奇袭白虎团》中那位侦察英雄严伟才的原型。
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的女儿出嫁只花了9块钱,买了些糖分分就算结婚了。此事成为街道上宣扬节约办婚事的范例。去青海后,有些战友要结婚了,我提及了人家9块钱办婚事的故事。一位战友说,由于她家有钱,以是花9块钱结婚,在别人的眼里便是美德;如果没钱人家的孩子结婚花了9块钱,别人就会说是寒碜。我溘然明白,一样的事在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人们对它的评价是不一样的。
后来,这位老爷子去世了,部队为他的子女另找了屋子,让他们搬出。他们不愿搬,部队就在大门上贴了通知布告,责令限期搬出。途经的人都能看到,搞得这些子女很没有面子。终极搬出后,那个小楼被拆掉了,重新盖了这个楼,安置了更多的军队干部。
上图:齐东路13号。
院墙处的两个汽车屋,曾经住着我一个姓陈的同学一家。他们家有6个男孩,靠父亲推车卖馄饨坚持一家人的生存,后来不准市民做小买卖了,政府就安排这位父亲进了青岛钢厂做了钢铁工人。1960年困难期间,政策又有所松动,他们家又推出了馄饨车子。记得开张的第一天晚上,在齐东路的北头,老邮电局的对面,好多人都围在车子阁下看热闹——在当时那也算是新生事物。记得最清楚的是,煤球炉子上的大汤锅里还真的煮着一只鸡呢。
现在想想,当时的政策有多么荒诞,就这么个卖馄饨的事竟成了新闻,让我记住了这么久。
上图:齐东路15号。
这便是我在前面写到的,拆迁之后重新盖的大楼,和齐东路上原来的风貌极不折衷。
上图:齐东路14号。
上图:这处公安的屋子原来是14号的汽车屋,后来改建成了二层。右边的楼房也是后来新建的。
曾被誉为当代散文四大家之一的刘白羽,先后四次游览青岛,留下好几篇赞颂青岛的散文。他是这样描写齐东路的:
“伏龙山、旗子暗记山间的一条街道,有着弯曲上升的深巷伸向山巅,路左边是向下倾斜的陡坡,窄窄的小巷带着一磴磴石阶波折而下,引向深谷。望着那一道道小巷摇荡着各式各样的楼影、树影、花影、人影,在烟雨的迷离朦胧中,这山城是何等的美呵!
我一任雨雾淋湿了,只凝望着想:这多像重庆市!
这多像鼓浪屿!
……”
刘白羽是从齐东路的北头往上走的,若按门牌号码算,他是倒着游览的。以是他说“路左面是向下倾斜的陡坡”。
在17号之前,齐东路是在旗子暗记山和伏龙山的两山山坳中蜿蜒而上的。从19号起,齐东路就背信号山而去,在伏龙山的半腰中延伸了。以是以下的齐东路,右面的院子进门都是下楼梯,屋子在坡下;也有的是进了院门平着走进去,直接便是二楼。左面的院子进门都是上楼梯,屋子在坡上方。
上图:齐东路19号。
这里现在是江苏路派出所。以前二楼三楼是街道办事处,楼下是派出所。
上图:齐东路21号。
这便是齐东路上老屋子的第四种情形,拆掉翻新的。翻新的屋子住着比老屋子舒畅,但是由于翻新隔断了历史,没有了秘闻,只是一栋屋子而已了。
最早这个院里楼上楼下各住一家,都是姓葛的,他们是亲戚。住在二楼的葛先生长西席是华新纱厂的一位经理,他的外甥苏丹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也因此知道这位同学和非洲的一个国家重名。一贯到四五年级,我们都是好朋友,也常常到他家玩。后来苏丹的姥姥去世了,他被在北京新华社事情的父母接走了。我们当时依依不舍。
此博发出后,有新浪网友留言:“华新纱厂好象有位葛厂长叫葛甚修(音),小时候常听我祖父提到。”我上网查了一下,对照葛慎修的经历,想起当年我同学苏丹的姥爷也是右派,并且老夫妇都是一口的河南话,可以确定,他便是葛慎修。有关葛慎修的先容如下:
葛慎修(1903~1976),曾用名葛省斋。河南范县人。葛慎修1935年7月于山东大学化学系毕业,被青岛华新纱厂常务董事周志俊聘为技师,合营周志俊筹建青岛华新纱厂印染分场。1936年华新纱厂受到日商在青岛的九大纱厂的包围,面临倒闭的危险,葛慎修通过市场调查,推出了售价高、本钱低的190阴丹士林布,取名“爱国蓝”,冲破了日商独霸市场的局势,赢得了消费者的欢迎,华新纱厂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在困境中求得了生存和发展。葛慎修由此得到周志俊的重用和提拔,1938年7月被周志俊聘为上海信孚印染厂厂长兼总工程师,1949(1945?——本博注)年7月为吸收青岛华新纱厂又被周志俊调回青岛任该厂一级副经理。1958年10月,葛慎修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道批驳,下放劳动三年。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后安排在印染分场化验室事情。
葛慎修1951年参加民主建国会,曾任青岛市民建副主委,市人委委员,市各界公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第一届人大代表,政协山东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委,青岛市工商联常委,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1975年12月退休,1976年12月病逝。1984年规复政治名誉。
现在他的儿子美籍华人葛彬堂在葛慎修的母校山东大学法学院设立了葛慎修助学基金,帮助山东籍的穷苦学生。
上图:齐东路21号甲。
这个院本来是先下楼梯,再从院里上二楼的。后来有人在这里开了饭店,就直接从二楼接到了街上,新开了这个门。现在可能又易主了,这个门就留下了。
上图:齐东路16号。
这里最早是傅炳昭的家。傅炳昭出生于1865年,山东黄县人。德国盘踞期间来青岛,他是最早一批闯青岛的黄县人中的大哥大。他凭着自学的一点德语,开设祥泰号杂货商店,专门为德国洋行采购洋酒、罐头、食品及五金器材。他长于也敢于投资,有钱就买土地、盖屋子,短短几年韶光,变身岛城房产大亨。1910年,他当选青岛总商会首任会长,成为公认的华商领袖。
1924年5月,胶澳督办高恩洪发起筹办私立青岛大学,傅炳昭和刘子山、宋雨亭等著名贩子出资参与成为校董。其余值得一提的是,本日太平路的天后宫得以存在,也和傅炳昭等人有关系。当时德国人为了威廉路(国民政府收回青岛后改为太平路)的培植,意欲将天后宫迁走。傅炳昭和当时的商界士绅胡存约等出面力争,迫使德国人放弃了动迁天后宫的动机。
看来当年的盘踞者还算是能听得进民间的不同见地。从本日的太平路、广西路的走向可以看出,当年是就付了天后宫和老衙门(今公民会堂处)的存在的。此事假如放在本日,早就大铲车一挥,给夷为平地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傅炳昭的后人还住在齐东路的老宅里。
上图:齐东路18号。
这个院里没有故事。只是左边的这个汽车屋里曾经住过一位拉洋车的师傅。上世纪六十年代,大概这是青岛唯一的一辆洋车了。
洋车在别的地方叫黄包车,两个大轮子,两根很长的拉柄。记得最清楚的是,这辆车的两个大轮子的胎都已经磨破了,由于这样的轮胎早就不生产了,只好用赤色的自行车内胎胶皮缠在轮子上。那时基本没有人雇佣人力洋车了,他紧张是为齐东路上的几位成本家老人做事,定期轮流拉着他们去天德塘浴池沐浴,或者去医院、走亲戚。他彷佛一贯就一个人过,仅靠这几位主顾的收入就足可以坚持生活了。
上图:齐东路20号。
这是座日式楼房。我有好几个同学住在这个院里,记得姓朱的一位女同学的家里还铺有榻榻米,宽大的壁橱里能睡得下一个人。后来她的姐姐也去了青海,和我在一个连里。这里还有一位姓李的女同学,她是我们的少先队中队长。
这个院里还有一位名字叫王长江的小学同学。他有两个姐姐,母亲去世了,父亲为他们娶了继母。王长江很聪明,也很好学。大约是1960年,我们上小学四年级,那时中国的经济涌现了问题,开始动员城里的人还乡。王长江百口被动员回曲阜屯子老家。那时我们关系很好,都为他难过。记得王长江很倔强地和我说,“没有关系,曲阜是孔子的故里,有很好的文化秘闻,我在那里一样可以好好学习”。在那种情形下能说出这样的话,让我很佩服。这么多年了,我对这番话一贯影象犹新。王长江走后,我还和他通过信,往后就断了联系。
前两年王长江来黄岛看望他姐姐,顺便去看望了当年的小学老师,和大家联系上了。王长江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规复高考后考上了曲阜师范学院,毕业后当老师。前几年,上海的一个区全国招聘中学老师,他去应聘,当选中。现在百口在上海定居了。我们都为他高兴。还是应了那句话:是金子总会发光。
上图:矿泉水这个汽车屋里,原来住着我一位姓周的同学,他父亲在这里开了一个裁缝铺。
上图:齐东路25号。
这个院里也住了好几位同学。有一位姓殷的女同学,还有一位姓于的男同学。
上图:齐东路27号。
青岛著名的小提琴教诲家董吉亭曾住在这里。董吉亭在基督教会里做过牧师,以是人们那时都称呼他为董牧师。不过他也因此在文革中没少遭了罪,并被撵到惨淡湿润的地下室里住。。
自解放后,董吉亭就没有公职,以教授小提琴糊口,兼教钢琴、大提琴。1977年应邀赴曲阜师范学院任教。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岛凡是学小提琴的末了险些没有不拜师董牧师的。那时所有中国国家级的乐团中险些都有他学生。著名指挥家吴灵芬、李传韵的父亲李厚义,也都曾师从于董吉亭。由于他的学生水平高,中心音乐学院还专门在青岛设了考点。1975年往后董吉亭不再招收学生,唯一破例的是1977年前后又教了吕思清一年。他自己的三个孩子也都在专业乐团。
我在去青海之前,在齐东路上常常能见到董牧师。他那时有五十多岁,常常穿一件中式罩褂,干净利索,很有风姿。
1979年5月,董吉亭于北京病逝。
原想找找齐东路的老人,多理解点齐东路老屋子的历史,让后面的博文更充足和深厚些。结果,找了几个人,都不尽如人意。真正理解齐东路历史的老人险些找不到了,60岁旁边的人,对自己院的过去还能说上一二,对全体齐东路理解得不多。因此,也让我更强烈地感想熏染到,真有必要抓紧韶光去抢救历史了。不然再今后,连“听说”过的人也没有了。
上图:齐东路22号。
2010年5月29号,青岛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在网上有以下的记录:本日,有四位日本客人到齐东路22号,个中一位65岁日本妇女,出生在齐东路22号,6岁时(1944年)离开青岛。这位日本妇女清楚地记得她的出生证上写着齐东路22号,可是当到了22号时,她好象记不准了,由于还有个22号乙(该当是22号甲,22号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建的——博主注)。她见告我有个姓陈的司机是个中国人,住在楼下。她还记得她的邻居是中国人,还送给她家点心吃。她想确认一下到底是哪个屋子。
上图:齐东路22号甲。
这便是妹妹在“我的齐东路·七——妹妹眼中的齐东路”中写的她们小时候曾经的百草园,她的那位同学姓汤,她爷爷是位很慈祥、很开明的老人。我有两个同学住在这里,一位男同学姓苑,一位女同学姓周。
上图:齐东路22号乙。
这里原是块空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给印尼回来的华侨盖了一座小楼,便是后来的市外办主任赵雪芳的家。后来此房易主,又拆掉重盖了现在这个楼。
上图:右边这个院是齐东路24号。后面的大楼是伏龙山上盖的屋子。
这个院里有位多年来的新闻人物,端木丽华。她是南京人,上世纪40年代末随丈夫来到青岛,就住进了这个院。端木丽华没有孩子,上世纪五十年代她是齐东路街道的居委会主任,她很尽心地为居民做事。我很小就记得端木大姨是个前辈人物,多次受表彰,还上过报。她老了之后,仍旧时时时地上报纸、上电视,不过那都是表彰她的邻居左老太和她的女儿曲艳芝的。
自1995年端木丽华的丈夫去世后,左老太就主动承担起照顾她的任务。2001年左老太生病临终前,请托女儿曲艳芝一定要像对待亲妈一样照顾好这位老邻居。曲艳芝遵照母亲的嘱托,十多年来全面承担了照顾端木丽华的任务,亲如一家。在邻居两代人的照料下,端木丽华生活得很幸福,如今已经92岁了,精神、身体都很好。
佳世客的中方经理尚慧杰从小也住在这个院里。
上图:齐东路29号。
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盖的市委果宿舍。这个院印象最深的是后来的居委会主任姜秀珍大姨,她是随丈夫于1949年从胶东解放区进城的。她是个放脚(包过脚又放开了),每天奔波在各个楼院之中。她大概干了一二十年的主任。他的丈夫王大爷原是市委交际处的科长,他最骄傲的便是1956年毛泽东来青岛的时候,他在迎宾馆卖力接待事情。他上世纪六十年代离休后,也参加了街道事情。他们夫妇都很受居民尊敬。
脚下的泊油路,便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夫妇发动居民参与铺就的。
上图:齐东路31号。
这里原是私营的道济医院,院长彷佛叫孙乾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还是叫道济医院,后来私营医院被取消了,这里成了市南区医院齐东路诊所,我们都称其为“小医院”。这个小医院给附近的居民供应了很大的方便。后来落实政策时,这个楼归还了原来的业主,后又出售。新主人把老楼拆掉重修了现在这个楼。这是近几年的事了。
上图:齐东路33号。
这个院也有我的好几个同学。不过这个楼是不是重新翻盖了?我印象原来彷佛不是这个样子。
上图:齐东路35号。
这个院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新盖的,是市立医院的宿舍。记得我小时候一天晚上肚子疼得厉害,父亲就到这个院请一位刘大夫来家里给我看病。
这个院还有我的一位小学同学林莉,后来和我一起去了青海,我们曾经在一个连。我们都回城后,她和丈夫(济南知青)留在了格尔木。1997年我第一次重返格尔木时去找过她,她那时已经是格尔木市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她的丈夫是格尔木市水利局局长。现在她退休后,随丈夫回济南了。
这是关于齐东路楼院先容的末了一段。
上图:齐东路30号。
上图:进了30号的大铁门,又分成了三个小院。
以前可不是这样,旁边两个门里是30号的院子,后来盖上了屋子,又分成了两个小院。
上图:30号老房东家的陈氏姐弟先容了这栋老屋子的历史。
陈氏姐弟的父亲解放前大学毕业后先是当状师,后来开过面粉加工厂,公私合营后是莱芜二路粮店的资方副经理。陈家是1949年买下这栋屋子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动员有多余房产的要捐献出来增援抗美援朝。那时说是动员,实在是在半动员半强制之下,陈家把三楼一层和汽车屋捐了出来,房管部门用来出租了。
实在和这栋俊秀的小楼比起来,楼前的这两棵高大的雪松改名贵。
1949年,陈家买下这个楼之后,又逢儿子过百岁,父亲的朋友来祝贺,送来了一雄一雌两棵有十几年树龄的德国雪松。根据青岛的景象特点,把雄树种在北面,雌树种在南面,便于雄树的花粉吹到雌树上。之后每到雌树结籽的时候,市园林部门就派人前来网络种子,回去造就栽种。可以说这两棵雪松是青岛雪松的老祖宗,也因此成为重点保护的工具。
30号和齐东路其他老院子一样,都是楼不大而院子很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好多单位都到齐东路来探求拆迁改造的工具。但便是由于这两棵雪松,阻挡住了好多将小楼拆掉重盖的企图。该当说,是这两棵大雪松救了这栋小楼的命。
上图:30号院里的雄性雪松。下图:雌树。
上图:原来的30号甲拆掉重盖了,门牌换成了30号乙。现在的30号甲是这些汽车屋子。过去汽车屋是不单独编号的。
上图:左面这个楼是齐东路30号乙。
这是原来的30号甲,也是一栋有很大院子的小楼。这栋小楼很有特色,全部是石头建的,类似城堡。抗美援朝时,房东把全体楼都捐献了。我有位初中女同学住在这个院里,她母亲姓臧,是合江路小学的西席,和著名墨客臧克家是亲戚。现在回忆起来以为不可思议的是,初中三年,每天上学放学,我们彷佛从来没有结随同行过。路上肯定相遇过,估计是由于十四五岁正是男女相见比较羞涩的年事吧。我这位同学比我晚一批去了青海,在工程团。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个院被改造了。改造方可不管你什么风貌,只想着多出些屋子,于是这些新改造的楼都没有院子了,院子多大楼就多大,也没有限高,于是就成了面前这个奶奶样。
由此也才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捐献风潮,把许多房东的产权给剥夺了,导致齐东路上险些每个老楼都是两种产权,有自留房,也有公有房。公有房都出租给了居民。至于汽车屋,由于都没有汽车了,以是全部都捐献出来了,为办事处所有。文革后落实政策时,只是把强占的自留房归还了。原来那些由于是“志愿捐献”的,不在“落实”之内了。
上图:这个楼也是新改造的,原来是青医附院的照顾护士职员家属楼。不过这个楼的大门不在齐东路,门牌号是伏龙路49号,以是不属于齐东路居委会。
上图:右面这个楼原来是齐东路32号,是张家的屋子。我和他家的老二是同学。那也是一栋很俊秀的小楼。
影象最深的是这个院里住着一家姓郭的,父子俩都是象棋爱好者。老父亲有60多岁了,每天在大门口摆着棋盘,和附近的居民下象棋,儿子下了班也来厮杀上几盘。我那时放了学总要蹲在这里一看便是一个两小时,回家后常常挨训。不过,几年下来我的棋艺大有转机。后来在兵团我还可以下盲棋呢。
说了半天,现在这个楼的大门开在了伏龙路上,是伏龙路56号。和齐东路没有关系了,齐东路32号这个门牌从此消逝了。一层的门头房是齐东路菜店。我妹夫一家就住在这个楼上。他们家是32号的老住户,拆迁后回迁的。
上图:我在拍照时,创造楼上浇花的这位正是我的小学同学,齐东路32号原来房东的儿子。我们自小学毕业后就没有联系了。
上图:齐东路51号。
这里住着好几位青医的专家。楼上住的刘家,夫妇都是青医的教授,兼任附属医院的科主任。女主人姓赵,是青医附院妇产科的主任。她过去曾经包过脚,后来又放开了。这在过去称为“解放脚”,可是周围人背后仍旧称其为“赵小脚”(前些日子在青岛大剧院上演的由张继刚导演、张千一作曲配器的山西大型说唱舞剧《解放》,便是反响的这个主题。没想到很多人将其理解成了1949年的解放,结果票卖得不好。过后让很多人懊悔不迭)。
高下图:齐东路51号甲和51号乙。51号甲彷佛也是住的部队的人。这两个院不很熟习,只能留张照片了。
上图:现在这里是51号丙。曾经是齐东路邮电所,过去买个邮票、发个信、打个电报电话都要到这里来。现在齐东路邮电局搬到了齐东路的北头,这里成了快餐店。
属于齐东路居委会的院落的先容到此就结束了。
关于剩下的那段齐东路,妹夫带我到辽阳路上的养老院,见到了84岁的张丽先生长西席,终于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上图:张丽先生长西席1981年到1988年做过齐东路居委会主任,他是堂邑路邮电局的离休老干部。
1971年,他换房住进了齐东路43号王子元家的屋子(王子元家被撵出后,住进了别的住户,张先生长西席和这位住户换了屋子)。1988年,为给王子元家落实政策,单位给张先生长西席家办理了屋子,搬走了。
张老给我们揭开了莱芜二路往登州路去的这段齐东路之谜。齐东路51号丙和53号之间隔着一条莱芜二路,到登州路口末了一个院是齐东路67号(过去没有这么多门牌,后来开了许多开店的门头房,也给挂上了门牌,一下子出来了这么多的号),这一段属于莱芜二路居委会;对面双号一段是市北区了,属于辽北路居委会。一条齐东路分属市南市北两个区,归三个居委会。
上图:莱芜二路把齐东路隔成了两段。
上图:这是莱芜二路口到登州路口的那段齐东路。工商银行那一壁属于市北区辽北路居委会,右面的院属于莱芜二路居委会。
有关齐东路的先容,终于写完了。此事在我脑筋里萦绕了好几年,现在轻松了。虽然有些院不熟习,只是或多或少地提到了一句两句。由于我不是写文史,是在写我影象中的齐东路,写我的齐东路,以是没有花费功夫去逐个院地采访、研究。有关齐东路更多的内容盼着有人来续写、补充。缺点、不准确之处,也希望得到示正。先把谢字留在这里了。
高下图:这些地段还保留了一点齐东路的影子。
一贯想写齐东路,实在是怀念齐东路的过去。那里承载着我儿童、少年的光阴和影象。这两年几次和小学同学见面,他们好多都是住在齐东路的。虽然几十年不见了,但是他们的一举一动依然透着当年齐东路上孩子的淡定和自持,特殊是女同学,至今还能隐约看出大家闺秀的影子。见到他们彷佛又回到了少年时期,真是悲喜交加。只管那时的生活很苦,就像现在有不少老年人喜好唱所谓红歌,实在他们未必便是喜好那些极左的、口号式的歌词,他们是喜好那个熟习的旋律,由此可以唤起他们对青春岁月的怀念。
我怀念的是过去的齐东路,或者说是文革之前的齐东路。并不仅仅由于那时年轻,而是由于现在的齐东路物不是人也非了。齐东路最大的遗产是老屋子。青岛俊秀的老屋子和路段还有很多,但都是在德占时欧人居住的青岛区。在中国人居住的鲍岛区,齐东路该当是最好的。这也是齐东路的历史代价所在。
齐东路还有一个更大的财富便是住在这里的人所形成的生活办法和文化风尚。齐东路上原来的居民中,旧的工商业者居多,险些每个院里都有一家两家;银行的职员也多,我有好几个同学家长都是在银行事情;还有当西席的多,我粗略地回忆了一下,能说出姓来的就将近20位,多数是小学老师,也有中学的、大学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市卫生局、市立医院、青医附院都或者征用老屋子,或者利用齐东路上的空地盖了宿舍,于是专家、教授、知识分子也多。这些人都是受过传统教诲的,身上透着一股民国范,其学识和教化不但表示在自身的言谈举止上,也表示在对子女的教诲上。齐东路上的大人见面都彬彬有礼,齐东路上孩子们都干干净净。这些构成了齐东路的主流风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齐东路上的住户中每次都有遭殃的。特殊到了文革破四旧的时候,齐东路成了重灾区。据同学和家里人说,当时抄家抄出的所谓四旧物品,都堆在各个院的大门口,点上火烧。那些日子,全体齐东路上都是烟雾环抱,乃至把柏油马路都烧化了。这些人家虽然被折腾到如此地步,他们住的屋子小了,财产没收了,存折冻结了,政治上更是没有地位了,但是几代人积淀下来的范儿还在,高雅还在,教化和教养还在。这便是齐东路的魅力所在。
齐东路上也有城市贫民,但是那个时期纵然是穷汉也崇尚那些有教养有教化的人,处处以他们为标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教诲自己的儿女。这就形成了齐东路向上的民风。这是非常难能名贵的。
我一位战友每年都要去西藏几次,和拉萨的上流社会人士有些打仗。一次他见告我,有位藏族人士对他说:“你们不要鄙视了我们藏族,我们是有贵族的民族。”此话给我很大的震荡。贵族并不是我们那种狭义的理解,也不是大款的同义词,更不代表奢华。贵族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贵族要有捐躯,要有担当,要有任务。贵族是一个民族崇尚的榜样。
一个社会不怕有不良风气和征象。怕得是人心不古,代价不雅观颠倒,崇尚无德,把欺骗忽悠当能力,把恶行当本事。实在只要人们崇尚善,崇尚文明,崇尚诚信,崇尚礼貌,这个社会就有希望。反之,就只会走向绝望,走向崩溃。
现在的齐东路上,大楼多了,住户多了,路边停的车也多了。但是老住户却少了。第一代老住户基本都不在了,第二代也都老了。还有一些有条件的都搬到东部新区了。齐东路沉沦腐化到和其他地方一样了,内在的精神没有了,原来的文明没有了,魂也就没有了。罩在齐东路上的历史光环也随之消逝了。
高下图:从这里还能看得出原来的那个齐东路吗?
往后,我会再去齐东路。去探求我的童年、少年,还有青年期间的一些影象碎片。
本文作者为网友“谈笑风不生”,原青岛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布告、社长谭泽老师,揭橥于2012年。青岛城市档案论坛公众号编辑发布,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