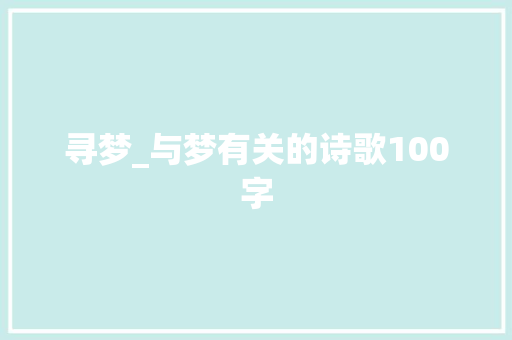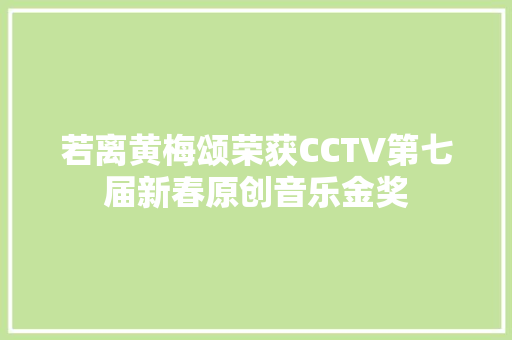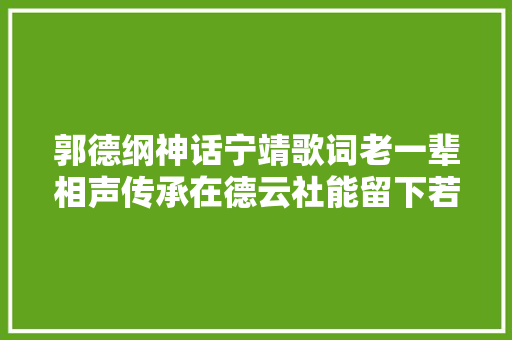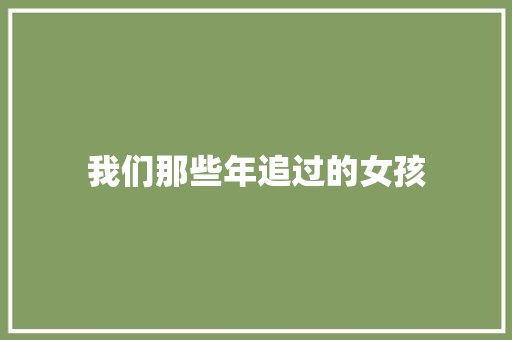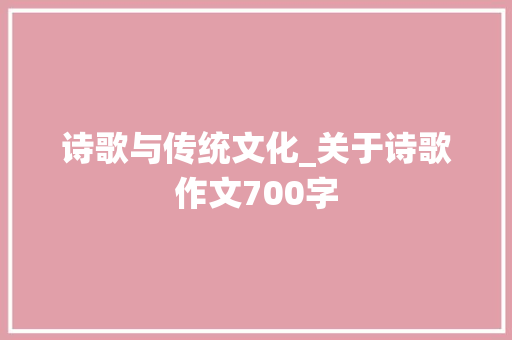贾浅浅的几首诗歌,经由网络曝光而产生了巨大的发酵,乃至各大官媒也参与了发文,不过发酵过后,涌现了两种不雅观点。
第一种不雅观点紧张是比较大众化的批评,一律认为屎尿屁的诗,不雅观感太差,韵律全无,与公认的当代诗歌大相径庭,根本不能成为诗,可能连打油诗都算不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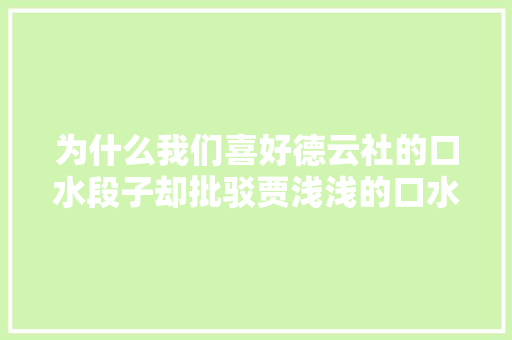
第二种不雅观点呢紧张是来源于报刊编辑,以及一些文学圈儿,出版社的各大护法们,认为大众以偏概全,彷佛读不懂浅浅的诗,就读不懂诗歌的美好与意境,彷佛新体诗这个“新”,便是越大略越好,越普通越对。
这也让我想起了这么一段相声,说是某地方言讲半夜起来上厕所非常大略,“谁”“我”“咋”“尿”就办理了所有对话,这可能便是上述第二种的妙用。
姑且不想谈这个争执,也毫无意义,普通人如果这么写,大家肯定笑笑便作罢,不会这么上纲上线的。贾浅浅之以是有这么大的热度,三个缘故原由:贾平凹的女儿;高校的副教授;在刊物揭橥过。
说回主题,为什么贾浅浅的诗,涌现屎尿屁这种词语,就让读者觉得到在侮辱诗歌,而德云社诸多角儿在利用屎尿屁这种包袱时,不雅观众就会如此原谅和喜好呢?
故意思的是,当德云社郭德纲师徒们使包袱时,批评他们的是貌似端正的各种大咖,乃至还有教授;而贾浅浅这种口水诗涌现时,批评他们的是步调同等的大众同胞。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人说,这有啥可比较的,相声怎么能跟诗歌比?我想说一种是艺术形式,一种是文学形式,不是说文艺不分家吗?
首先说每一种文艺作品的形式,终极都是用来为大众做事的。
大众对相声与诗歌的需求不同:对相声的需求来说,直不雅观目的是哈哈一笑,解暂时的忧闷,如果有更深刻的东西,也是一笑过后的些许感悟,愉悦快乐为主,教诲意义为辅;对诗歌的需求来说,第一感官是诗韵幽美,故意境与深度,从字里行间能感想熏染灵魂的碰撞,以及自己的感悟,其他次之。
屎尿屁这种包袱,让相声本身更贴合普通的生活,更加“雅俗共赏”,而且它不是流传作品,像快餐一样,须臾即逝,这场用了局不一定用。而诗句,是要印在书刊,要揭橥的,它须要广泛流传,直击民气,它是灵魂的产物,大众会把它放在心里一定位置,更长久一点的位置,而那些不是浮面取巧的屎尿屁,它们显得太丑陋。
很多新体墨客,也要保护诗的纯粹性,更要明白所谓的自由,是在诗的范围里自由,新体诗的发展不在于精简笔墨,如果纯挚从“精简”上去用力,就可能让新体诗的“自由”又掉入新的坑,有一定韵,有一定意境,打动人心该当才是一种准则。
我可以听郭德纲的相声,也可以读席慕容的诗;我可以听孔云龙版《扒马褂》里的于谦吐屎笑开了花,也可以读《三生石》的“那一世,你为清石,我为月牙儿”而伤怀思念…,我却不能读“手捏一块屎,像一个归来的王”来共情,如果与家人谈笑时大概我会提到孩子这样的趣事,分享我的快乐,但却不可能去对着每一个陌生人说,我怕陵犯了他们的感想熏染。
生活是万象的,它包括了所有的好与坏,原谅了世间万物;相声是生活的,它可以探求到你会快乐的那个点;而诗歌是神圣的,我须要它点中我的某个灵魂感想熏染,而不是给我抓痒,拿洋葱呛眼让我堕泪。
我须要相声带给我的快乐,更须要诗歌带给我的愉悦,这便是我的感想熏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