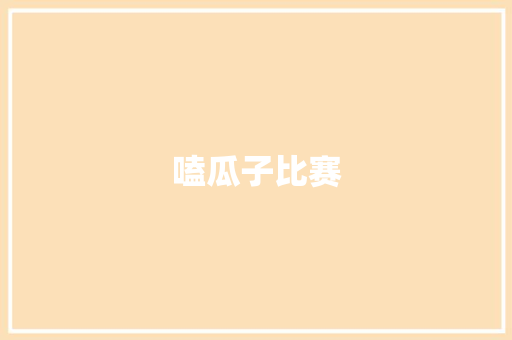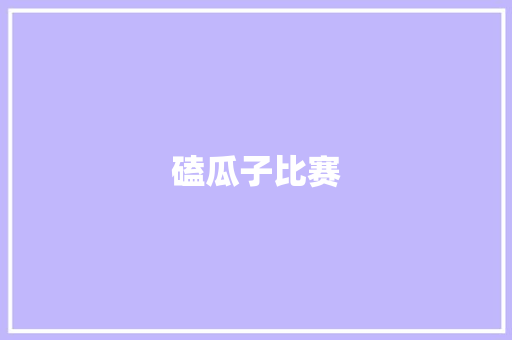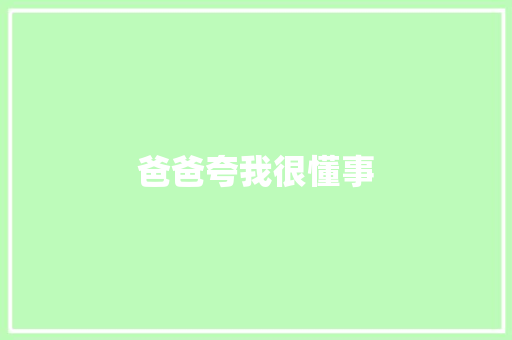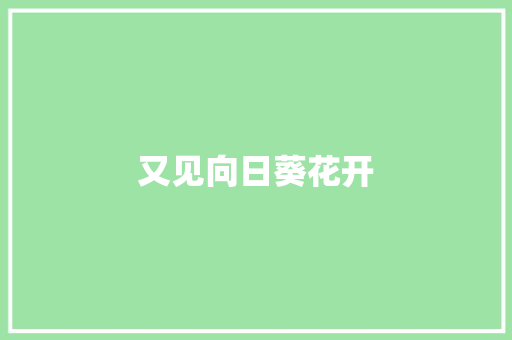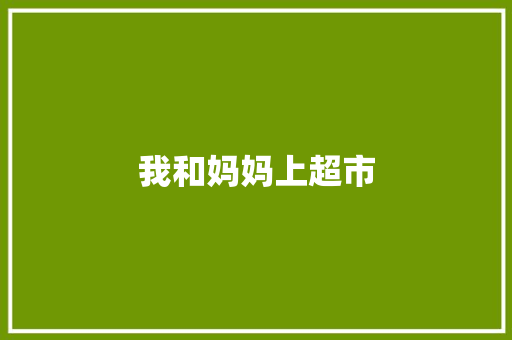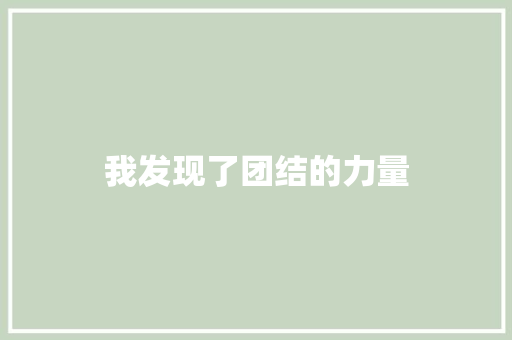嗑瓜子也是一种艺术。有的人在嗑瓜子的时候,喜好悄悄地,“咯”的一声脆响,瓜子壳就开了;再听见“呸”的一声,瓜子壳落进了垃圾桶;手起壳落,动作麻利娴熟,在这一“咯”一“呸”抑扬抑扬的音调中,瓜子就越来越少,瓜子壳越来越多。
嗑瓜子的姿态,男士可以很洒脱,女士可以很优雅,丰子恺曾这样写过嗑瓜子的男人:“那些闲散的少爷,一只手指间夹着一支喷鼻香烟,一只手握着瓜子,且吸且咬,且咬且吃,且吃且谈,且谈且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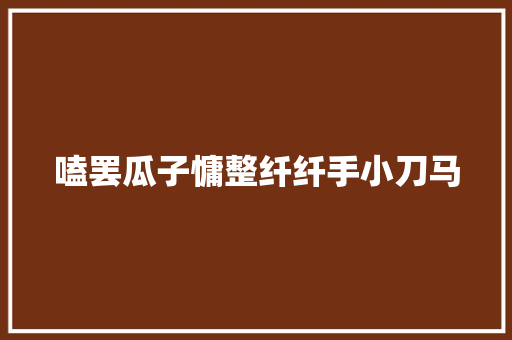
好一个闲散少爷,多惬意啊,嗑瓜子彷佛是某种清闲生活的象征,还有这嘴巴,无论若何忙乎也不会出错,吸、咬、吃、谈、笑,交叉进行,利用自若。他这样写嗑瓜子的女人:“她们用兰花似的手指摘住瓜子的圆端,把瓜子垂直地塞在门牙中间,用门牙去咬它的尖端,‘的,的’两响,两瓣壳分别拨开,咬住了瓜子肉的尖端而抽它出来。”瞧瞧,兰花指,逐步地往嘴里送瓜子,樱桃小嘴红唇,悠悠地往外吐瓜壳,把个女民气坎的闲适与姿态的优雅表现得淋漓尽致。
嗑瓜子实在也是一种心情。一种闲散,一种别致,一种慵
别鄙视嗑瓜子,那也是一门技能活儿,不是每个人都能把瓜子嗑得这么美,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把瓜子嗑得这么好。当磕苗条的葵花籽时,首先要将瓜籽放在两齿之间,用舌头轻轻托起,一点点向尾部磕去,发出悦耳的声音,然后用舌轻巧地一卷,仁儿便顺利滑进嘴,顿时满口溢喷鼻香。当然,如果嗑出一颗外的来,那也是非常恼火和憋屈的事情,一样平常都会伴随着“呸呸呸”的一直地倒口,才能吐干净。难怪有那句话:嗑瓜子嗑出一个臭虫来。是很倒人胃口的,也是大煞风景的。
葵花籽是大多数人的最爱,一个小小的“傻瓜瓜子”可以风靡全国,也可见它的魅力所在。
当然,也有的人喜好西瓜子。在磕西瓜子时,跟葵花籽是完备两样了,须要十分博识的技能,你若是急性子,是很难嗑好西瓜子的,很多时候只能是弄一个满口碎碎渣渣的,不得要领,皮碎仁段也是最常见的了。
实在,对付西瓜子,你既不急,也不可拖,要拿到十分的火候将那瓜子放在两齿之间,否则便是皮碎籽断的结果。接下来便是最关键的一步,这时要用两指轻轻夹住瓜籽,要做到不松不紧,快速地“嘎”的一夹,皮破仁出,只剩下洁白丰硕的瓜子仁了,舌头一卷就可以进入口腔里了。当然南瓜子也是如此这般,只是那瓜子更软,碎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下嘴的时候力度要轻,过程要偏慢一些,当然,也有人喜好用手剥南瓜子,自当是另一种吃的乐趣了。
在嗑瓜子的时候,还可以备一杯上好的绿茶,毛尖龙井雀舌都可以,边嗑边吃边喝。那种过程便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相传,嗑瓜子的习俗在明代已经盛行,清代民国愈演愈烈,晚清之前,“瓜子”紧张是西瓜子,晚清以来南瓜子开始盛行,民国期间葵花子又异军突起,终极确定了三足鼎立的局势。中国人精于饮食,喜食瓜子,可能源于节俭的理念,而后逐渐深入到饮食文化层面,成了一种习俗。
据讲求,嗑瓜子的习俗最早兴于北方,或许是由于北方冬季寒冷而漫长,农闲时大家整天呆在家中避寒,消磨韶光的紧张办法便是嗑瓜子谈天。据悉,吴越广为流传的《岁时歌》记载了“嗑瓜子”的习俗:“正月嗑瓜子,仲春放鹞子,三月种地下秧子,四月上坟烧锭子……”
康熙年间文昭的《紫幢轩诗集》中有诗《年夜大》:“侧侧春寒轻似水,红灯满院揺阶所,漏深车马各还家,通夜沿街卖瓜子。”“乾隆帝在新年之际,在园(圆明园)内设有买卖街,依照市井商肆形式,设有古玩店、估衣店、酒肆、茶楼等,乃至连携小篮卖瓜子的都有”。
在文学作品中更是不遑多让,《金瓶梅》《红楼梦》《孽海花》等明清小说中都有卖瓜子、嗑瓜子的情节。在古代,瓜子虽然不是什么奇异玩意,但也透着一份情意。“瓜仁儿本不是个希奇货,汗巾儿包裹了送与我亲哥。一个个都在我舌尖上过。礼轻人意重,好物不须多。多拜上我亲哥也,休要忘了我。”
瓜子的诱惑,很少有人能够抵挡,每到过年的时候,多买两斤瓜子,一定是为亲朋好友来串门的人准备的。当然,瓜子也很随意马虎上火。有所谓的推举说,我们每周摄入的坚果量为50到70克,只吃瓜子,每天均匀下来也就只能吃不超过两把。
如今各种新式品种频现,比如山核桃味、绿茶味、红枣味的瓜子,加糖又加盐,吃多了就更不好了。但纵然如此,有几个爱嗑瓜子的人能忍得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