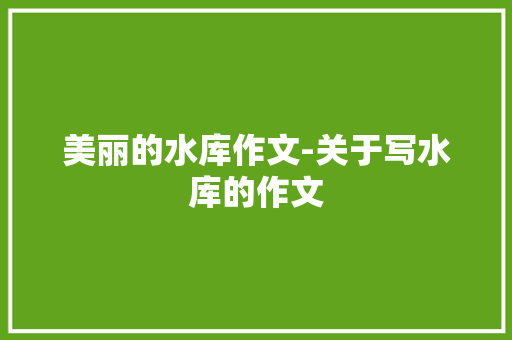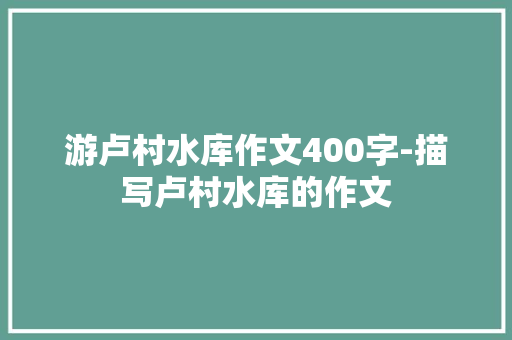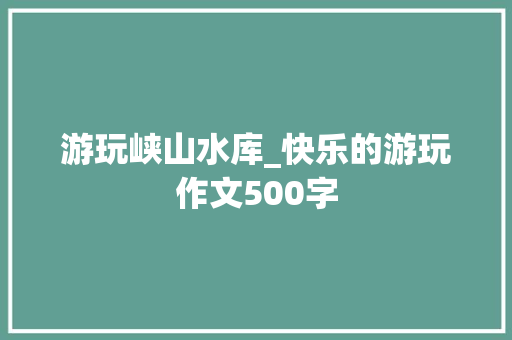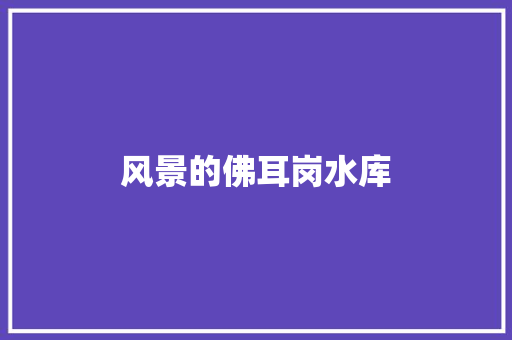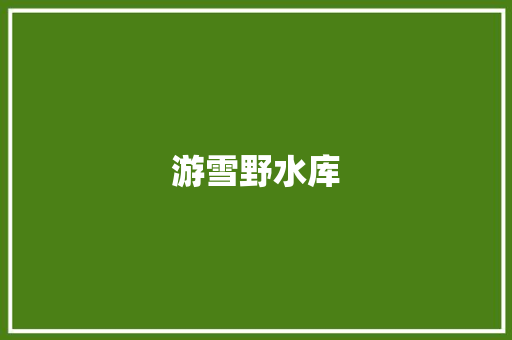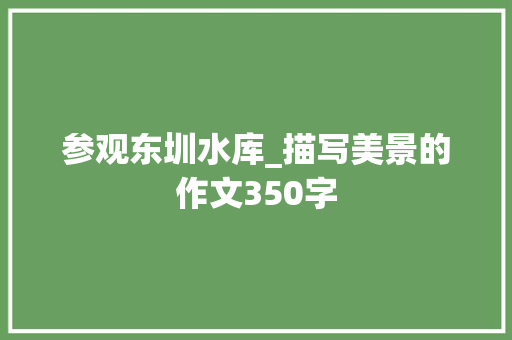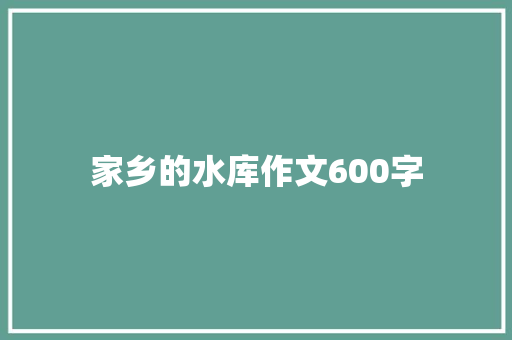(作者简介:马中珍,1965年下放铜山岭农场)
深秋,铜山岭农场20世纪六十年代建成的一座青年水库,时隔八年后, 要加宽加高重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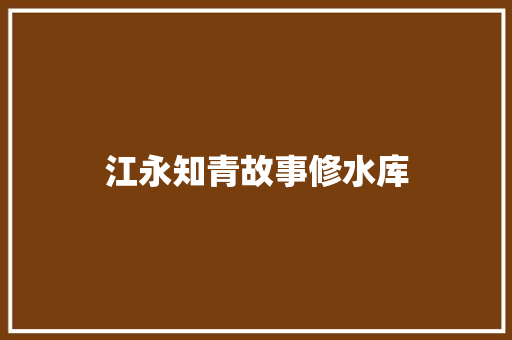
我扛着锄头、箢箕和铺盖,来到农场修水库的基地--山鹰队的牛栏边。这牛栏比较大,住得下两百来号人。上次修水库,这牛栏刚刚建成,没有关过牛。这次来住,不久前刚把牛迁走,打消牛粪后,地上、墙上用石灰消过毒,在牛栏两边地上平放着几根杉树,在树上铺上木板,再在木板上铺层稻草后便是睡觉的统铺了。其余,上一次来的是纯知青,而这次是由农场老职工与知青稠浊组成的修水库大军。走进牛栏,三分之一处立一道墙,将男女寝室分开。我把带来的草席往稻草上一铺,打开被盖,这便是我的新床了。
夜悄悄的,牛栏里弥漫着牛粪味,有人有节奏地打着呼噜,偶尔从隔壁传来女同胞细声的窃笑。触景生情,我难以入睡。上一次修水库的情景,总在我面前涌现:石油灯下,农场场长手拿两只由贫下中农精心编织的畚箕,当着两百多号知青的面年夜方冲动大方地说:“我们要以愚公移山的劲头改变铜山岭农场的面貌……”一席话,让我们激动不已;曾在这里,一句句《欧阳海之歌》的朗读声,让全体知青听得心潮澎湃;还是在这里,知青自编自演的演出唱《水库上的姑娘》让我们看得心花怒放……
水库工地上,一个人半天的任务是挑一百担土,大家挑土来回都起小跑。这任务按当地人的话来说架点势(努点力)可以早点收工;松点劲,任务还有点压头。我们知青经由多年的磨炼,也向老职工学会了调度自己的体力,不再是一味地蛮干了。想起来那次修水库真像在玩命,沉甸甸的担子,陡峭的坡路,对付嫩肩弱骨的我们真是莫大的磨练。肩膀肿了,脚走跛了,骨头要散架了,我们咬紧牙关坚持挑下去。伤病号被安排在牛栏屋安歇,可队长一离开,伤病号爬起来又奔向了水库工地...
收工吃过晚饭后,大家挤在地铺上听水库指挥长点名和支配事情。牛栏中间过道靠东的墙上挂着写满名字的考勤栏,这是沿袭上次修水库时的管理办法,目的是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人的身和心都在水库工地上。散会后,牌迷们打起了扑克“争上游”。这里对打输了牌的人有种特殊的惩罚,那便是要挑担百多斤的柴火站在一旁,等到打完一盘后,由输了的人换下他。
我们几位玩得好些的知青坐在一起评论辩论着自己的出息和命运。知青中的一些战友按政策招工或病退陆续离开了农场。天下上的事就有这样怪,只要大家在一起,条件再差也安于现状,一旦有人走了,这心可就安不下了。我们开着玩笑说:“现在有辆汽车来接知青回长沙,我崽不就走,什么都不要了。”说归说,笑归笑,私下里各自寻着道路、想着办法离开农场。我也正在办病退,只等长沙方面批下来了。
韶光一每天过去,水库也修上去了。冬天的雨下个一直,水库工地又正处在北风口子上,雨水在这里不是直着下,而是横着扫过水库坝顶。我们穿着蓑衣戴着笠帽,下半身还是被雨水飘湿了。路很滑,担子也格外重。景象很冷,可我的亵服却汗湿了。挑到五十五担时,安歇的哨子吹响了,恰好雨也不下了,只有北风仍在一个劲地吹。我裹紧蓑衣坐在扁担上,望着通向场部的逶迤小路。不远处的小路上,场部的通讯员正朝水库走来。
“马中珍!”农场通讯员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信一看,是长沙南区知青办公室让我办病退的证明。我欣喜若狂。几位知青围了过来,“祝贺你……长沙见。”他们握了握我的手,我的眼睛湿润了。
要走了,锄头和畚箕送给了老职工。牛栏的考勤栏上,我的名字已被抹去。我拎着被盖走到牛栏外,望着不远处的水库大坝。不禁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我默念着:再见了!用我们的血和汗垒起的青年水库。再见了!留下我们青春年华的铜山岭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