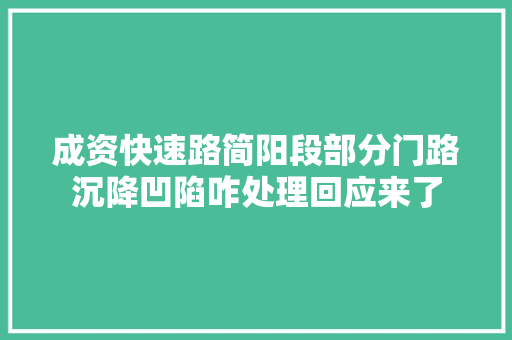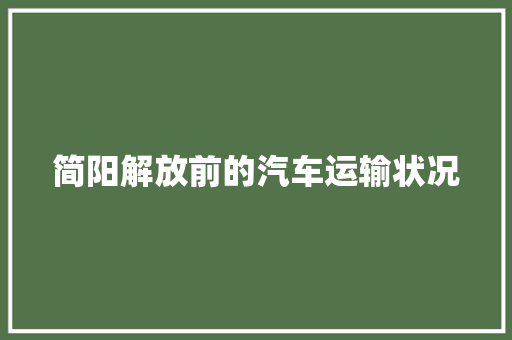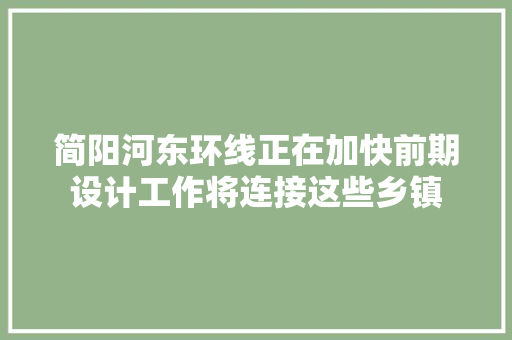刘中桥的为人与为文
傅 恒 林文询 何世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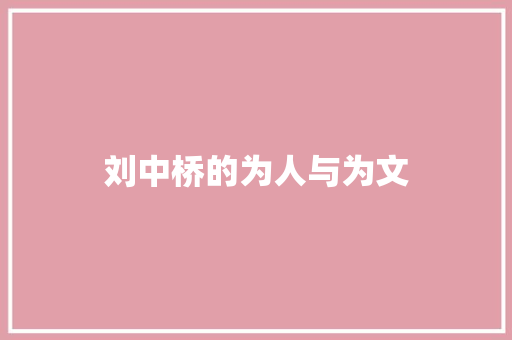
呼唤阳光
胃出血刚好,有朋友劝你练气功。方法很大略,清晨闭目静心而坐,意守丹田。丹田在这儿——朋友拍拍小肚子,反复打发,关键是意守丹田。就像你打发业余作者们。
刘中桥
选在星期日清晨开始,靠在床头想丹田。一米八的大块头让双人床也显娇小。你的肤色和体魄总让人不由自主想到“康健”这个词,然而,你很令人失落望,胃出血之前你就连续吃了两个月的中药粉,疗效毁于一旦是由于你主持了十天文学改稿班。文化馆联系的作者们只要隔上三五个月没有人在省刊揭橥作品,你就深感比胃痛更难熬痛苦,这便注定了中药粉在你身上威望扫地。眼下你身边又有一叠稿子,险些每一篇都附着言辞恳切的信,多数情形是信比稿子写得好。你便是从这样的稿子中创造一个又一个有苗头的人和一篇又一篇有苗头的习作。近几年,经你辅导修正、提笔润色、热心推举,简阳这地方已有二十多人次四十多篇小说在省市级以上刊物揭橥。这实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造诣,能达到这个高度的县级文化馆,在全首都找不出多少个来。许多人夸你长于发掘新人,夸你的阅读判断比一些职业编辑更准确。你由此成为业余作者们心目中的奇人,都关注着你那双具有非凡阅读力的眼力,却很少人把稳到你极其深奥深厚的心灵。
儿子在床前轻轻叫你,小鹅蛋脸上挂副小眼镜,其貌酷似你。
“爸爸,鸽子为啥总在太阳升起前叫?”
你果真听见咕咕声,那鸽子是文化馆宿舍楼后面的居民所养。儿子多次听你告诫作者不雅观察生活要细,把方法听会了。
你说:“它们、在呼唤、太阳。”还是很文学。
妻在一旁嗟叹,你忙眯上眼睛闭上嘴,意守丹田。
另一单元传出电子琴声,当然是音乐组的周中夫在弹,听他停停歇歇反复奏那几句,你明白他又在帮别人改作品。他年轻时在志愿军文工团拉过手风琴写过流畅动听的歌,转业到简阳文化馆便替别人在七个音符间填写了大半辈子,前几天已填了退休表,还不愿停下文化馆辅导干部的职责,哪怕是星期天清晨。你惊异过去居然没人想到搞个“金狮杯”、“金龙杯”之类的征文,写一写这些基层文化战线的……人梯。
你来文化馆前就在《散文》等报刊发过作品,那以前在车队修汽车,主修底盘上那个叫“中桥”的部位,后来你就把“刘中桥”作为笔名也作为儿子的大名。从修理汽车变为修理稿子,由常年摆弄钢铁换成在乱麻般的稿件中劳碌,发掘作者自己尚未知晓的才能,打消他们生理与文思上的障碍。你的眼镜后是双不很通亮却让人感到容量极深的眼睛,每隔不久,那双眼便在镜片后长长地闭一闭,端庄沉默中彷佛在酝酿某种聪慧,让打仗你的作者感想熏染到踏实继而转换出希望,顺理成章地就有人说你身上有一种迷人的性情色彩。
文化馆地处公园内,别人转公园是安歇,你却每次转都是与作者谈稿子。个子高大说话难免要弯腰,于是更显得像掏尽肺腑苦口婆心。你说话缺速率,慢条斯理中常让人想起虔诚兄长。三两次发言很难吹糠见米,那稿子便成了台上的乒乓,在作者与你之间来回反复,末了誊写下来早已分不清哪字哪句哪段是谁写的了。你来文化馆第一次辅导创作便有四篇小说被省、市刊物选中,渗入你笔墨最多的《小阁楼》竟被三家刊物同时看上。作者们笔耕多年从未变成过铅字,当场被喜悦压得脸发白手发颤,由于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件极不随意马虎的事。然而,熟习的人却创造最反常的是你,极少人见过你喜形于色,包括多年前你妻子十分难得地由屯子户口转进城,过多的生活艰辛已使你不敢轻易喜庆,可那天你一改平时的端庄谨慎,只管作品上署的全是别人的名字。
稿件与作者整天装满你的脑筋,你苦心研究了二十余年的自己的创作却荒漠了。正由于痴心于文学创作你才离开“油水”大的汽车队,调入人称“净水衙门”的文化馆——那时你以为文化馆是专门从事写作的,途经公园时,曾几次望着文化馆的大门入迷。
“笔会”留影/1983年于空分厂
刚来时还试图做到创作、辅导两兼顾,一段韶光后才明白,除非敷衍业余作者们!
到后来,一个个作者经你辅导在省刊揭橥处女作,你却只写了一些评价他们的笔墨。同时,你正在上学的女儿和儿子由于顾不上辅导,成绩降为中下也没察觉。你从小失落去父亲,母亲把你拖大,她退休前在做事行业事情,喜好谈天,多年来你一贯很把稳陪她摆龙门阵,如今竟由着老人每天默默拄动手杖独清闲公园里转,在石凳上坐。你强制自己与她聊几句,一开口便是谁写作进步快,谁还欠构思功底。你母亲听得似懂非懂,笑得也勉强。
窗外鸽子“咕咕”,一声接一声,这声音你太熟习。初中毕业你当过三年多民办西席,失落业后便在家自学,那时邻居也养有一群鸽,每天清晨你就在“咕咕”声中早读,常常为一句话一个观点苦闷多少天,“指示”你的惟有那清晨的鸽声。这辈子你都记得无人辅导的烦恼。
鸽声中断断续续插入琴声,你因势利导设想那琴声在丹田里奏鸣,越用力越清晰地想出老周一手握笔一手操琴的样子,连他花白的头佝偻的背也如在面前。你在老周家瞥见过他胸佩志愿军战功章的照片,那么漂亮那么精神。你惊叹,帮别人改改曲子,怎么就会把自己改得这般老态!
天下好师傅都是拿生命教徒弟。
那次有个陌生的小伙子来找你,看他欲言又止的神色,你鼓励他只管说。他说他的稿子多。你缓而沉的语调中饱含诚恳:“拿来嘛。”他又说:“我不是简阳的作者。”你说:“总是作者。”他欣喜若狂捧出一叠稿,像一匹砖,说他写了百多篇废品仍未去世心。你说:“好。”他说他的生活里不能没有文学。你说:“好。”他说坚信自己能为社会贡献崭新的精神粮食时,你的沉稳中已透出激动:“好!
”这位来自屯子的小伙子后来一贯在打听你为啥对业余作者那么激情亲切,你听说后淡然一笑:“由于我们这儿是文化馆。”
你吞一口津液,试着用意念送入丹田,仅仅专注了少焉,连你自己也不知送到什么部位去了。
都知道经你手引上省刊的作者和作品多,却少有人理解你每年的读稿量有多少,为更新和补充知识所耗的精力财力又有多少。那天你去新华书店买书途经北门桥,见一位你辅导多次的作者劈面走来,明明瞥见你了,他却伪装看河水把脸掉开。你记起了,他最近刚提干。那一刻你真有点百感交集的滋味。当年的县政府曾准备提拔你为修志办副主任,你推辞了。你曾去《四川文学》编辑部学习半年,无数个夜晚都目睹编辑们加班替作者看稿改稿。编辑中多数人曾风靡文坛,当上编辑后便将心血洒在了别人的稿子上。你问他们为啥不自己连续写,回答都差不多:几个人写,哪有几十几百人写好!
你想起了朝霞,燃尽自己,托出满天阳光。你把那种感想熏染写入散文《秋夜的灯光》,打动了一大片读者。那“灯光”,大概便是你放弃很多,包括放弃自己创作来推出更多新人的一大内在缘故原由。
以为安谧才发觉鸽子声稀少了,你微微松开眼,一抹金黄挂在对面墙上,太阳已升高了。本日是星期天,照例会有一二十个作者来文化馆茶园摆谈,许多构思许多作品便是这么开始的,比费钱费力地开会更有效果。你再忙都要设法参与,听到高兴时便会情不自禁发出缓而沉的长音:“哦——”
猛然想到又没故意守丹田,你不免暗自可笑。妻子无可奈何地叹口气。你拍拍身边那叠稿子对她说,下个月又有作者出作品。她说你胃出血刚好。你还在说作品:“会连续出的……”
(本文作者傅恒,籍贯简阳,一级作家;曾任内江市艺术馆馆长和内江市作协主席、沱江文艺杂志主编和青年作家杂志主编、成都邑作协主席、省作协党组副布告和省作协副主席、巴金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等职务。)
“文学茶话会”/1990年于简阳公民公园
“夕阳远巷,风雨故人”
中国当代文坛,听说有“京派”、“海派”之分,有没有“川派”?估计也有。星宿云树且不说,只感想熏染那气场就差异甚大。京都文坛气大声洪,好似神坛;海派文坛作古正经,喜好“造型”。而集中于天府之都的四川文坛,犹如别具一格的老茶馆,终年烟雾环抱,轻软闲适中,时时发出一两声语惊四座、声传京沪的叫嚣。当然立身严谨的也有,如一批端庄而存心的军旅作家;勤奋的也有,如由各县乡集镇“闯”进蓉城的写家枪手。至于我们成都本地的文人,包括那些身心皆已溶于这富贵温顺之乡的外来客,其总体特色,最好是用散漫而执著来概括。
对“执著”就不必多阐明了。这“散漫”固然有慵
但在这中间,我创造也有例外:此人被像我这种生性狂放忝列巴金文学院的“川军”老小子戏称为“教头”,从口头到心底都对他敬而不远,仿佛兄弟伙,文章事聊得,家常话说得,龙门阵摆得,乃至“坛子”也涮得、玩笑也开得……一言以蔽之,难得。
难得尤在“教头”也挂名评论界。都知道这搞评论的和搞创作的是一对死活冤家,关系相称奇妙。表面看,写作者对评论者大都是恭而敬之,以受宠为荣,这是当代文学的一大特色(古代乃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彷佛不是这样)。个中道理很大略,现今的文学已失落去过去的自然生存状态,变得急功近利暴躁至极,操作家者太多,文山书海爆市,要想“脱颖而出”,侥幸成名,还难免要靠“文外功夫”,恭请或贿请论家以至媒体参与炒作。这种人,尤其是庸常者及未成名者,表面上对论家恭敬如奉神灵,转过身去或有了些许小名声,每每会“含血喷人”,胡说八道。表面特殊谦卑的,更随意马虎“一阔脸就变”。可惜好些论家不明底里,不知背后文章,或者为谦卑像所迷醉,年夜方脱手,“奖掖”,“扶持”。“教头”既系界中人士,又有点人缘,也免不了要做些奖掖扶持之事,写些论说批评之文。然而不雅观其文章,听其发言,除努力于稚嫩中创造新意、于贫瘠地挖掘潜力以外,其他话都较有分寸,极为简单,很少摧残浪费蹂躏“表情”,信口开空话套话实际也是假话之河。至于批评(狭义),也原则而敦厚,多数是把阅读后那番热扑扑的感想熏染,融于蕴藉之中或音弦之外,三言两语,点到为止,听凭你信多少听多少,不信算白说,无脸面可伤,无架子可拆。总之是朋友交心,实实在在,明明白白,一如其沉沉实实的身影。对如此低调的批评人士,我总希望能与他多点摆谈互换,更希望他能为我写点批评笔墨,可惜至今未能如愿,也未曾因此就少了来往,反而是友情进步神速,几近于脱略形迹、推心置腹。
傅恒(左二)、林文询(左三)、何世平(右二)与简阳作者/2017年12月22日于贾家“大山邻居”田舍乐
说来说去,“教头”究竟是谁?实在貌不出众、名不惊世,此人是四川作协巴金文学院创作室的刘中桥师长西席。说他貌不出众,不单指像貌,于他还应加上“声貌”。他面相敦厚而染满沧桑,身材高大而略显佝偻,衣着简朴如力夫老农,一副老式眼镜又酷似三家村落校究,惟有深度镜片后那双浑圆大眼才多少显得有些厚重。这大块头往面前一站或是一坐,你面前就彷佛立着一块饱经风浪的岩石,蜀中灵山秀水间、深沟大谷中常见的那种粗糙石头。
“教头”还是一块沉默的石头,一样平常情形下绝不多言语,所谓笑口难开。而一旦开口,你便会感到是在与故人对坐,哪怕是说文学、叹世道,也犹如闲聊家常。他讲话语速缓慢,语意平实,既不张扬,也不华美,看似木讷,却是声沉沉、语沉沉,言皆有物,论皆有骨,一下子就能与遗存的“假大空”、盛行的“矫虚玄”差异开来。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论者,我当然乐意与他互换,掏心窝子长谈。
像“教头”这样的像貌、“声貌”,很难与那些滚滚不停,或者专踩痛脚尖酸刻薄的理论大师们联系在一起,只当他是一个市井闲人。我和朋友们明白,这“闲人”有学问,有教化,能与我们产生“夕阳远巷,风雨故人”般的朴拙交情。因此我至今不悔十多年前初次与他共会时说的一番话。那大约是1992年,一个盆地湿漉漉的夏天,我们在嘉州开笔会,照例要恭请外地大腕们来点缀增光,照例主理方也要首先向大腕们致敬,而我一开口便讲:参加这个会,我感到很荣幸,能与我们四川的刘中桥在一起,当面听他说文学。此言一出,室内溘然寂静,室外的雨滴滴嗒嗒,彷佛在不识趣的随声附合。我知道主人客人都有些意外而惊异。但接下来的十几年,岁月作证,能结识刘中桥这样一位朋友,确实让我受益不浅。
要说遗憾,自然也有一些。交往十几年,我只读过几篇他的文章,连关于巴金文学院创员的那部分,我都未读过。其缘故原由是我先有一个错觉,认为他只是“述而不著”的文坛职业读者。另一个错觉来自他写的《也说文学批评中的“叙事角”》:主见为文“紧张出于兴趣,无需积累卡片和考虑术语,明知话随风散,何必苦心经营。”这话正对上了我的胃口。大概他真把当今的文学批评看穿了,具有这种不雅观念和心态,能够相对超脱一些、镇静一些,处在乱哄哄的文坛上,无溺陷之苦,少违心之疚,想来这也是一种人生聪慧。
如今摆在面前的这本《刘中桥说文学》,点滴汇聚,三十多题。我不敢说它是一个深潭,让人以为碧沉沉深不见底,潜蛟于中,水浪于外。但我相信书中有多少可一读之文,可榷商之论,不管是直抒见地,还是点评作品,都留下了心血和空间。我也不敢说书中的文章,是什么金声玉振,悠然传韵。但我相信它一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不欺不狂、意在互换的实在话语。反而是我这篇纯粹出于兴趣,随笔涂抹的笔墨,既不像书序,更不像评介,那就让它如刘中桥所言,尽快“话随风散”吧。
(本文作者林文询,籍贯资中,文化学者,编审;曾任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省作协主席团委员等职务。)
流沙河师长西席与简阳作者/2011年6月18日于省文联宿舍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平生第一次为人作序,一呼即诺,居然不推辞不谦让,连电话那真个刘中桥也吃了一惊。惟有刘中桥,我才能如此随意。此平常人约请彼平常人,高卧西窗,静谈秋水,杯琴毕矣,丘壑过之。
我在文学界结识的第一位朋友便是刘中桥。那是1982年春,我第一次参加县上的笔会。三岔湖边,这位大个子的虔诚长兄是笔会的繁忙组织者,还要为一群热血喷涌的文学青年提笔改稿。他衡文的眼力和对文学的执著,给几家杂志社的编辑都留下了印象。当年秋日,他被《四川文学》编辑部调来学习业务,我至今认为是我们几位编辑缺点的厚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写作方向。此前,他已开始散文创作,走的是柳柳州、欧阳文忠公的路子,文风冲淡清华。此后他成了专为基层作者供应信息,加事情品,争取园地,用“评论”支撑他们起跳的“人梯”。在人生最成熟的时令,耗费掉了许多宝贵精力。这批作者早已分开文学军队,消逝在商海或官场,而刘中桥所得到的,不过是一点已经变得入眼生疏的笔墨。可能是为了纪念这段播种激情收成苦涩的岁月,他将已正式揭橥的那部分,编入这个评论集,列在“起跳与冲刺”栏目内。
“行人靠右”是交通的基本法规,用于文学评论,不过是表明作者的为文方向。刘中桥的文学评论,从题材上看,完备是他本职事情的一种延伸。这个评论集的重头栏目,便是他到四川作协从事组织事情后,对文学院“丛书”、文学院笔会、文学院长篇小说阶段性成果和部分创作员作品的评论辑录。这些文章,对列名文学院,在全国已有影响或在四川显得生动的作家,如阿来、裘山山、星城、傅恒、邓贤、施放、郭彦、何大草、何世平、易丹、乔瑜、李一清、贺享雍、刘继安、张建华、郁小萍、曹庶民、杨继仁、温靖邦、武志刚、佳云、牛俊才等数十人,或深或浅都涉及到了。这种立脚点有得有失落,让人感到有些惋惜。毕竟他读书多,影象强,目光敏锐,下笔灵巧,有条件放大范围,再多关注一些“洛阳纸贵”之书,用“讲经说法”来扩大影响,他舍此不为。我估计这内中隐情,除了生性过于散淡,恐怕还有不习气“仰视”的生理拖累。由于我也看过一两篇他偶尔“越界”的应命之作,持重拘谨,行文板结,隐去了挺有“意思”的一壁。而“这一壁”正是他文章的个性所在。
刘中桥的文学评论,多数是切点小,入题快,笔墨简短,却能捉住关键。他用一个中篇为例,这样概括裘山山小说的紧张特点:
以其合乎逻辑的事宜联系与过程的清晰完全性,险些把小说完备还给了故事。而这些故事都具备比较现实的生活内容,随意马虎让人产生认同感。在艺术处理上,她的作品不承担流派与主义的沉重“义务”,不演绎过于抽象的主题,不刻意错移情节的因果关系,看她的集子中,当然不可能找到那种在深刻性与主题之间形成严重断裂,但比较新潮的小说。她写的多数只是一种人们熟习,也值得相信的生活常态,即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喜怒哀乐,尴尬暧昧都来自生活本身,也都带有某种文化意蕴。阅读之后,能产生出回味咀嚼的延伸,遐想起一些比小说故事更多的问题。
这便是裘山山多年来,能以变革不大的题材范围,大体同等的写作路线,始终吸引着读者的奥秘。读者欣赏她的这些小说,她也信赖读者的欣赏眼力,不为风动,不赶时髦。
刘中桥书影
刘中桥的文学评论原谅丰富,归理明晰。他评论何大草小说集《衣冠似雪》时,先宕开一笔,讲近年的文坛,把从三皇五帝到慈禧光绪的历史,又乱哄哄的爆炒了一遍,读者以为新鲜。实在这些“宫廷秘闻,王者气候”,早已是“明日黄花”,它们的黯然气数、如梦兴衰,未必能久驻笔端而魅力不散。接下来才切入何大草两个“风格殊异”的中篇,作比较剖析(一个以荆轲刺秦的史实为背景,写“隐埋的人性之光”;一个取材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晚年离乱之悲,凭借想象对人物的“内界”进行关照与破解),解释它们的创新代价在于构造如一座立交桥,有许多层面、来路和去向,把历史“改写”成了耐人寻味的画面,并授予工具原来没有的新鲜感,与我们以往的阅读习气拉开了间隔。结尾处回应开篇,讲如何把握历史小说的分寸感:“小说是复苏的,也要带点儿神秘,才更靠近人生世相;但是,过于复苏或神秘,大概就不是小说而是讲义和符咒了。”全文不敷千字,分为三个层次,读起来无局促负重感,读后所得,也不限于只是对何大草个人作品的理解。
刘中桥的文学评论剀切坦直,又自然有度。他用邓贤作品为例,指出造成纪实长篇“轰动效应”的双重成分,既有作者亲历亲闻的切肤之痛,以其敏锐的心智,承担过当时的苦难,更有生活真实所具有的冲击力量:
一段雄奇悲壮的历史本身,就隐含着某种表现形式。当它经由作家之手而具备文学形态时,纵然不精雕细琢,仍有着它独特的魅力。这魅力系于内容切实,在阐述时能斗胆放言,一吐为快。由于画面既现成,只需再取好“角度”,评点核阅。
然后掉转笔锋,一矢中的,就当前层出不穷、“因文生事”的历史传记提醒读者:
敢于把小说装扮成纪实,无非是企图利用人们生理影象上的盲区,一旦框架上历史背景,十分迂腐的内容可以变得意味深长。假如拆除这道特定的背景,还原故事的本来面孔,阅读效果若何?是否会产生平淡无奇和受人愚弄的觉得?
总的说来,刘中桥阅读面比较宽,新知旧学都有一点,为文时能做到远取近譬,灵动生动,虽不敢说是有多少真知灼见,但他半数以上的文章,都带有这种简劲抒怀、耐读可赏的个性。时下或因分工过细,常见某些文学评论,词不称意,理过于情,作者彷佛不善于散文,某些散文又情浮词丽,穷于道理,难得这种笔下两者兼顾的“中和文风”。
集子里的其余两个栏目,一个是“关于期刊”,我作为前编辑,已无必要再评说;另一个是“诗文批评录”,附录的汪向东文章,对此已有触及,也无必要再多此一举。我还想说的是对刘中桥本人的印象,对附录的《呼唤阳光》一文补充几句。
想起刘中桥,就要想起四个字:古道热肠。印象最深的是我在《青年作家》主持事情那几年,省内某些地、市、州乃至某县举办文学笔会,刘中桥总要来电或来函举荐新人新作,代人恳邀或力劝我到会讲课选稿,而当时他的身份不过是省作协一借调编辑。每每《诗》云栋梁,《语》曰青蓝,爱才惜才之情溢于言表。每次知道我又带回几篇稿件,他总会眼睛一亮,半张着嘴仿佛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学,然后从背后再递一篇,故作惊异地问:“你眼睛很毒哦!
咋没看上这篇?”1989年春,自贡为两位青年作家举办作品研讨会,我因故推托,想不到他竟三次来电来函力劝我到会,言辞恳切地先容两位青年作家艰辛的创作经历。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推辞,这一去却欠妥心摔了个脾分裂,差点丧命。他为此懊悔数年,来信竟写道: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去世。刘中桥给人最初的印象是举止木讷,寡言少语,经由交往,又多出一些印象:为人的无伪不敷,处事的行义周仁。在文学园地里,他做了许多卖力不出名的事情。这二十多年间,文学的时尚就在身边,彷佛举步也可以遇上,但他总是在故意无意地绕道走,过着相对单调生僻的岁月,没有多少乐趣可言。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我们的主不雅观想象,并不即是刘中桥本人的觉得,这一杯苦茶,于刘中桥或许正是无尽的品味。他尽可能不赴冠盖云集之地,也就少了许多对号入座、点名起立的累赘;他不信鼓噪一时之论,也就不会招致惊诧莫名、晕头转向的烦恼;他对“待价而沽“的文学样品兴趣索然,自然也就不会去见庙烧喷鼻香、跪地磕头。在经历了多少人情冷暖后,反而可以持坦然的心境,闲看文坛花着花落,从“民视我视,民听我听”的平常生活中,寻求一种更为实在的抚慰。当前比较本色的诗人情怀,确实越来越少了,因此至少在像我这样的朋友圈子里,大家常戏称他为“教头”,是许多中青年作家书赖的老大哥。看着这本即将印刷、又注定没有市场的书稿,回顾起二十多年前三岔湖边我们初次见面时他为文学青年热心奔忙的身影,回顾起二十多年来刘中桥无偏无党的作人和不激不随的作文,我就会有一种宿命感,以为心中有话,而且早该说了。
(本文作者何世平,籍贯成都,文化学者,散文家;曾任青年作家杂志主编、成都音像社社长和成都邑作协主席、省作协副主席、峨影厂厂长、峨影集团党组布告和董事长等职务。)
(注:刘中桥,本名刘存品,男,1943年出生于四川简阳城关镇。简阳中学59级初中学历。职称文艺创作一级。前半生打工糊口,当过公办和民办学校的代课西席,考试测验过汽车修理;后半生以文学组织和文学创作辅导事情为业,先后在简阳县文化馆和四川省作协任职。支撑过新期间一批简阳家乡作者,为了在省级文学期刊上实现空想的 “第一次起跳”,指示过巴金文学院不少作家的创作。用儿子的名字做笔名,写有几十万字的作批驳介和文艺随笔见于省内外报刊,个中大部分篇目已辑入《行人靠右》和《刘中桥说文学》出版。简阳政协第七届(1987年—1989年)和第八届(1990年—1992年)常委兼文史委主任;简阳第十二届人大(1993—1998年)代表;1990年,简阳县委县府付与“简阳1990—1992年度首届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拔尖人才称号”;1992年,内江市委市府付与“1992—1995年度内江市学科带头人称号”;得到四川省委宣扬部首届(1994年)、二届(1999年)、三届(2003年)四川省文艺评论奖;1988年,得到四川郭沫若文学奖委员会颁发的“第二届四川文学奖精良组织事情者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