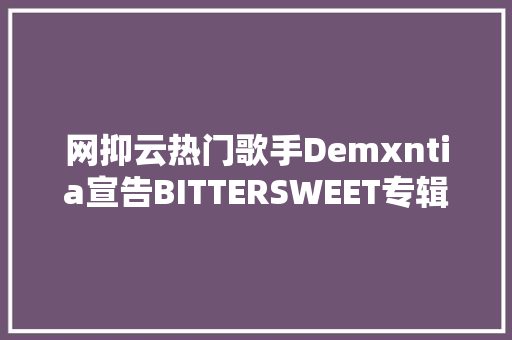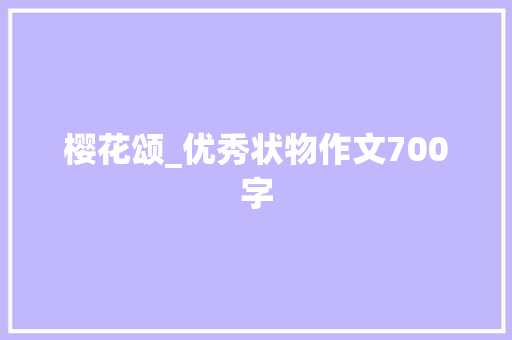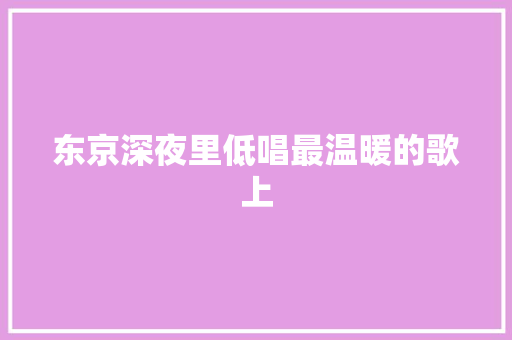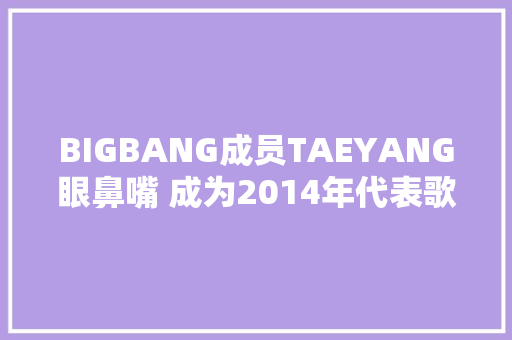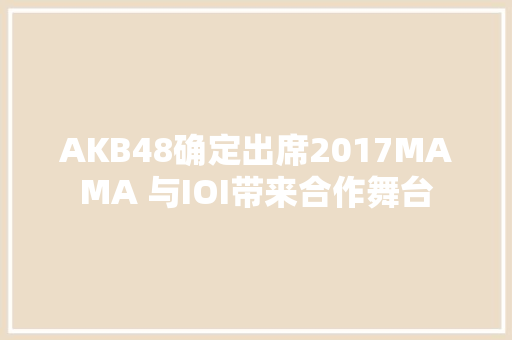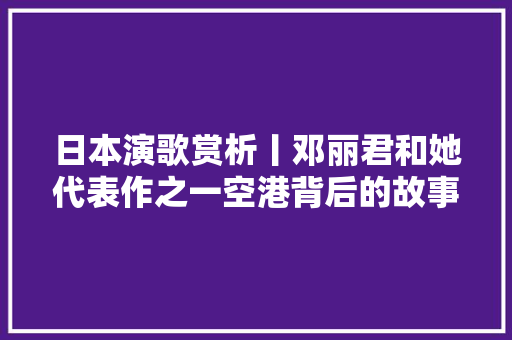《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商务印书馆2015年
一,日本侵略方针的改变1.七七事变:惩罚入侵1935年日本在华北事变中的方针是通过一系列事宜和冲突来蚕食华北地区,但遭遇到中国公民愈演愈烈的反日行动,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接管“停滞剿共,同等抗日”的主见。为此,日本军方在1937年发动的卢沟桥事变是对中国日益飞腾的抗日感情进行反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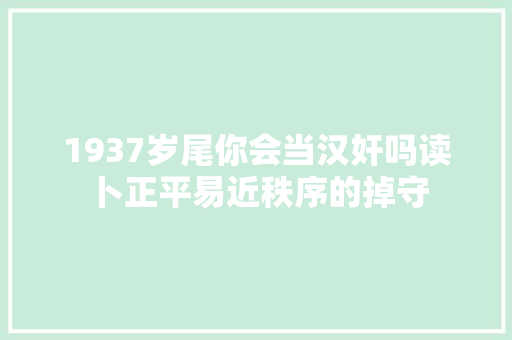
蒋介石国民政府在7月17日揭橥“庐山声明”,表示对日本挑衅的抗议,但考虑到“我们是弱国”,与日作战是不得已的末了选择。【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在1941年12月9日(珍珠港爆发后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末了关头,我们当然只有捐躯,只有抗战!
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搪塞末了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 ——1937年7月17日《庐山声明》
庐山声明揭橥后,一则希望将日军侵略方向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二来也为了引起国际社会的把稳,国民政府开始在上海地区集结军队备战。7月尾攻占京津地区后,日本政府和军方环绕着下一步辇儿为发生了不合,政府希望在知足其对华北地区的政治利益哀求后会谈结束战役,军方则迫切愿望将地区冲突扩大为全面侵华战役。日本军方强硬派见中国军队在上海集结,遂找到扩大战役的借口,8月13日爆发淞沪会战,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但三个月的战果仅仅是攻占上海,此时日本军方意识到中日战役是场持久的花费战。于是两手准备,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国民政府会谈停战,另一方面连续向西进攻国民政府都城南京。
11月尾陶德曼向国民政府转达了日本和谈条件,日本没有哀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有哀求承认满洲国,也没有哀求赔款,蒋介石认为日方的条件并非亡国条件,决定接管。但随着12月13日南京城的失守,日本取得了军事上决定性胜利,随即提出了更为苛刻的停战条件,包括“日满华互助”(即承认满洲国)和“向日本做必要的赔偿”。12月28日国民政府召开非正式会议,谈论日本的第二次和平条件,末了同等认为中国无法接管如此屈辱的条款。
3.近卫声明:永久征服1938年1月10日日本提出了第三次和平条件,条款更为苛刻,扼杀了中国接管和谈的统统可能。1月13日日本内阁会议达成了“不以国民政府为会谈对手”的一存问见,并于1月16日由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揭橥声明:
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旧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末了重新考虑的机会,一贯等到昭和13年。然而,国民政府不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公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全体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互助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度两国邦交,帮忙培植复兴的新中国。
声明中明确提出“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互助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既然抗战初期江南地区原有的国民政府机构或撤离或被摧毁,那么可以效仿九一八事变后的伪满洲国,扶植当地势力建立起听命于日本的新政府。终于,“战役由迫使中国政府让步的惩罚性入侵,转移到推翻国民政府的统治,代之以日本辅导下的政权”,日本侵略方针正式从军事侵略转为永久征服。
二,沦陷区居民与日本的互助1.互助的必要与无奈当日本军方也意识到中日战役的持久性后,日本政府开始动手规复日军盘踞区的正常生活秩序,以补充战役资源。因此日方须要一个相对安定的盘踞区,一个能汲取资源的计策后方,一个尊敬日军统治确当局。对战火后幸存的沦陷区中国居民而言,生活还要连续,须要一个能担保社会治安确当局,一个能供应城市生活正常供应的机构,一个能避免无端被日军杀害的保护力量,纵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承认日本监督下“政府”统治和抢夺的“合法性”。
既然在坚持社会正常秩序上日本与沦陷区居民的利益是同等的,那么二者之间就有互助的可能性,即“承认盘踞者权力的条件,受盘踞者监督,连续实行政府职能”。
“盘踞当局不可能仅仅依赖暴力来管理盘踞区。最残酷、最固执的征服者都须要地方上的引导和情报供应者。成功的盘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内部的背叛者、同情者以及野心家之间的共谋。”
——卜正民《秩序的沦陷》
2.互助的过程为了迅速规复盘踞区生活秩序,日本政府征召了一批熟习中国国情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职员,组建宣抚班,并在12月初迅速投入到江南各城镇以培植新政府。宣抚班成员聆听日本“特务部”的演讲,此行的任务是“拯救在英美奴役下的旧中国,扶携培植新中国”。
宣抚班到达盘踞区后,首先组织治安坚持会以规复地方正常社会秩序,之后鼓励地方头面人物出面建立地方自治会,经由半年旁边韶光的各方共谋,正式确当局公署机关开始自走运作。“汉奸”/互助者紧张来源于地方头面人物,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新政府培植过程,他们紧张承担的任务是发放良民证,帮忙坚持社会治安,清洁道路,规复经济生产和交通,卖力缴纳税收,为日军做事,参加“自治政府”等。
至1938年4月尾,宣抚班成员基本完成预设任务,即“规复”地方秩序,监控地方老百姓的活动,供应“沟通”的渠道,许可日军以最少的冲突来换取地方上的资源。此时城市政府基本在日本掌握之下,虽然屯子偏远地区生动着盗匪和抗日游击队。
三,重新评价抗战初期的“汉奸”/互助者当卜正民通过搜集各方资料从而展示出更全面的互助者历史图景时,该当暂时抛开道德评价,重新的角度来评价他们。
1.基于行为表现判断互助者除了承担上述与日本人互助的任务外,嘉定自治会会长孙芸苼考试测验吸引在上海租界避乱的家乡人投资,试图规复嘉定经济;镇江自治会会长郭志诚战前是大照电气公司经理,战后规复当地电气供应,同时组织镇江商会和同行公会发展经济;南京的吉米·王在日军,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沦陷区居民之间周旋,既在金陵女子学院招募妓女为日军做事,也曾难堪民救援粮与日军发生冲突。由此看来,互助者的行为带有明显的抵牾性,毕竟他们本身便是多方利益的凑集体,“既想为本地人匆匆进利益,又想为雇佣他们的盘踞当局提高经济效益”。
2.基于行为动机判断与日本人互助的动机各有不同,镇江的郭志诚认为规复城市电气供应是尽到自身职责;南京的吉米·王曾对同屋人说过,“与日本人互助是个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上海的苏锡文在战前是个被国民政府排挤的北洋期间官僚,担当上海市长对其而言是个重掌权力的好机会;一个前上海政府职员,由于生活困顿而申请加入上海市新政府;上海郊区基层社会的地方头面人物则利用“盘踞政府”供应的机会,与其他头面人物争夺权力。对他们而言,与日本人互助只是一种生存手段,而非生存目的。
供应食品是抵抗行为还是帮助盘踞者建立秩序?征募妓女是与日本人互助还是保护大多数妇女免遭日本兵的性陵犯?如果吉米·王的动机不是帮助或阻挡日本人,而是利用这些意想不到的机会来发财致富, 那将改变我们对他的评价吗? ——卜正民《秩序的沦陷》
3.基于行为结果判断互助者的行为结果在抵抗者眼里看来是通敌行为,帮忙日军稳定地方秩序,从而抽着力气连续攻占中国。但若是放宽历史的视界,互助者的行为难道不是在保护沦陷区公民的生命财产吗?而那些纵然是十足的抵抗行为,如1940年崇明岛上游击队引爆地雷炸毁满满一火车的日本兵,结果导致了附近村落落的一百多个村落民惨遭日本人的屠杀【类似事宜如百团大战导致日军对华北地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此时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个是可能增加普通民众对日军的仇恨而导向抵抗运动,另一个是可能增加对日军的畏惧而与残暴的盘踞政权互助。
无论互助的缘故原由多么繁芜,与大胆的抵抗者以及设想的畏缩的通敌者比较,现实里的互助在效果上更模棱两可,在运作中更困难。模棱两可不虞味着令人费解、无法阐明,困难也不虞味着合为难刁难盘踞当局毫无贡献。模棱两可和困难意味着我们不能根据我们强加的道德哀求来推断处于仓促条件下人们行动的缘故原由,亦不能仅仅根据参与者不能预测的结果来评估他们的行为。让历史行动阔别被民族主义感情束缚的假想,或者阔别使其老掉牙的道德预设,使事宜退回到无法预见的不愿定状态。盘踞之初,谁能知道“盘踞政府”是在日本失落败一天后倒台还是四年后崩溃?谁能知道它将被共产党政权所取代?谁能知道地方头面人物与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哪个派别的互助代价更高? ——卜正民《秩序的沦陷》
尾声正史便是如此的吊诡,一旦被盖棺定论后,黑白一定要分明,容不得墙头草。电影《鬼子来了》(2001)里的村落民们并不像《平原游击队》(1955)的村落民那般积极支持抗日奇迹,与日本盘踞军的日常交往中并未感知到身在沦陷区。因此,普通人在抗战时最好的选择是如崇明岛上的李鹤庐那般,“只管他同情战役期间处于地下活动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但他和他的家人并没有卷入个中,这可能是有家室但又短缺手段逃向内地的人的唯一选择。他把这看作是忍受沦陷期间的生活但不屈服通敌者的最好选择”。
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1997)里呼吁“勿忘历史,否则便是二次屠杀”,卜正民则更为专业地提出,“我们既不能接管在历史真实面前调油加醋,也不能对已发生的历史事实熟视无睹。我们的任务是透过这些人为设置的道德框框,核阅其背后的政治事实,来理解实际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在《秩序的沦陷》中的历史图景虽然冲破了汉奸——英雄的模式,但吹去了历史迷雾,让我们看到了战乱史中被大动荡所卷起的个人,而我们对那些互助者的评价也该做出调度,黑白之间尚存灰色地带。
电影《鬼子来了》截图
至于《鬼子来了》这一幕,很可能是真实的,虽然现在看来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