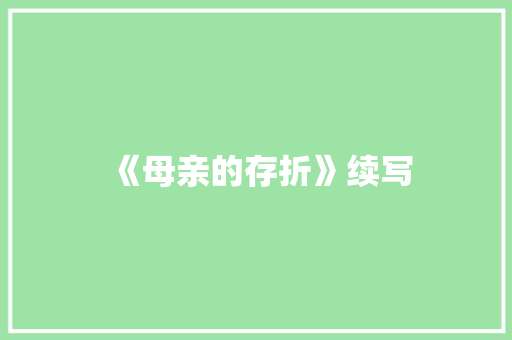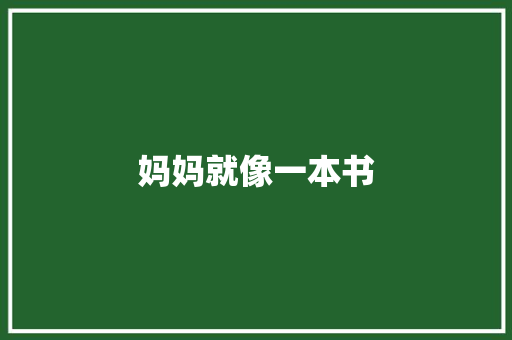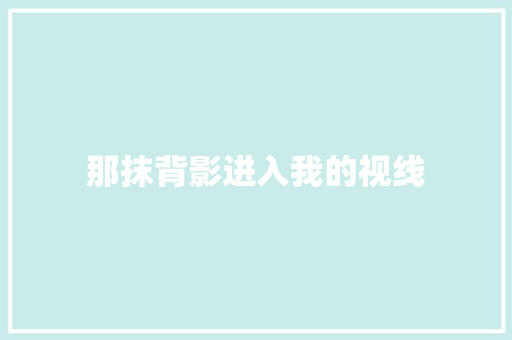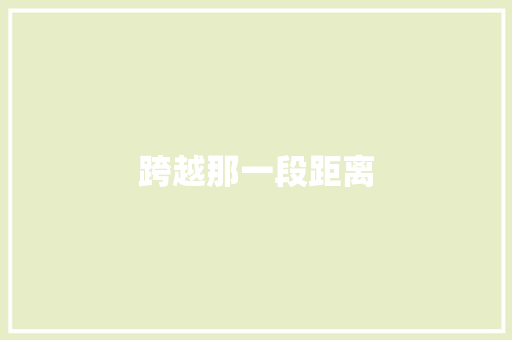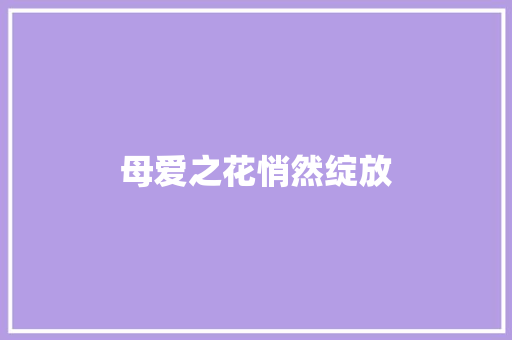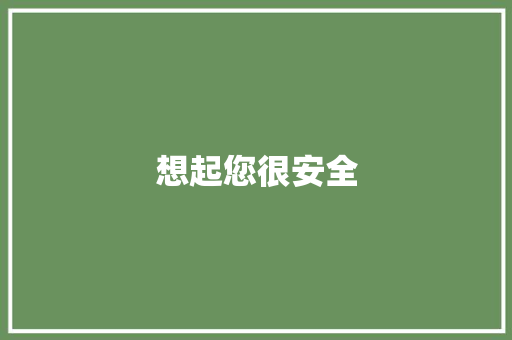视频加载中...
你陪我终年夜,我陪你变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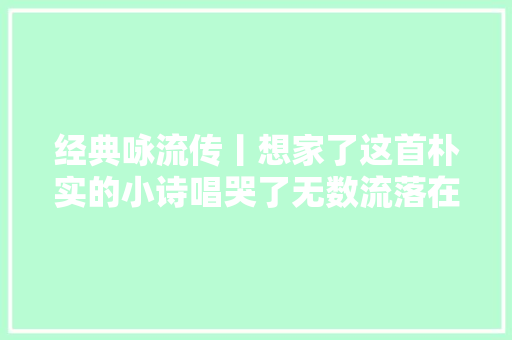
听完这首歌顿时泪目
有亲人的地方便是家
岁暮到家
清·蒋士铨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
寒衣针线密,家书墨痕新。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
低回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报喜不报忧
是游子共同的默契
每当面对母亲充满关怀的讯问:
“在表面是不是过得很辛劳?”
本就无法陪伴家人的子女
心中更是愧疚不已
不忍向母亲诉说羁旅流落的风尘
实在,这样动人的亲情
早已在两百多年前
被一名游子写进了诗里
乾嘉期间
有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
少与汪轫、杨垕、赵由仪
并称“江西四才子”
诗与袁枚、赵翼合称“江右三大家”
戏曲亦为清代大家
他便是著名文学家、戏曲家蒋士铨
而他的这番造诣
离不开生命中一位特殊的老师——
母亲的教诲和熏陶
蒋士铨从前家境贫寒
但无论日子过得多么清苦
母亲仍不忘严格教导儿子
辅导儿子成才
在他4岁时,母亲“断竹为字”
待他记住一个字后又打散
隔日再让儿子用竹枝排成所学过的字
直到他熟记为止
冬天寒冷,母亲就坐在床上
拥着被子教儿子读书
夜里纺织,母亲把书本放在膝下
让蒋士铨坐在一旁诵读
乃至会摇醒昏昏欲睡的他
督匆匆他连续学习
母亲教子得法,课督甚严
酷暑寒冷,勤学不辍
蒋士铨九岁时就熟读很多诗文
十多岁时,母亲就让他随着父亲“行万里路”
成年之后,蒋士铨在外游历,诗名渐著
然而,贰心中始终牵挂着家里的亲人
1746年,蒋士铨在年终前夕赶回家中
瞥见母亲为他缝制的寒衣针脚周详
家书墨痕尚新
一针一线,一字一句
都凝聚着浓浓深情
久别相逢之际
母亲的脸上难掩喜悦之情
然而她细细端详之下
总以为孩子有些瘦削干瘪
连忙讯问起在外的艰辛
感怀母亲对自己的关心
蒋士铨写下了诗作《岁暮到家》
全诗措辞浅近朴素
却动听至深、饱含真情
尤其是这句
“低回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更是道出了无数游子的心声
如今,经典传唱人黄品源
登上《经典咏流传》——致敬经典的舞台
他怀着和蒋士铨一样的深厚情绪
忍着泪传唱这首两百多年前的小诗
借歌声遥寄乡愁和对母亲的思念
黄品源的温情演绎
也唤起了大家对母亲的思念
廖昌永回顾起了童年时的石油灯
小时候,母亲便是在油灯旁踩着缝纫机
为儿女缝制新衣服
正如诗里那句“寒衣针线密”
撒贝宁感慨之余
回忆起自己在读大学时
有一次,母亲去学校看望他
而他却由于劳碌欠妥心忘却了这件事
等撒贝宁猛然想起向招待所狂奔时
已经是晚上八九点旁边
一推开门
母亲正在停电的房间里吃着泡面
伤心和愧疚涌上心头,他不禁放声痛哭
在母亲心里
等待孩子、关心孩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但这却让撒贝宁深感“低回愧人子”
母爱是沉默又温顺的
她将关心凝成了一句句嘘寒问暖
将爱意融进了亲手做的每顿饭
将思念化作无时无刻的顾虑
她总能够第一韶光细腻地察觉
孩子的身体和生理变革
母亲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
也没有震天动地的壮举
然而对孩子来说
母亲便是生命中最伟大的英雄
亲情与孝道
始终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
每个人的内心都深藏着
对父母朴拙的爱
当陪你终年夜的人
如今已满头白发,等你归家
愿光阴温顺以待
能陪父母逐步变老
愿万家灯火,家家团圆
子欲养而亲犹在
便是莫大的幸福
(编辑 崔智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