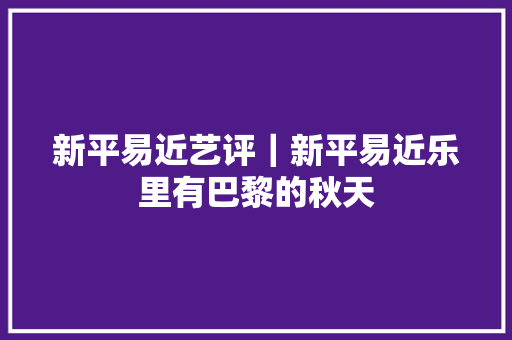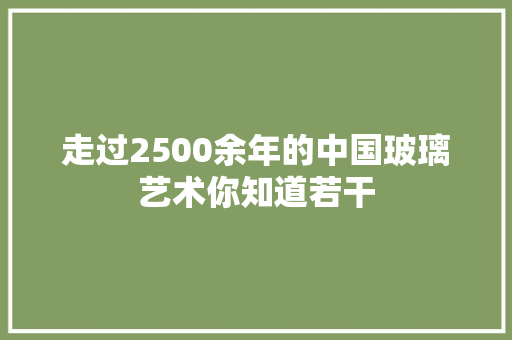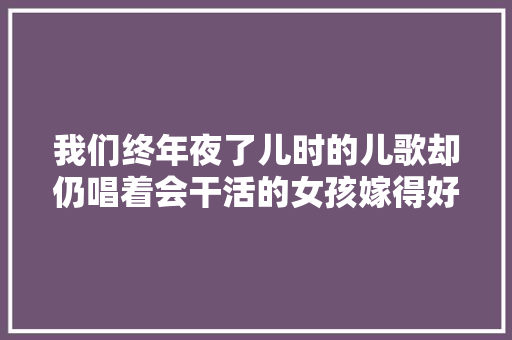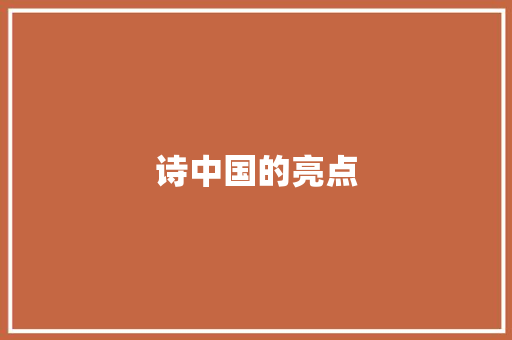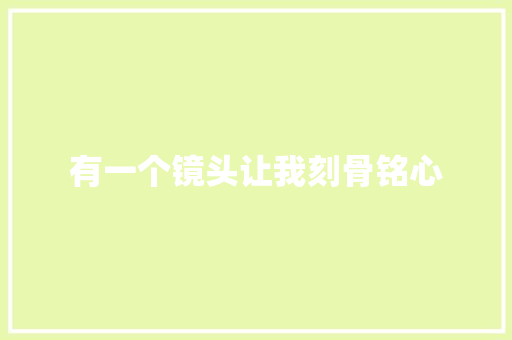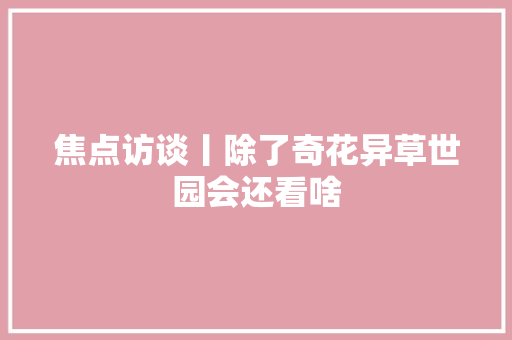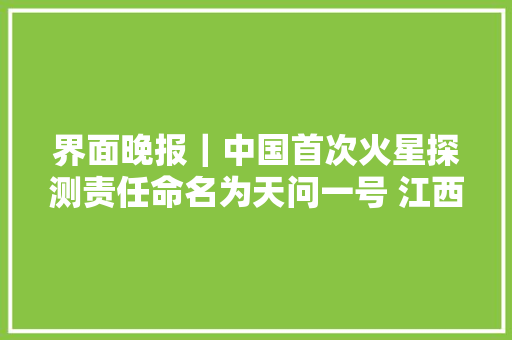由于川普在与希拉里的大选辩论中数次提到中国,福克斯电视台于是跑到纽约唐人街上去随即采访路人。这段视频展示的全是刻板印象:不会说英文的老年人、不懂政治且口音浓重的憔悴的华人,以及屈曲地在跆拳道馆拍摄一段空手道视频代表中国功夫。
【10月3日晚,福克斯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名为“奥莱利实情”的政治评论节目,个中包括一段主持人沃特斯手持发话器在唐人街采访的视频。节目对华人的嘲笑和奚落引发众怒,CBS、美联社等主流媒体都刊文批评。(来源:环球时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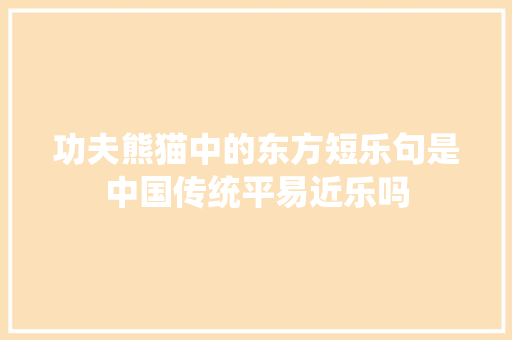
除了展示视觉上的刻板印象,福克斯电视台同时也在音乐上刻板了一把,片头、插曲都是那支耳熟能详的“东方短乐句”。
我们对付这段“唻唻唻唻哆哆啦啦哆”的小调真的不能再熟习了,看过《功夫熊猫》系列动画电影的的朋友们一定也听过那首片尾曲《功夫格斗》(Kung Fu Fighting)吧,“东方短乐句”贯穿了整首歌曲。这首由卡尔·道格拉斯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早在1974年便以单曲唱片的形式问世,在美国不胫而走,在中南美洲国家也广为传唱。如果说这首歌的歌词描述了一个西方人眼中的功夫天下,唐人街来的中国潮人,打得对手高下翻飞,每个中国人都是功夫高手。
刻板印象令人印象深刻,就像海内常常认为东北人都是女穿貂皮男戴金链、福建人就一定读不出美国总统胡佛一样,这首自带刻板印象的盛行歌曲也加强了歌曲开头“东方短乐句”代表东方的印象。
诚挚地讲,就像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一样,西方人实在不大能清楚地分清中日韩(虽然在我们看来三国之间差距很大),以是“东方短乐句”虽然用在表示中国的地方最多,但也被音乐人用在表示泰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上,比如摇滚乐队Rush在《功夫格斗》问世次年推出的《往曼谷的路》(A Passage to Bangkok)以及以及1980年The Vapors推出的《成为日本人》(Turning Japanese),都用到了“东方短乐句”。
东方短乐句虽然短,但却暗合了中国传统音乐“五音”宫商角徵羽,东方特色的是一定有的,同时也一定不是卡尔·道格拉斯创始的。东方短乐句的历史要长,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动画片中,涉及东方,尤其是唐人街的时候,就会涌现这段标志性的音乐,但都算不上特殊出名,最出名的一次大概要数美国指挥家伯恩斯坦在1957年的演讲,演讲词中将“东方短乐句”成为“中国传统民乐”——虽然中国人并没有听过。
一种盛行的说法是,“东方短乐句”来自1847年T·康莫(Comer)指挥的《阿拉丁与神灯之大中华奇不雅观》(The Grand Chinese Spectacle of Aladdin or The Wonderful Lamp)中《阿拉丁快步》一节,但是略懂音乐的朋友看了乐谱就会知道,实在它和“东方短乐句”基本没有相像的地方。
【阿拉丁快步】
清末适逢美国淘金热,中国开始大规模向美国移民,(不熟习这段历史的朋友可以看看孙俪主演的电影《金山》),随着中国移民的到来当然是中国的市民文化。
到了十九世纪末,首先引起美国人把稳的大概是中国式赌钱——番摊,番摊非常类似现在在大赌场里的玩法,1900年,美国作曲家波特·R·安东尼的乐章《番摊》中就涌现了一段节奏高度近似“东方短乐句”的音乐小节。同期间在美盛行的东方摇篮曲《妈妈的中国双胞胎》(Mamma’s China Twins)开头的音节和“东方短乐句”千篇一律。
《妈妈的中国双胞胎》之后,越来越多的音乐涌现涌现与之相似的地方。但这种相似并不局限在中国干系的主题上,与日本相关的音乐也常常能够听到,比如1917年阿瑟·菲尔德(Arthur Field)的《我的横滨女孩》(My Yokohama Girl),开头也是这样的。
到了1919年在音乐剧《东方即西方》(East is West)中,作曲家罗伯特·伍德·博尔斯(Robert Hood Bowers)创作的《中华摇篮曲》中,正式形成了“东方短乐句”的雏形。
到了1925年的乔·桑德斯的《喷鼻香港梦女孩》(Hong Kong Dream Girl)里,开篇的东方短乐句已经和《功夫格斗》里的没有什么差异了。
可以说,经由三十年的韶光,从最朴素的中国摇篮曲中提炼出元素,终极形成了一组固定的节奏和腔调,用以代表中国,以及受到过中国文化影响的远东(东亚地区),并在日后的发展中成为了一种刻板的印象。就像针言、俚语一样,一旦被过于广泛地利用并定格下来,就很难改变了。
《功夫格斗》新鲜出炉时,中国尚未改革开放,而在福克斯白老外的眼中,当下的中国仍旧是彼时的样子容貌,说不好是可悲还是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