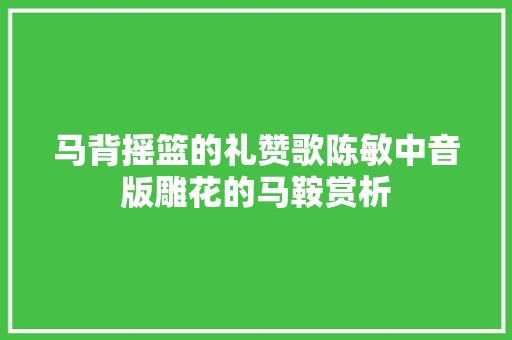Kongurey (Where Has My Country Gone?)
Kongar-ol Ondar/Paul Pena - Genghis Blu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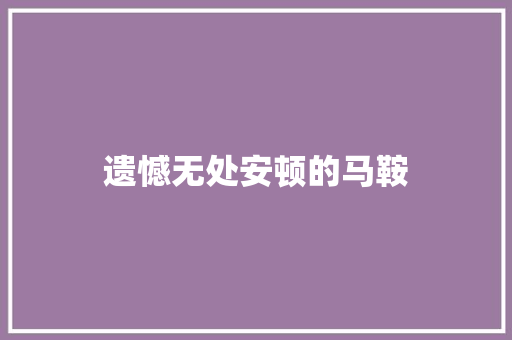
转自:布里亚特 作者 博尔姬·朱拉
2014年8月,我们一行带着无限神往闯入苏尼特草原时,它竟然以赤地千里的断交和令人疼痛的荒漠,颠覆了我们之前对它所有想象和憧憬。赛罕塔拉,这个被称之为“俏丽草原”的地方,又是一个大旱年。皮卡车在一马平川的大地上奔跑,绕过层层叠叠、没完没了的网围栏,我们找寻着所有与马鞍有关的人和事儿。
如果你能够听懂蒙古语,“苏尼特”一词是非常有质感又极具神秘感的词汇,官方对付“苏尼特”的阐明是由一位名叫“雪尼惕”的蒙古族远古部落首领演化而来的。可在民间,人们甘心相信它是“昼夜兼程”的意思。于是,演绎出很多不同版本的关于“昼夜兼程”的传说。可无论这天夜兼程地赶着驼队在这里汇合,还是昼夜兼程地守护成吉思汗的护卫队,彷佛都在诉说和通报着某种信念。
在苏尼特草原的腹地行走,低矮而稀疏的草,稀稀薄薄地铺在地表上,仿佛给大地穿了一件透视装,我们依然能够瞥见它袒露的身体。
如果以一匹蒙古马的名义游历草原,此刻,我是一匹垂头丧气又无家可归的马儿。仿佛自己是一匹前世被主人变卖了的蒙古马,被迫离开了圣洁的草原,那么忧伤,那么难过。
这次远行是冥冥中的声声召唤,让我如此执拗地探求在路上,是在探求前世绿草如茵的赛罕塔拉牧场,还是那曾经牢牢地安顿在背上的马鞍?“我是马,背上有鞍”,这样的豪情使我忘却空气中弥漫的燥热与不安,忘却在探求的路上碰着的挫折和艰辛。
当回过神来,从未有过的一种写作的任务心油然而生,然而,这样的任务感却让我倍感无力,乃至在那个残阳西下、黑云压城的夜晚,泪洒苏尼特。第一次觉得到了脚下的地皮在呼吸,我与这个天下息息相关,我和大地之间有着如此醇厚的关联,令我难以自控,无法逃脱。在孤独中流放自己,就在那个夜晚,我深刻体味到了此番苏尼特之行的主题,与我内心的某种情绪达成了心灵中的殊途同归。
马
没有马,何来鞍?
在进入马鞍之前,我还是想多说说草原上的蒙古人与马。细细品味,他们像承受了天启般组合在了一起。
抛开“草原生态、城市化进程以及游牧文明的渐行渐远”这些略显沉重的话题不说,只是从蒙古人与马的角度去核阅蒙古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便可以生动地揭示蒙古族的实质所在。
马曾是游牧民族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他们生产生活中主要的伙伴。蒙古人对马的分外情绪还由于恶劣的环境和艰巨的生活,他们须要把对生命的期望,对美好生活的神往寄托在某一个事物上,于是在目所能及的天下里,他们选择了马。马使得他们的生活不再平淡,脚步不再迟滞,空想插上了翅膀,生命得到了升华。
游牧民族长期逐水草而居,隆冬的风雪,盛夏的难耐,无休的跋涉,颠簸的生活,使蒙古人尤其看重速率与力量,而马兼具着这两点。
信赖与忠效是蒙古人与马相互关系最准确的表达。蒙古民族给了马情侣般的信赖,而马回报给蒙古人的是勇士般的忠效。蒙古人的马可以从沙场上把奄奄一息、全身是伤的主人驮回到草原;蒙古人的马可以在赛马比赛中为主人再拿一次冠军而累去世在赛场上;蒙古人的马可以长久地跪在酩酊大醉的主人身边,费尽心机把他带回温暖的毡包里。
蒙古人世代与马相依为命,马是他们的朋友,是他们的留恋,是他们的骄傲。蒙古人与马在草原上相互依托,构成了一幅美得没有边际的图画。
然而,在苏尼特草原奔跑了4天,我们仅在一个薄暮见到了两匹马。真是两匹俊秀的蒙古马,棕黄色的鬃毛,四肢细长,目光和顺,低头饮着水,阁下站着一位帅气的牧马人,“苍茫、长风、断崖、流沙”这样的词汇一个挨着一个地罗列在心里。乃至回到呼和浩特,那个苏尼特草原的薄暮还会时时时地浮现面前。
鞍
鞍,无疑是马的伴侣,就像牛奶是咖啡的伴侣。可牛奶离开咖啡还是牛奶,而鞍离开马就只能是一个摆设。
随着草原上的马逐渐被摩托车、四轮车、轿车取代,马鞍更多地涌如今了博物馆的陈设厅里、蒙餐馆的装饰墙上、抑或是蒙古人家的客厅中心。当外地游客走进我们的博物馆,在讲解员的娓娓道来中问这问那,他们对蒙元文化的浓厚兴趣也只能勾留至此了。而更多的蒙古人隔着陈设柜厚厚的玻璃,默默无语。
提及马鞍,大多人只对它有个观点化的认知——马背上的坐榻,犹如我们臀下的沙发那么随意马虎理解。可是,如果细说马鞍的由来、构造、组成部分,我这个蒙古人都是懵懵懂懂的。
听说,马鞍的发明是在春秋战国之交,赵国为对付胡人,抛弃了传统的兵车战,变为胡服骑射,组建了骑兵部队,揭开了古代中原地区单骑历史的序幕。
最初,古人将马系上辔头后,便直接骑光背马,但这样骑马,很难掌握马的动作,而且韶光一长,人也会感到不舒畅,于是便在马背上放置了类似于褥垫或坐垫的东西。
当时马鞍的形状就像两片枕头,里面用羊毛填塞起来,表面都用皮革制成,与其称做马鞍,不如叫鞍垫更准确。这个鞍垫可以折叠,有三条带子将其固定,一条叫肚带,是从腹部来固定鞍子,再用带扣把它勒紧;其余两条,一条是胸带,从胸前穿过固定鞍垫的两侧,防止前后滑动;一条叫鞧带,是绕过马的臀部固定鞍垫的。这样的鞍垫前后高下都比较固定,坐在上面比较稳。这种鞍具一贯持续用到秦朝,仍办理不了马剧烈运动时人在马背上前后滑动的问题,骑手只有靠双腿牢牢夹住马的腹部才能保持平衡,自然十分疲倦,加之作战时要利用兵器,这种鞍垫就显得不足科学了。为了防止骑手在马背上前后滑动,人们想到了让马鞍前后略有拱起,这样就能够前后稳固。汉朝,就有了鞍桥,前鞍桥防止人向前滑动,后鞍桥防止人向后滑动,鞍的形状在实践中逐渐得到完善。
到了元朝,蒙古人对马鞍的制造达到了壮盛,设立了制鞍局,工匠达到了成百上千人。匠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制作出各种十分风雅的马鞍,不但人骑上去舒畅,连马也显得精神。元朝期间,对马鞍的改制终极完成:“其鞍辔轻简,以便驰骋,重不盈七八千,鞍之雁翅,前竖而后平,故折旋而膊不伤;缀镫之革,手揉而不硝,灌以羊脂,故受雨而不断烂,阔才喻一寸,长不逮四总,故立马转身至顺。”
马鞍的制作和利用,使游牧民族终极完成了其马背民族的又一个文化构型。
马鞍是游牧人发展的摇篮,历代的蒙古男儿都视马为宝,对付马鞍的讲求和装饰也不亚于女人对衣饰和扮装品的追逐。
如今,更多草原上的牧人已经把马鞍当做一种图腾,对马鞍制作的浮夸与讲求乃至令人咋舌,有金制马鞍、银制马鞍。他们彷佛把对马的情绪一股脑地都砸向马鞍,不惜重金。让我嗅到了这样的潜台词:我们已经失落去了马,可不能再失落去鞍!
做鞍杈的汉人
赛罕塔拉镇的居民区以平房居多,这里充满了平常百姓家浓浓的生活气息,小狗听到我们的走动,隔着门洞在里面“汪汪”叫,小孩子三三两两走出家门,好奇地望着我们,可镜头对准他们时,他们又腼腆地跑掉。
走进一条狭长的巷子,不远处便是韩师傅家。四合院子里堆满了木材。这是从河北运来的桦木,这种木材最适宜制软鞍杈,能担保鞍杈不开缝,不变形。韩师傅总会提前一年买好木材,担保木材有一年的晾晒韶光,第二年再砍鞍杈,依次顺延。韩师傅站在院子的正中心,如数家珍地给我们先容着鞍的点点滴滴。两个偏房是他的手事情坊,韩师傅的儿子正在对着一个鞍杈心神专注地打磨。
韩师傅只做鞍杈,这完备属于木匠活儿。事实上,很早以前草原上做鞍杈的基本上也都是汉人。在苏尼特草原,韩师傅的鞍杈远近有名,角度舒适,工艺风雅,使他成为了牧人的好朋友。如今虽然搬到了镇上,可是,只要老乡家有人要做鞍杈都会找到他,以是他对马背的熟习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一个蒙古人,乃至多于蒙古人。他说,骑马在草原上驰骋是他最幸福的时候!
鞍杈是由六块雕凿出来的实木拼对粘合起来的。两侧各有一块长形木板,顺向平铺在马背上,其上各接一块拱形木,在马背上空两两相交成一桥型,供人乘坐。桥型前后各有一弧形木块,前面的稍高,角度近乎直立,以防奔马急停时骑手跌落,后面的相对宽阔、平坦,使骑手乘坐舒适。
韩师傅说,做鞍杈讲究个“三圆、二平、一合”。所谓“三圆”是说鞍杈的前后鞍桥圆,龙口圆(龙口是指鞍桥的下口,也便是搭在马脊的空洞部分),梁头圆(人的臀部打仗的地方)。所谓“二平”便是说鞍杈在马脊上的两块平面板要平整光滑,要同马脊梁吻合,下压的力量均匀。所谓“一合”便是说鞍杈最讲究合套。由于它的分外构造,工匠们不用锯子,这显然有别于其他木工活。制作时,首先要把木料粘合成鞍杈的大样子,粘合是要一定技能的,因此把“一合”作为制作鞍杈的主要环节。为什么把制作鞍杈叫做“砍鞍杈”呢?便是由于制作要用砍、钵、焊、挖、挫的办法,不用锯。韩师傅说,要想真正学会制鞍杈的手艺,少说也要十年的功夫。他说,磨练一个好鞍杈的标准便是在马背上放一张纸,骑上一圈回来,纸无缺无损,那鞍杈绝对便是一流的。
韩师傅的鞍杈,牧马人拿回去是担保能用一辈子的。最近几年来,订购鞍权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忙不过来,两个儿子也加入到制作鞍杈的行列中。可以说,韩师傅的小作坊已然是一个家族式的经营模式了,鞍杈的买卖也一年比一年好。
我好奇地问,草原上的马越来越少了,为什么要鞍杈的人却多了呢?韩师傅说,现在大部分的需求都是为了知足一些商家的手工艺品,当马鞍用的大概有,但是不多了,大多是为了寄托情绪。
做马鞍的银匠弟子
“磔子是马鞍的主要组成部件之一。它的浸染是防止鞍蹬子碰伤马身两侧,同时防止马身上的汗水毛渍弄脏骑手的衣服。也有保护骑手,防止脚全部插入蹬口发生危险。”苏乙拉大概看出了我们一脸的迷惑,于是把一个刚刚包装好的马鞍拆装,拿出来做讲解。
苏乙拉是一个五十开外的中年男子,他在当地的有名度不仅来源于他的手艺好,还由于他的师父是德王府的御用银匠。曾经,他的师父道尔吉的哥哥是德王府的御用银匠,哥哥去世后,道尔吉便上门为德王府加工王公贵族所需的各种银饰。道尔吉70岁的时候收了苏乙拉为徒,于是,他便成为了道尔吉师父的关门弟子。
苏乙拉虽说是一个银匠,可是他制作的鞍磔也可以说是一流的了。
如今的草原,有的地方仍在沿用比较古老的制磔工艺。把皮革晒干后浸泡水中3至5天,趁着湿把毛刮净,放入芒硝水浸泡7天旁边,取出趁湿鞣作,也便是用浮石揉搓,用木棍搓压,直到把皮革弄定型。再根据所需的尺寸裁剪成磔子,然后涂上畜生的骨头油就可以了。现在制作磔子中最抢手确当属喷鼻香牛皮磔,这是用化学质料配方泡制的皮革,这种磔子光上油就要12道工艺,麻油、桐油,要把皮革硝熟、揉搓、修理、炀面、压花、铺垫、透油等风雅绝妙的工艺。这样制成的皮革,光亮平滑犹如绸缎,裁制出来的磔子不仅精美而且舒适。
鞍杈上面的骑乘部分敷以玄色喷鼻香牛皮,以四枚银泡钉固定,其他朝外的部分施以红漆,所有的棱线部分都可以饰以小指宽的白银或白铜鞍条。鞍桥旁边两侧凿孔,以牛皮带悬挂起一对马镫,同时也在这里固定肚带根和肚带。肚带根是用牛皮劈成细条再体例起来的,肚带结实优柔,是用马鬃或马尾编织成的,一端系有带扣,二者在马腹下牢牢相合,才能把整套鞍具固定在马身上。鞍桥下面是鞍韂。鞍韂又分为“大韂”和“小韂”,其浸染在于遮挡飞扬的尘土,同时也起到装饰和美化浸染,在古代汉语中又叫作“障泥”。就好比汽车下面的挡泥板。大韂是垂于马背两旁的两大片玄色喷鼻香牛皮,肚带根和肚带从鞍桥的两边向下打孔穿过大韂,隐蔽在大韂的下面。小韂是一小块圆形或梯形的玄色喷鼻香牛皮饰片,覆在鞍桥旁悬挂马镫的凿孔上方,有条件的人家还会在那上面缀上烧饼大小的六、七个银泡子。大韂的下面是覆在马背上的两层毡子,便是古汉语中所说的“鞯”了。
鞍桥的四个角上也要打上小孔,穿上四到六根小指粗细的牛皮捎绳,蒙古语叫做“甘吉格”。“ 甘吉格”的缘起本便是长途出行的时候在马鞍上捆绑行囊的皮绳,如今除了后面两角上还各保留了一两根细软皮绳外,别的的都演化成了黑亮粗硬的装饰物,有时下端还要打上银箍。人骑在立时颠起来的时候,“甘吉格”有节奏地打在大韂上,“夸夸”作响。
看似并没有那么繁芜的马具,在苏乙拉的讲解中生动美好。每个孔的存在都合理必要,每根皮条都有不可小觑的功能和职责,我想问,都不是用来乘骑,无非是一个陈设品,干嘛这么疲于细节,何不学着偷工减料?没出口的话还是理智地咽了回去。实在,答案就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