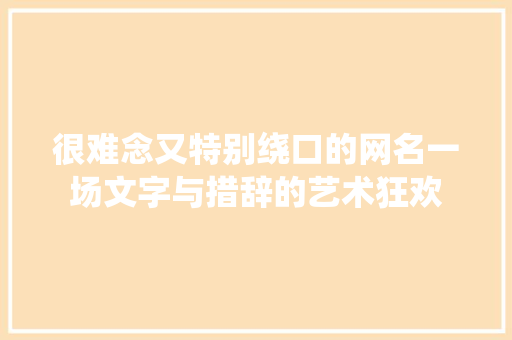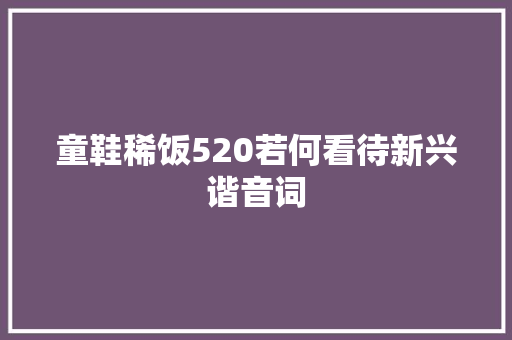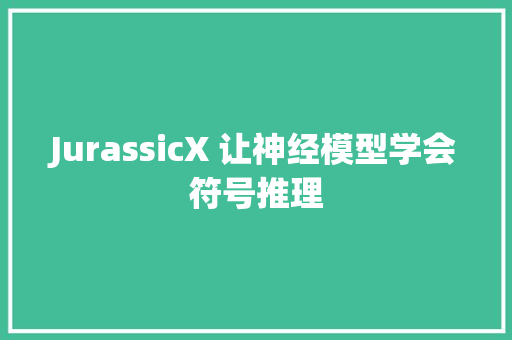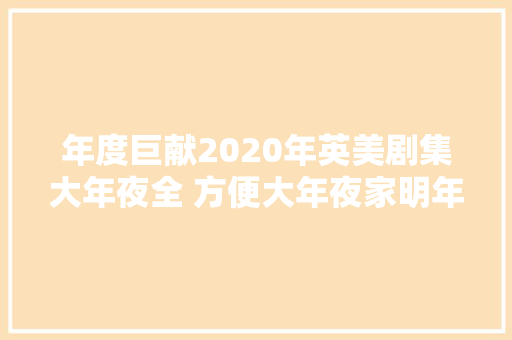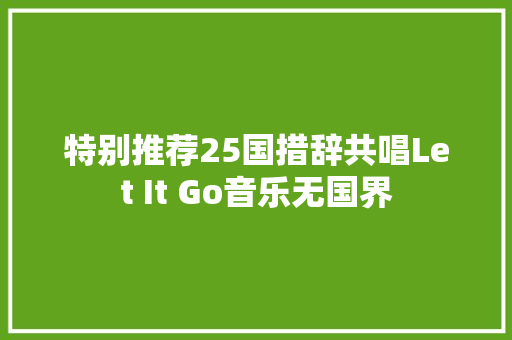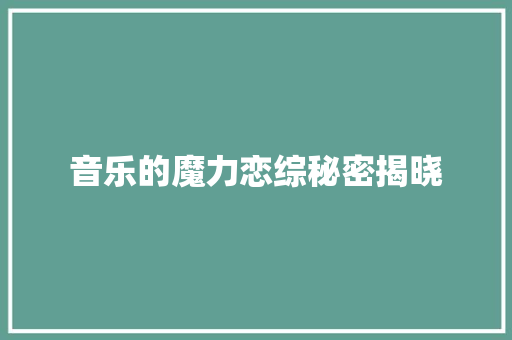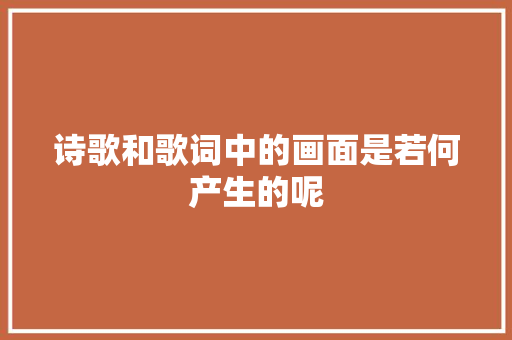刘熙载《艺概》分为《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六部分,个中《书概》属于书论,其他五部分属于广义的文论。在《艺概》的文论和书论中,“疏”“密”二字均多次涌现。鉴于文学和书法是两个不同领域,文学和书法的疏密势必存在一定的差异,加之刘熙载在文艺批驳时常点到即止,造成了《艺概》“疏”“密”的内涵仍有不明之处。
措辞和形质的疏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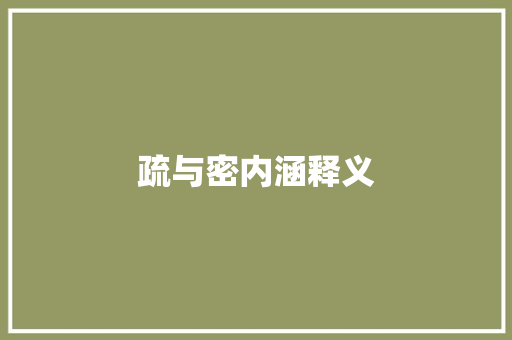
《艺概·文概》曰:“《檀弓》语少意密。”又曰:“《檀弓》浑化,语疏而情密。”(以下《艺概》引文仅标注篇名)显然,“语少意密”与“语疏情密”意思附近,故措辞之“疏”即措辞之“少”。“少”不但是措辞笔墨字数少,更是指措辞简约、扼要、洗练。于是,《文概》又曰:“刘知几《史通》谓《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余谓,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
比拟可知,措辞的“简而要”“约”“省”便是措辞之“疏”。反过来,措辞之“密”不但是措辞笔墨字数多,更是指措辞繁缛。在《文心雕龙·体性》中,刘勰提出了八种文风(“八体”),个中“精约”和“繁缛”相反,“精约”有“核字省句”之义,“繁缛”则是“博喻醲采”,即广泛作喻、铺陈、描述从而具有彩丽竞繁的措辞美。《文心雕龙·体性》又曰:“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藻”指华美的文辞,刘勰用“密”来形容“藻”,进一步佐证了措辞之“密”便是文辞艳丽、繁缛。
如果说措辞是文学的物质外壳,那么形质便是书法的物质外壳。中国古人看待书法以形神不雅观为最普遍盛行的视角。形质的“疏”“密”指笔画之间、字与字之间、行与行的间隔大小,间隔大为疏,间隔小为密。例如,汉隶的结体以横扁为主,以是高下笔画的分布多茂密;杨凝式《韭花帖》字距、行距大,以是显疏朗。《书概》曰:“蔡邕洞达,钟繇茂密。余谓两家之书同道,洞达正不容针,茂密正能走马。”此句的“洞达”因与“茂密”对举,故指疏朗。蔡邕隶书的结体以方形为主,高下笔画的分布比《曹全碑》《礼器碑》疏朗一些。锺繇楷书的结体以扁方为主,且笔画肥厚,于是显茂密。但刘熙载敏锐而辩证地提出,蔡邕隶书虽疏朗,但仍有茂密之意(“不容针”);锺繇楷书虽茂密,但仍有疏朗之趣(“能走马”)。
笔法和章法的疏密
法度也分疏密,如刘熙载说:“[孟子]度越诸子处,乃在析义至精,不惟用法至密也”(《文概》)。法度的疏密紧张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笔法的疏密。《词曲概》曰:“耆卿词,周详而妥溜。”“周详”指笔法风雅、周详。如柳永(字耆卿)《定风波·自春来》:“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喷鼻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把“日上花梢,莺穿柳带”与“犹压喷鼻香衾卧”相比拟来反衬思妇之怨,尚不很详细,至“暖酥消”(肌肤变差、腰身变瘦)、“腻云亸”(头发散乱下垂)则非常细腻,将思妇的哀怨和惨愁形象直不雅观地刻画出来。
笔法周详有助于将人物、景象、动作描述得生动如画,但利用过度会造成拥挤、堆砌、疲塌的弊病。但这些弊病并不是笔法周详一定导致的结果;笔法周详是可取的,不可取的是过度利用这种笔法。书法也强调笔法周详,相反,笔法粗疏则多被诟病。《书概》曰:“五代书,苏、黄独推杨景度。今但不雅观其书之尤杰然者,如《大仙帖》非独势奇力强,其骨里谨严,真令人无可寻间。此不必沾沾于摹颜拟柳,而颜、柳之实已备矣。”刘熙载提出,杨凝式(字景度)《大仙帖》笔法极严密,虽在外在形质上与颜真卿、柳公权不似,但得到了颜、柳的真核。
第二,章法的疏密。章法之“密”指构造或逻辑严密,“疏”指构造或逻辑具有跳跃性,即“断”。《文概》曰:“《左传》善用密,《国策》善用疏。《国策》之章法、笔法,奇矣,若论字句之精严,则左公允推独步。”章法之“疏”(或“断”)表示为,在描写的景物、阐述的事宜、论述的道理等方面具有间断性、跳跃性,给人一种逻辑不严密之感。但章法不能只有“疏”(或“断”),还要使看似不干系的景物、事宜、道理等做事于一个共同主题,即“明断暗续”。实际上,章法的“暗续”正表明全文构思周密。是故,章法之“密”而不是“疏”才是文章成功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经义概》提出:“法取密而通。”
在书法中,章法的疏密有两种情形:一是指字距、行距的大小;二是指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照料情形。前者实质上是可见的形质的疏密;在后一种情形中,书法推崇的是章法之“密”而不是“疏”。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曰:“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行间茂密”即章法之“密”,指的是高下旁边的字在大小、是非、欹正等方面相互映衬,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由此高下旁边的字不是伶仃的,而是联系紧密的。
内容和神采的疏密
在文学中,内容的疏密有以下几种情形。其一,物象的疏密。《赋概》曰:“赋以象物。”物象的塑造就涉及疏密问题。但《赋概》又曰:“赋之为道,重象,尤宜重兴。兴不称象,虽纷披繁密,而买卖索然,能无为识者厌乎?”作赋不能纯挚追求物象的繁密,更要讲求物象的起兴功能,即能使读者触物起情,否则,一味的繁密就会造成物象拥挤,甚至没有生气流于其间。其二,事宜的疏密。上文“其事详而博”“事详”“事增”便是事宜之“密”,反过来,事宜之“疏”是事宜少或略。作者阐述事宜是疏好还是密好,不能一概而论;就中国史传文学而言,“辞约事详”确实是一个普遍追求。其三,情绪的疏密。“语疏而情密”是指措辞简要而情绪丰富,这常常是文学追求的胜境;反之,文辞艳丽而乏真情则是文学应避免的疵病,如《文心雕龙·情采》曰:“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其四,义理的疏密。《文概》曰:“密者,义法也。”又曰:“太史公时有天河之言,而意理却细入无间。”前句并不是对“密”下定义,而是说“义法”可以呈现出“密”的特点,后句“意理却细入无间”正是意理丰富茂密之义。其五,言外之意的疏密。《文概》曰:“言外无穷者,茂也;言内毕足者,密也。”“茂”的本义是草丰硕,草丰硕自然会造成“密”的特点,以是“茂”“密”具有明显的同一性。《文概》这句话与其说是对“茂”“密”的定义,不如说是一种互文手腕,即是说,“言外[韵味]无穷”“言内毕足[义法]”既是“茂”,也是“密”。
很多文境、诗境、词境不仅有情景交融的层面(“实”),还有景外之景与味外之旨的层面(“虚”)。刘勰的“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文心雕龙·隐秀》)、严羽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辨》)等,说的都是文学作品富有言外之意,而富有言外之意正是“茂”“密”的一种情形。在以上五者中,物象的疏、密都有合法性,而事宜、情绪、义理、余味之“密”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多是被肯定的。
书法的神采也有疏密问题。《书概》曰:“古人草书,空缺少而神远,空缺多而神密。俗书反是。”“神密”“神远”是神采茂密、韵味深远,这正是书法追求的高雅境界,反之,气韵缺少或稀薄则是书家力争战胜的弊病。
综上可知,《艺概》乃至中国美学虽然常常把“疏”“密”并用(即利用的是这两个字的变形说法),但并用的“疏”“密”所言说的工具很可能不是同一个东西。例如“语疏情密”“语少意密”,“疏”(“少”)言说的是措辞笔墨,“密”言说的是“情”“意”。“疏”“密”有时确实是两种相反的风格,例如书法的结体、诗词所塑造意象的疏密便是两种不同风格。作为风格的“疏”“密”都有其合法性,只是不同的作者和批驳者在二者之间会有所偏好。“疏”“密”并不总是指风格,在某些情形下乃至是一种弊病。例如,史传文学的事义之“疏”、诗词的余味之“疏”、文学的章法之“疏”以及文学的意象过密、书法的字距行距过密,都反成一种不敷。总而言之,“疏”“密”的安排要视详细情形而定,“疏”“密”二字的利用也须要谨严才能精准。
(作者系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本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仅代表作者不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供应信息发布传播做事。
ID:j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