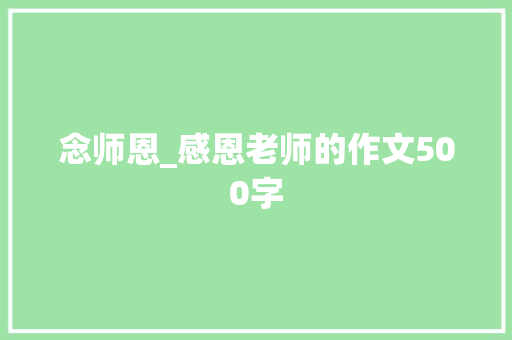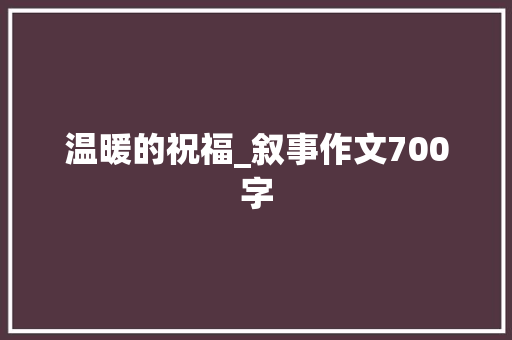轻倚脂奁 上新妆
台步熟稔 旧曲调

抛却云袖 暖雕梁
我第一次见到清寒是在民国八年,他站在一条漆深的巷子里,就在一枝探出墙头的梨树下,白衣,白帽,白皂靴,执一把白色的折扇唱着:唱尽旧曲,欢不见;痴念错缘,悔断肠。
他生的真好看。
几经辗转,不知是什么因缘,我在寒春堂里谋了个洗整戏服的差。寒春堂,我默念着这三个字,恰那个谪仙一般男子所在的戏班。
于是我每日提了个小凳子,就坐在一个小小的破院子里,一件件洗着戏服。那些戏服仗着平日里自己的光鲜艳丽,倔强在水中不肯下沉,但只消我用手指轻轻一按,戏服绝望地吐出一串气泡,就黯淡躺在盆底,任我摆布了。我何尝不是这样,一个逃荒出来的孩子,一个家仇难报的孩子,在这样的光景里,能够这样平平安安的,哪怕一直这样洗下去,也是好的。
可我莫名喜欢听那些哥哥姐姐们唱戏,捏了嗓子,咿咿呀呀的,当真好听,我知道自己能有如今的平安日子已是万幸,可我竟是那般不知足。我想登台。我想唱戏。
每日做完了手里的活计,我就常猫了腰躲在那些哥哥姐姐练戏的戏台后面,听他们拿捏几段唱词,台步踩得咚咚响。我渴望着,渴望像他们一样站在戏台上,穿一套戏服,抛一节水袖,暖一段雕梁。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狂放的渴望,竟趁着他们每天早上吊嗓子的时间,在后山寻了个僻静的地儿,也学着他们咿咿呀呀的,甚至能学出几句唱词来。可我觉得不够好听,脑子里全是那个素衣男子的悠长唱腔。
我至今无法用语言描述我有多羡慕那些哥哥姐姐脸上绘出的惊鸿,特别是他们手腕一提为眉角勾出的完美弧度,那些胭脂就像勾人的小妖精,日夜勾引着我的魂魄,我常暗想自己如若描上那样的胭脂会是如何的扮相。一日里我偶然拾到了一位姐姐废弃的脂粉,虽都见了底,可我仍是欣喜若狂。于是在那样的一个夜晚,天上只有月亮独自酌着一杯历经了沧海桑田的陈酿,用迷离的醉眼肆意洒下大片的月光,整个院子都醉了,我也朦朦胧胧地从我那厢房里拿出了那套废胭脂,就那样鬼使神差来到了我洗整戏服的小院儿,那般恍惚地寻了个凳子,坐在了我平日的大木盆边上,掏出脂粉来,对着木盆里的水小心勾画,仔细而谨慎,一笔一笔,几近沉迷。那水可真清啊,映出满满的天,抓住月光不放,也照出了边上的竹影成双。像清寒的眼睛,我如此这般想着,透亮而沉静。却忽得发现水中真的出现了一双如此的眼睛。我慌忙转身,看见那个素日清雅的白衣男子迎着月光对着我,三千青丝松挽一个髻,越发映得他如月容颜,颔首,浅笑,他挥手示意我坐好,从我手中缓缓抽走了眉笔,轻声说:“丫头,像你这般画是不行的,你如此坐好,我给你画罢。”他真的执起眉笔,在我的脸上精心勾画,猛地呼吸一滞,他的手触上我的脸,是淡淡的冰凉,天上的月光应该也是这样的触感吧,又带着几分轻柔。我就这样对着他的专注清颜,一瞬,竟看痴了。笑比月光华,腮边生情忙,玉渗白肤脂,丹唇抿凄凉。我和他就如此在这月色盈满的院子里,一坐一立,就静静伴着月光流转,缓缓的,舒适清朗。“好了,丫头。”他收回手去,仔细端详,又满意点头,我自水中窥去,水中清晰显出一副杜丽娘的扮相,清秀的眉眼,一点红唇,眉角弧度可人,整个竟像偷去了梨花的三分姿色。回头看他,他轻轻一笑,顿时草长莺飞,明亮了整个世界。“丫头,我听到你每日里在那后山练戏了,明早随我去见师父吧,我求他,求他叫你唱戏,你是个有戏魂的人。”我竟痴无言语,他伸手揉了揉我并不整齐的头发,转身而去。我呆呆望着他的背影,看着他白衣配着一袭乌发,淡出了小小的院门,淡去了远方。我仍那样呆呆坐着,盈月新挂疏梧桐,半岁静祥,顶了一脸杜丽娘的妆,不怕夜长,坐到天亮。
清寒果没有食言,第二日就带我见了师傅,倚着昨晚的妆,我唱了段杜丽娘的念词,师傅欣喜缓缓点头。于是我也照例分了旦角,领了水袖,配了胭脂,每日也啊啊哦哦地唱着,与那些哥哥姐姐一样。只是夜里,我总会握着他与我描妆的半支眉笔,一遍遍在心中绘着他的模样。
时光静长,戏班里的哥哥姐姐也都个个正式登台,很快便轮到了我。师父找到正在练戏的我,与我说了登台的时间,又道:“你也要正式登台了,以前的名字也不便再用,想个名字吧,也算给自己的一个新生。”这是戏班历来的规矩,我早已在心中拟好,于是脱口而出“清柒,就叫清柒好了。”师父想了想,点头同意,却又问我打算唱哪台戏,和谁唱。我心中满是那个唤我丫头的男子为我描眉的模样:“我要唱《牡丹亭》,和清寒一起唱。”可难色却涌上了师傅的脸:“清柒,昨日商泠与你提了同样的要求,我已允了她……你看……”心中的某根弦被狠狠拨动,发出了沉郁的呻吟,但我仍是笑:“这也无妨,师父能收了清柒为徒已是大恩,永生难报,登台的事情,不与清寒也无妨。”我安然转身,看向那房顶上的梨花。
是夜,我独身一人坐在窗前,手握那半支眉笔,望着天上的半轮弯月久久发呆。却忽得听到房门被轻叩三声,我放下手中的眉笔,起身开门,是他。我那个朝思暮想的人儿就站在我的面前,却一言不发。又是久久对着,月光还似上次流淌,只是淡了半分。是清寒缓缓先言:“丫头,我……商泠她……”我微笑示意他不必再说,转身带上房门。又过了许久,我听见他远离的脚步,才匆匆把门打开一个缝,以不易察觉的呼吸,暗色的眼眸,看着他单薄的身影消失在小小的院门。
我跌坐在椅子上,许久,才莫名沉重地抬起手指,蘸着早已冰凉的茶水,一遍一遍写着“清柒”二字,又看着水迹一点点消散化为乌有。清柒清柒——我终想做清寒的妻。我知道这终究算是痴想,他已是我的贵人,只要学戏,我相信我会有出头之日。但我实在不能忘记那个月色好到不真实的夜,他执这支眉笔为我温柔勾眉。我想与他同台,唱《牡丹亭》,唱《长生殿》,他唱柳梦梅,唱唐明皇,我唱杜丽娘,唱杨贵妃。纵使是得寸进尺,我仍是那般想得到。
但我们都不能。
第一次的登台可以用完美形容,我一唱红遍京城。达官贵人们都争着向寒春堂递帖子,争得头破血流,只为请我去他们府上唱一个堂会,或赴一次宴。
那晚的庆功宴,所有人都喝了很多酒,那三年的梨花酿醉了众人,醉了淡色的月光。我谢了师父,谢了众人,独自坐在一角浅浅地笑。恍惚间,有人走到了我的身后,听脚步声,我知道是他。四杯薄酒,熏红了他的面颊,越发衬得他如一枝傲绽的梅花。他一个踉跄扑到了我的面前,眼神迷离却是认真。他大着舌头,词不成句,却将每个字咬得那么重:“丫…丫头,我知知道……你计……计划划着什么……么,我……我心心疼你呀。别那样好……好吗?我陪你呀。”我心下已是一惊,不知他是如何知晓,但我触着他的温度,趁他眼神此时不清,已是满脸的泪。又听他断断续续说道:“丫头,你你唱戏……戏戏是为天下人,还是……”声音到最后已不可闻,却发现他趴在我前面的桌子上睡着了,像个孩子一样。于是,在这个月色清淡的夜里,又是我们两个,又是在那个院子里,我陪着我的清寒坐了一晚上,一直到天亮。
无人知道我和李督军有了什么约定,只是突然一天,我在众人惊愕的眼光中坐上了他派来的汽车,师父看着面前的一包金条眼里有写不出的惆怅。我提着裙角,环顾四周,单单,单单没瞧见那个淡色的影子,别过身子用手帕拭了拭眼角,然后迫使自己带上最惊心动魄的笑容:“走罢。”任凭素白梨花落满我乌发。
就这样,我住进了李督军的府中,仍是一个花旦戏子的身份。还记得那日李督军酒后勾着我的下巴,细细端详,而后又缓缓开口:“清小姐,只要三件事。三件事后,或放你归去,或李某设宴迎你为新妇。啧啧,果然是一个水灵灵的花旦小美人儿。”“清柒知道了。”我别过头去,说道“清柒”二字,心中却不由狠狠一颤,清寒,那个肯唤自己丫头的谪仙般素衣男子,如今又是如何,总是他是如何伤心换的天悲怆,现在怕是都化成了剪影一般,看不真切了。
为了完成李督军所谓的任务,我开始和不同的人搭戏,唱《西厢记》,唱《百花记》,唱刀马,唱青衣,可身边的人儿都不是清寒。唱一折戏犹如编一个谎,要让所有的人相信并为之感动。但我骗不了自己,他们都唱不出清寒的嗓音,因为他们都不是清寒。
在无数个灯火阑珊的夜里,风与戏偏廊。七月流火,我只着了单衣倚在窗边,用手指尖在窗框上点着不成曲调的节奏。我又在想着那个唤我丫头的人了,盼着他早些忘了我,重整温润,但打心底儿又不愿教他忘了,恨那么一辈子也好。看着那一弯月亮,我就独独坐在那儿痴了许久。银月影纵诉洛阳,漫漫长夜候今央,重杏犹似稀雪相,少年已非重游郎。
来到李督军的府上已经五年了,等最后,等最后我完成了所有的事,就办下一个大宅子,接寒春堂的人都去里面住,热热闹闹的。如若,如若清寒他,肯谅了我……嘴角刚勾起一丝笑,就听门外小厮说道:“清小姐,督军给您这次请的搭戏的角儿到了。”我敛了笑容,淡淡道:“让他进来罢。”
即使听到来者的脚步靠近,我并未转身,只是随手拿了一盒上好的胭脂细细磨着,漫不经心候着来人向我屈膝问好。“丫头,你这一走就是五个年头啊。瞧瞧你,都把自己养瘦了。”正在磨胭脂的手狠狠一颤,那熟稔的清朗音调,我这一生是听不错的,可为何来着是他…..泪水决堤,无法抑制涌出了眼眶,我浑身颤抖,缓缓转过身去。模糊泪眼中依稀是那绣了梨花的白衫,挺拔的身影,如星明眸,还有那如旧的,像盘了百年的玉一般温润的浅笑。思绪成愁,待我日思夜想的人儿就这样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竟不知道如何面对。就那样呆呆望着,心中无限愁思难理,好似一直相对无言到皓然苍颜白发。
要说京师里的名角,所有人都说是清寒和清柒。听闻楚督军要在寿宴上请他俩唱台戏,整个京城都沸腾了。清寒与清柒将要同台,所有人都在期待那一天,那个足以在茶余饭后成为所有人谈资的那一天。
我将与清寒同台了,唱的是《牡丹亭》,我从来都想与他唱的那一折。
开戏前,我们在后台,他拿出眉笔,正伸手准备画眉。我微笑上前,从衣襟掏出半支眉笔,叫他坐好,一笔一划,为他描着,就像他那夜为我画眉一样。时间在针脚外浅诵《上邪》,我欲与君绝。
鼓停琴止,一曲终了,杜丽娘与柳梦梅携手归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昨日今朝,眼下心前”,“从今后把牡丹亭梦影双描画”,我永远记得这一天,我与他唯一同台的一场戏,被我小心翼翼收藏在了记忆的最深处,连他袖口的胭脂一点,在斑驳的过往中,也分外清晰。
忽然间人群大乱,我自锦衣华服中抬头张望,楚督军胸口插着一根钗头凤倒在台下,身旁的清寒已不见身影。
“我知道你计划着的事。”
“我心疼你。”
我似乎在此刻知道了一切。就像一朵梨花的凋零所呈现出的真实,所有的过往都浮现出来,所有的行为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于我,于他。但可悲的是,这样的真实,在这一瞬竟如此令人厌恶,我一遍遍在记忆中重复,却悲哀的发现这本来就是错的,本来就是错的。任凭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如何用泪水冲刷我的悔恨,可是都回不来了,就像一缕梨花的香气飘散空中,再也回不来了。
他终究与我是一段错缘。家仇国恨,楚督军做过的人狗不如的事情我会记一辈子,母亲临死前的凄凉眼神就那样每个夜里盘桓在我的脑海,弟弟在襁褓中戛然而止的哭声就那样时时刻刻回荡在我的耳畔,像是梦魇,却不是梦魇。我知道我能等到这一天,我用五年时间为今天做准备,那淬了毒的凤头钗本承载了我所有的仇恨,却难想……
清寒的白衣在我的脑海里不散。
清寒的血染的红衣终生在我的脑海里不散。
终是错缘,但愿那月落重生灯再红。
我不再唱戏,只是握了那半支眉笔,站在他常站着的地方,才发现那里可以望见我平日练戏的旧戏台……
恍惚间,远处传来了飘渺的歌声,似有似无,是谁在吟唱,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我只要攥着我的半支眉笔,在梨花树下点着小碎步,一圈一圈,好像那月下的旧时光,好像在旧戏台上,好像我的清寒,还远远看着一样:
轻挑残阳 晒西窗
画中烟雨 奈凄凉
赤脚板起 伶鼓上
贵妃扇掩 流年荡
不堪伶仃 夜寒长
风透青衣 戏偏廊
更执素手清弦拨不动
候到天明 染鬓霜
浇一壶 陈年酿
水送清冷 天茫茫
醉疑那 月成双
点破虚影 化星光
吊眼梢 连髻旁
美眷如花 单步惆怅
起悲歌 舞单裳
借一场烟雨 寄入梦
轻倚脂奁 上新妆
台步熟稔 旧曲调
抛却云袖 暖雕梁
唱词如咽 念玉郎
憔悴娇颜 并悲慌
挑抹不复 清音绕三婉
一曲尽罢 皆断肠
浇一壶 陈年酿
水送清冷 天茫茫
饮清月 解浊酒
疏影梧桐 漏星光
悲歌尽 单裳凉
烟雨聚散 恨梦已僵
强啼红铅 满目荒
候无人时 泪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