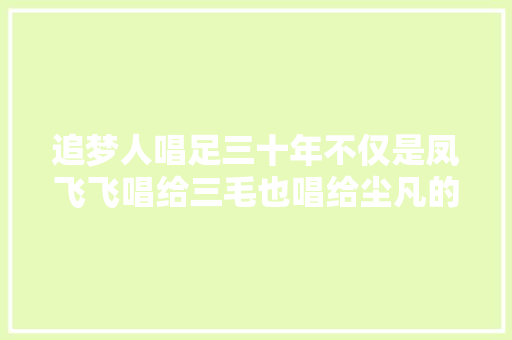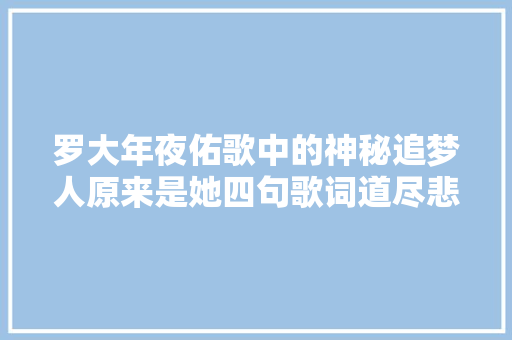出版:北方文艺出版社
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三毛,水底有一个隧道,一贯通到深海,进了隧道里,只见阳光穿过漂浮的海藻,化成千红万紫亮如宝石的色彩,那个美如瑶池的地方,可惜你不能去同享,我再去一次好吗?——某次,荷西下潜之前对岸上的三毛如是说
那日,荷西送走三毛和她的父母,就回到了拉芭玛岛。第二天事情完,他和朋友们去海滩野餐,像之前的很多次海边野餐一样,他要下到海里为大家捉些鱼回来吃。这对荷西和朋友们来说是件最普通不过的事情,会潜水的荷西总会潜到水下为大家带上来很多美味海鲜。他也常常把捉到的鱼带回家。有一次,三毛在厨房做饭,荷西就提了一条很大的章鱼回来,他跟三毛说,他潜到海底的时候这条章鱼缠住了他,他就把它捉住了。可是这一次,荷西穿上潜水衣,提了射鱼枪下海后却迟迟不见回来,朋友们预感到不妙,纷纭奔向海滩,会潜水的朋友和附近的村落民一遍又一遍潜到海里探求,一贯到了半夜,玉轮升到半空时,他的尸体才被打捞上来。
这一次小别,成了永别。
这一年,他们没有过完秋日。他们的故事,静止在1979年9月30日。这一日,间隔中国的中秋节不到一周。他未留下只字片语,便与她永久地分别了。
得知荷西失事时,三毛那长达几个月的不安感与现实发生的事情一下子对接起来了,“咔嚓”一声,不安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撕心裂肺的痛。只管这一年三毛有各种不祥的预感,但这结果她还是无法承受。她之前一贯以为,那些不祥的预感是针对自己的,先离开的人会是她。在接到噩耗的那一刻,三毛从心底升腾出一种“狂渴”的生理反应,这种觉得在往后的日子里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每当她过于悲哀的时候,“狂渴”感就会袭来。
她赶回拉芭玛岛时,荷西的尸体已经躺在墓园阁下的斗室子里,这个墓园是她和荷西常常闲步的地方。她不相信躺在那里的是荷西,可是她进去确认,又千真万确是荷西。他的脸,他的潜水衣,他的射鱼枪,每一条都是吻合的。
相爱时有多欢快,告别时便有多痛楚。荷西去世后,三毛陷入半疯状态。
守灵的夜晚,她守在荷西身边,像往常一样拉着他的手,在他耳边喃喃重复着:“荷西安息……荷西安息……安息……不症结怕,一贯往前走,你会看到阴郁的隧道,走过去便是白光,那是神灵来接你了。我现在有父母在,不能跟你走,你先去等我……要年夜胆,要年夜胆,没有我的时候你也要年夜胆。”三毛说完这些话,荷西的眼睛流出了鲜血,随后,鼻子、嘴巴也流出了鲜血。这是荷西的回应吗?那时他已去世去两日。三毛一边用手帕擦荷西眼里的血,一边擦自己眼里的泪,他们的血泪交融在了一起。
这一日,她没有大哭,所有悲哀都随着眼泪默默地流下。很多年后,她和齐豫、潘越云互助出了一张名为《三毛作品第十五号——反应》的唱片,这张唱片由她亲笔写下的十二首歌词组成一张完全的音乐传记,串联起她半生的故事,里面有一首歌词——《现代》,便写了这个悲哀之夜——
日已尽潮水已去
皓月当空的夜晚
交出了
再不能看我
再不能说话的你
同一条手帕
擦你的血拭我的泪
要这样跟你
血泪交融
就这样跟你血泪交融
一如
万年前的初夜
荷西下葬那日,拉芭玛岛秋日将尽,阳光白得刺眼,秋蝉在墓园里叫着悲哀又迢遥的直调。那是三毛人生中最悲哀的一天。这是他们末了的告别。这日之后,三毛便要独自生活在这颗孤独的星球上,再也见不到荷西了。她亲手将钉子一颗一颗钉入他的棺木,每一次落锤,心都被刺得血肉横飞。钉完棺木,再捧一抔黄土撒上去,她没用铁铲,用手捧着一抔抔黄土埋葬了他。当黄土盖满他的棺木时,她溘然失落去理智,她不忍心将他一人留在地下,反悔似的去挖深埋他的黄土,挖到十指流血时又彷佛溘然复苏了一样,说服自己:“放手吧,让他去安息吧……”等黄土堆积成堆,她又扑到他的坟上,痛哭,痛哭……又在心底告别了千次万次:“这一次我真的要走了,荷西……安息……安息啊荷西……”她下定决心似的哭着奔向墓地外的方向,又不舍地狂奔回来,扑倒在荷西的坟前。反反复复,疯了一样。家人、朋友不忍看她这样,把她带回了他们在拉芭玛岛的小公寓里,她的年夜夫朋友给她注射了镇静剂。然而,镇静剂也没有让她睡过去,她依然睁着眼,醒着感想熏染这份痛彻骨髓的悲哀,嘴里梦魇般喊着:“荷西回来……荷西回来……”
这一日,她悲哀得精疲力竭。
三毛在荷西下葬这日哭过、疯过之后,便很少在人前落泪了。那天往后,三毛彷佛把自己罩进了一个透明的罩子里,里面的她看似已与凡人无异,不哭、不闹、安静懂事,乃至可以自己开车出去为亡夫买花、订墓碑。但任何人都近不了身,那种溘然丧夫的痛无人可以真正体会,旁人的安慰只会徒增更多悲哀的感情。她谢绝了很多朋友的陪伴和帮助,不想被打扰,用自己的办法独自吊唁。
她每天很早就起床,一个人上山陪他。每隔几日,便带一把赤色或白色玫瑰,为他坟前的花瓶里换上新鲜的花。然后坐在他的坟前,跟他说话。有时候会一贯坐到天色暗下来,直到守墓老人拿着一把古老的大钥匙,走到她身边低低地抚慰着:“太太,回去吧!
天暗了。”
而荷西走后,每个夜晚都很漫长。就寝也是奢侈的。她每晚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玉轮,升起,又下沉,夜复一夜。那段韶光的影象太深了,已经刻进了生命。那张名为《反应》的唱片里还有一首歌词——《孀》,写的便是那些孀居的夜晚:
许多个夜晚
我,躺在床上
住在一栋海边的屋子里
总是听见晚上的风
带着一种呜咽的呻吟
滑过我的窗口
我坐在那个地方
溘然发觉
我原来已经没有家了
是一个人
每一个晚上
我坐在那里等待黎明
那时候我总以为
这样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到了给荷西修墓碑的时候,她也谢绝找工人帮忙,这是她为荷西在世上做的末了一件事情了,她要独自完成。她乃至不让父母陪同,她已不想让他们太过悲哀。那天一大早,她瞒着父母独自上山。墓碑是她提前找岛上的老木匠打制的,她画了草图请他给做出来,并在上面刻上:
荷西·马利安·葛罗,安息,你的妻子纪念你!
她一个人把墓碑背上山,然后坐在他的坟前,用玄色的笔在十字架上一笔一画仔细地描着荷西的名字,写完,晾干,再一遍一遍涂几层透明的漆。等漆也晾干之后,她用手捧来黄土撒到荷西的坟上,再用手、用尖石头在阁下挖一个小坑,把墓碑栽进去,周围用小石块围住。她不想用铁铲这种快速的工具,她想用一种最古老的形式为亡夫筑起一处永恒的安息之地。
除此之外,她还要处理荷西在人间留下的事情,麻木又机器地去做着一件又一件无奈的琐事:
要去葬仪社结账,去找法医看解剖结果,去警察局交回荷西的身份证和驾驶执照,去海防司令部填写失事经由,去法院申请去世亡证明,去市政府要求墓地模样形状容许,去社会福利局报告去世亡,去打长途电话给马德里总公司要荷西事情条约证明,去打听寄车回大加纳利岛的船期和用度……
时时有认识与不认识的路人经由我,停下来,照着岛上古老的习俗,握住我的双手,亲吻我的额头,喃喃地说几句致哀的措辞然后低头走开。我只是麻木地在道谢,根本没有在听他们,手里捏了一张已经皱得不成样子的白纸,上面写着一些必须去面对的事情。
有一次,走在路上的时候,她忽然停了下来,在大太阳底下呆呆地站立着,她那个转速已经缓慢的大脑在努力弄清楚,为什么自己会在这种情境里。几天之前,荷西还与她以及她的父母一起在岛上过其实实在在的欢快生活,那种真实的欢快氛围还未散去,转眼便已是如此田地。直到路边书店的老板把她拉回到阴凉处,才把她唤醒,那种“狂渴”感再次袭来,她躲进书店大口大口喝着冰水,冰水让她从刚刚的虚妄中复苏过来。
统统不是梦境。
而她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再若何的噩梦都会有醒来的一天。但是,她跌落进一个永无止境的黑洞里,只在不断地下沉……
一个人在悲哀的时候,能哭出来是最好的,可那些日子,她是不哭的,她看上去安静又懂事。刚刚离开大加纳利岛的父母又陪着三毛返回,看着女儿时而撕心裂肺,时而沉默不语,十分心疼,却什么也做不了。即便是父母,此时也进入不了女儿的内心,这种告别的痛楚,无人能与她分担。大概,天下上没有感同身受这件事,每个人的痛楚都只能自己体味。父母也只能站在女儿自我设置的那个保护层表面,看着她哭泣、发呆、强忍疼痛为亡夫处理人间未完的事……他们再若何心疼也插不上手,只能为她供应每天最基本的生活所需——做好饭,求着她吃一点,吃一点吧。等三毛处理完面前紧要的事情,父母便将她带离这个伤心之地,回到了家乡台湾。那时候,家人和朋友们都有种不祥的预感,以为三毛是要自尽的,这种自尽的气息在她沉着的脸庞下暗涌——表面越沉着,暗中越彭湃,所有的人都担心她是不打算一个人活下去了。
实在,直到荷西去世一年多往后,三毛去西班牙看望荷西的家人,她的婆婆为了争取到大加纳利岛的房产,还说出过“你反正是不要活的”这种话。婆婆的心里也一贯认为,三毛是一定要随荷西一起走的了。这里,我实在不忍用“争夺”一词,由于三毛是不争的,她只是不想那么快就把她与荷西的那个家扔掉、卖掉,但公公婆婆却坚持要让她卖掉那屋子。与三毛关系最亲的荷西的妹妹卡门也怪自己的父母太过分,但失落去荷西的三毛已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了,她所留恋的是他们那曾经生活过的家,以是迟迟下不了决心。
被父母带回台湾后,三毛还是呆呆的,反应迟缓。好友琼瑶来与她彻夜长谈,这场漫长的发言只有一个主题——求她一定不要自尽。七个小时往后,两个人都精疲力竭,三毛终于答应了琼瑶:“好,我不自尽。”大家都知道她是看重承诺的人,悬着的心放轻松了一些。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用度酬谢。报料微信关注:ihxdsb,报料QQ:338640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