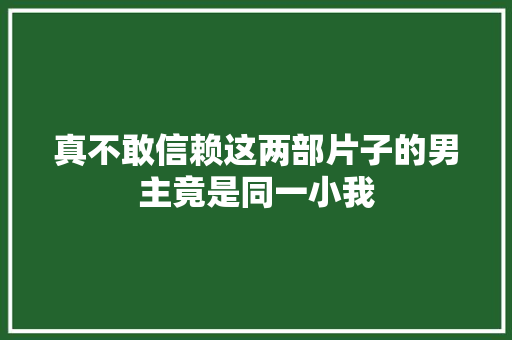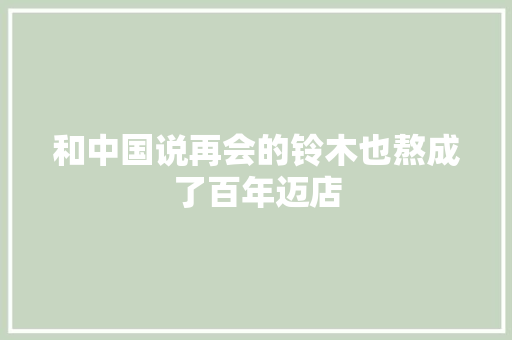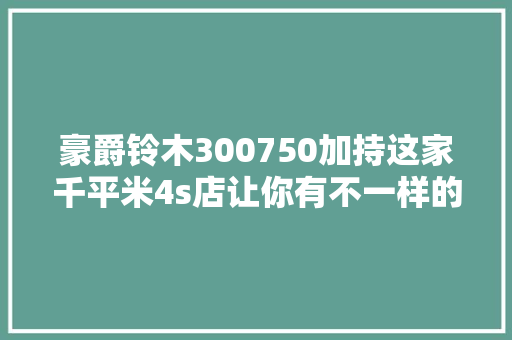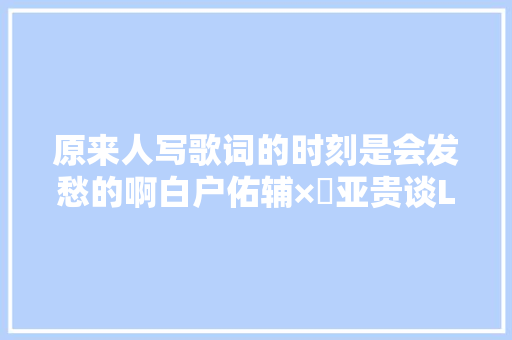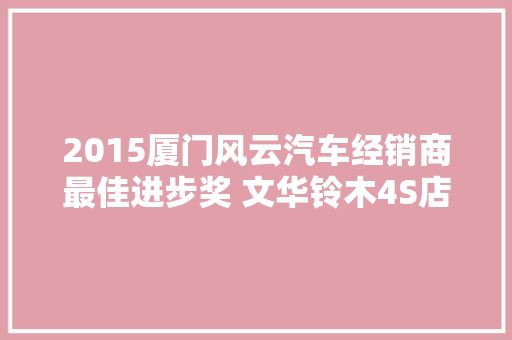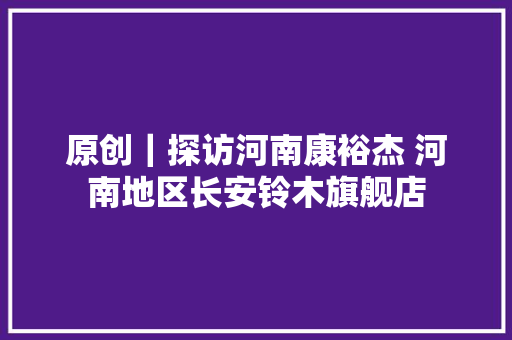吴虹霓 ©Min
文 | 杨罕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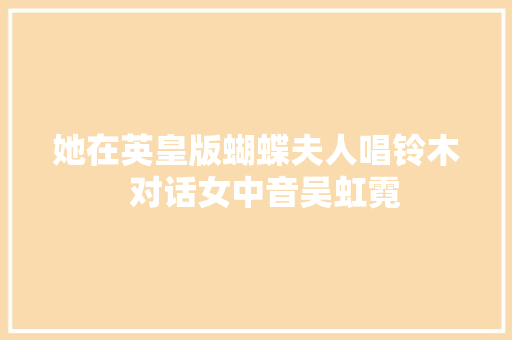
今年3月尾,我在英国皇家歌剧院不雅观看了一场普契尼《蝴蝶夫人》,由立陶宛女高音阿斯米克·格利高里安(Asmik Grigorian)主演蝴蝶夫人巧巧桑,而中国女中音吴虹霓与之互助,饰演女二号铃木。
吴虹霓不仅常在海内的一线音乐厅登台献声,也是如今为数不多的生动于国际主流歌剧舞台上的中国歌者,且曾与英国爱乐乐团、圣切契利亚音乐学院管弦乐团等乐团在音乐会中互助。能在这样一个大制作中饰演这样一个角色,并与当今乐坛一线名伶搭戏且相得益彰,使我对这位1994年出生的青年歌唱家刮目相看。不久后,有幸与吴虹霓在伦敦进行了一次茶话访谈,遂整理记录如下。
杨罕琚:你饰演的铃木非常动听,唱演俱佳。但这该当是你第一次唱铃木吧?
吴虹霓:是的,这是我第一次唱,我该当是历史上年纪最小的铃木了……普遍来说,《蝴蝶夫人》会约请较年长的女中音出演铃木,我这个年纪的女中音一样平常会去唱剧中的凯特。当然,我在接这个角色前就见告剧院,我不要演一个“白头发的老人家”,由于那不像,我要演一个没熟年龄限定、可以自由发挥的铃木。
杨:是的,你是一个很特殊的铃木,从演出到声音。你之前也以演唱莫扎特、罗西尼为主,比如《女民气》里的多罗贝拉或《灰姑娘》里的安吉莉娜。铃木须要的声与形与这些角色都不同,我想或许算是你演过最“重”的角色?
吴:我可能不会用“重”来形容,我会去避免这样判断。铃木确实是一个中低声部偏多的角色,不过对年纪偏大、声音偏低的歌者而言,第三幕的高音也很难唱上去。如果在罗西尼歌剧之后溘然拿到这样一个角色,唱起来当然会有些不舒畅,但只要节制足够的技巧,通过一段韶光的演习就能找到须要的声音位置。一个好歌者须要知道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把声腔调回它该当属于的位置。
杨:你的声音尤其是中低音区确实格外好,有种“sympathetic richness”(温情的浓郁感)。其余,你的演出也相称动人,有生活感,给人以仿佛沉浸个中的自然深切。
吴:这个角色如果演得、唱得不好,或没有碰着一个好制作,很随意马虎仅仅成为“ensemble”(合奏)的一部分,由于她永久都在“做事”巧巧桑。但我理解的铃木不是这样的:在这个制作里,你会创造实在她比所有人在台上的韶光都多,这意味着她险些没有缺席巧巧桑全体的发展过程——从女孩到嫁给平克顿,蝴蝶的身边一贯有铃木像妈妈一样陪着,她们之间超越了雇佣关系而像亲人一样,这种感情非常深厚且特殊。演这个角色必须很投入,每一晚演完我都在后台哭得很厉害……
杨:每一次都如此投入吗?无怪乎你是本制作的亮点之一。我也非常喜好你与饰演蝴蝶夫人的阿斯米克·格利高里安的差错,你和她从声音到演出上都非常合拍。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感想熏染?
吴:这是我第三次和阿斯米克互助了,我们比较有默契。我太理解阿斯米克的性情和她演这部歌剧的觉得了,她塑造的蝴蝶到第三幕时是独特的、带着恍惚的,由于蝴蝶等盼了太久、太久。在细节上我们很懂对方,谁做一个动作,对方就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来衔接。
举个例子,第三幕里在平克顿离开后,铃木答应凯特独自向蝴蝶透露原形并请凯特离开,这时蝴蝶溘然在屋内呼唤铃木。于是“我”(铃木)就崩溃了,我捂着自己的脸、强摁着自己不要哭出来,让蝴蝶不要过来,敦促凯特与沙普莱斯赶紧离开;蝴蝶这时候涌现并催问“平克顿来了吗”,然后溘然向我把手伸来——她须要来自我的希望,但我本能地背过去没有接她的手。这个动作原制作里是没有的,也不是我们刻意设计的;排练的时候导演就对我们说,这个太好了,“Keep!
Keep!
”(保留),我们之间的化学反应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杨:你们自然地进入各自的角色了。
吴:没错。接下来当蝴蝶看到凯特两人的存在时,她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她左顾右盼,泪水在眼眶中打转。蝴蝶接着说了一句“Una Donna”(那个女人),于是我转头了,然后我就从她身边逐步走到自己的垫子前;我的手在抖,但不是那种夸年夜地抖,而是由于想到即将发生的事而自然地战栗。这里我与指挥(Kevin John Edusei)也很有共鸣:他一贯等到我眼泪快要掉下来的时候才奏出那两个让我下跪的和弦。蝴蝶随后说铃木你是我见过最好的人,使我崩溃而开始大哭,我的手揪着自己的衣襟,强忍着不发出抽泣的声音,眼泪却不自觉地往下掉。
我唱完后,蝴蝶让我见告她,平克顿到底回来没有,不是低声地要求,而是带着点凶恶劲儿,“你最好见告我”。你想,她苦苦等待了三年,不承想男人竟带了个别的女人回来:她的内心是有火的,但又难以对我产生发火。以是阿斯米克是抓着我的肩膀而不是扶着,逐步跪下问,“你和我说,他是不是还活着?”我的眼泪打转又不能哭,我更不敢看她,也不知道如何回应,只轻轻地回答一句:“sì(是的)”。
杨:毫无夸年夜造作,但格外简约、真实而动听。
吴:你来的那天我们恰好在录像;那么近的镜头下,那么明显的细节,如果没有真情实感的话,你是骗不了人的。(注:发言间,虹霓向我展示了录像片段,纵然是在镜头的高度聚焦下,她与格利高里安的演出也极为真切而投入。)同样的,如果碰着一些不会演戏的歌剧演员,我们之间没有化学反应,不能造诣对方,那我们的演出就不会像你说的那么“生活化”,这部制作就不可能那么成功。我起初对铃木较低的音域并不是那么舒畅,但和阿斯米克一起排练磨合一段韶光后,我唱起来就不感到阻碍了。这种觉得很难阐明,彷佛便是一个眼神,而不须要多说什么。我们俩第一晚演完就牢牢拥抱了良久,我们都很感谢对方,很愉快能有对方在身边。
杨:我想你们一起互助的过程中一定充满了奇妙的意见意义,每一晚详细的演唱感想熏染也有所不同吧?
吴:是的,我演了六场,场场感想熏染不同,阿斯米克该当也是这样。我们也并不是百分之百按照第一场的办法来,由于每一晚你的能量不同、不雅观众不同,全体剧院的磁场也不同。伟大的音乐总是有无尽的诠释办法,就像是我从上学时便唱罗西尼,同一种技巧、同一部作品,但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人唱都一贯产生着完备不同的感想熏染。这也是我这么热爱这个专业的缘故原由,它永久很新鲜、很故意思。
杨:我可以问问最能在精神上勉励你的歌唱家是谁吗?
吴:很多,我还挺随意马虎欣赏别人的,无论是哪一类型的歌唱家。最近我从阿斯米克身上学到很多,我也很欣赏奥罗佩萨(Lisette Oropesa)唱歌的技巧。但详细来说,也得看他们唱什么曲目,演什么角色。
杨:如果就以铃木而言呢?
吴:没有唉,我想是我自己。我有一个习气,在演一个角色时不太会去借鉴或者说复制别人,我会不雅观察别人的优点,但始终要担保这能成为我的一部分,我不须要感想熏染别人的感想熏染。
我和我的老师安·默里(Ann Murray,爱尔兰裔女中音名家)之间也是如此:我们俩完备不一样,我也不借鉴她,我们也并不一定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她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说:“你要记住,我不是你的老师,我是你的声乐辅导(vocal coach)。你的技能很好,我不须要也没有办法教你发声。”她打了一个比方:一个已经足够好的花瓶,只须要寥寥数笔点睛,不须要做过多改动。
杨:那么她是如何点睛的呢?你从她身上学到了什么?
吴:一方面,安是为我指引方向的人,保护着我让我不要走偏,我根据她的履历和建议来决定我的曲目和职业发展。另一方面,她教会了我授予声音想象力与感情。有一次,我们在谈论莫扎特《女民气》里多拉贝拉的唱段,歌词里有一句“甜蜜的吻”,我脑中想着许多细节处理,但唱得一点都不“甜蜜”。安让我停下,叮嘱我一定要记住自己唱的是什么;实在她并没有见告我该当怎么唱,但记住她的话,当我第二遍再唱到“甜蜜的吻”时,我自然地就笑起来了,也就唱得有传染力了。安教会我真正进入音乐——纵然只是练习一个片段,也必须知道你须要做什么,不然你只是空有一副很多人也有的好嗓子。和安上课,你必须懂得所有唱词的意思,由于你骗不过她,不然她不会给你好神色看。
杨:你认为你未来在音乐中的追求是什么呢?
吴:那天阿斯米克上大师课的时候,有人问她一部作品怎么样才能唱得好,她回答说她从来不会想这个问题——你只能思考怎么样才能唱得“像自己”。天下上已经有过最伟大的录音了,我们可能超过他们吗?不可能。而我们的环境和须要的唱法也不一样了:帕瓦罗蒂老破音,却不影响他成为天下上最伟大的男高音之一;但本日信息这么发达,谁破个音谁就完了。若何唱得好是一个伪命题,由于每个人对“好”的观点都不一样,以是如何唱得“像自己”、有辨识度更主要。当然,你须要对“自己”有复苏的认知,有阅历和履历,你不可能在“唱得很好”的同时不生活化,没有觉得。当然,音乐家始终应做事于音乐,我们的个性不应凌驾于音乐之上。音乐成就我们,可能会为我们带来名气和追捧。但你要知道,不雅观众追捧的不是“你”,而是你饰演的角色、你的舞台形象。成为艺术家就意味着要常常问自己,是否乐意一辈子非常低调地做事于你热爱的音乐、热爱的奇迹。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