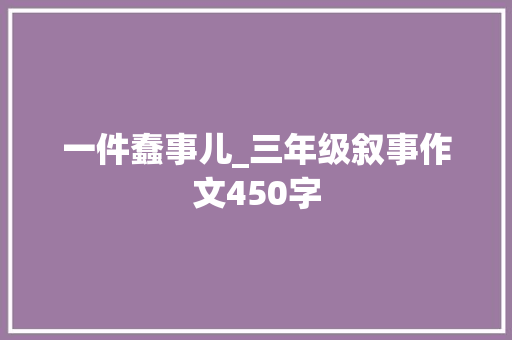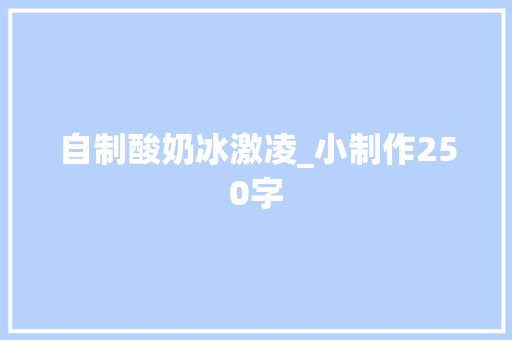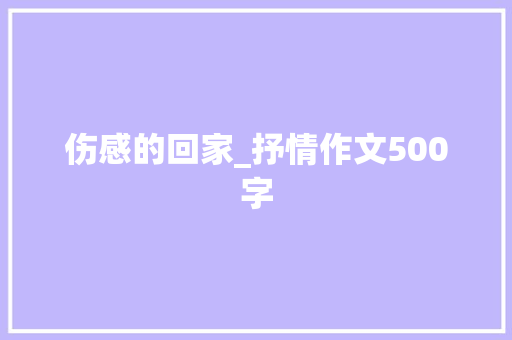姥爷姥姥住在西合营公社南场大队的六道巷,这个巷子呈南北方向,大致有一千多米长,很深,宽约八九米,路面铺了一些石头石子,但却不太规则也不平坦。巷子两侧七扭八拐地大致规整地盖了三四十个大大小小的院子,大的院子里可以种地做场院养畜生,小的院子有土木构造的,也有不少砖瓦构造的。有的院子正上房、东西下房、小南房,从台阶到门窗再到房顶的椽子灰瓦,还很讲究很场面。巷子里住了大致上百户人家。巷子的北端连着西合营的南北向主街道,可以一贯到北边的红旗街上堡下堡。从北边出了巷子向东,则连着五四三二一几道巷子,一贯向南通向粮库汽车站和县第二医院。与西合营的镇中,俗称北中的中学校牢牢相邻。
壶流河滩

六道巷以巷为界,分为两个生产小队,巷东为南场大队五小队,巷西为六小队。姥爷姥姥和二个舅舅及家里人都是六小队的社员。
姥爷名讳守文,粗通文墨,是个木匠,祖传的,手艺在当年的西合营镇上是很有名气的。提起南场的邓家木匠,实在是一批人,姥爷是个中的领头人物。两个舅舅,大舅名有,二舅名前(钱),寄寓了姥爷的深深期望。都从小学艺,自然而然干了木匠这一行。母亲一贯学习很好,后来考上了就在西合营镇上的蔚县师范初师班。
当年,公社成立了社办企业,姥爷入了企业,好象叫公社的木匠社。挣工分,也有补贴,日子还过得还可以。大舅参了军,入了党,退伍回来进了镇上的农机站,仍干木工活,挣上了人为。二舅常去外地干活,北京张家口蔚县城里都干过。
姥爷中上的个子,身体很结实,能吃能干,爱喝浓茶,很少吸烟,稍喝点酒,无不良嗜好。抡奔子、推刨子、拉大锯、盖屋子、修家俱、做门窗,样样手到擒来,请他帮忙的人很多。除了完成木匠社的活计,工余韶光也帮人们修修门窗桌椅等家什,有时还帮人们盖盖屋子,手头还是比较活泛些。
如果生活没有大的变故,一家人的日子还是很幸福的,可偏偏亲姥姥早早地就得了大病,治了良久也回天无力,扔下三个没成年的孩子走了。当年,亲姥姥只有三十来岁,母亲才上小学,两个舅舅更小。姥爷怕孩子们受后娘的治,良久没再续娶,直到母亲和两个舅舅都终年夜了,才迎进了后来的姥姥。后姥姥是外地人,有亲戚在西合营,前夫去世了,无儿无女,也是个可怜的人。
母亲蔚县师范毕业后,却正遇上了什么文革时的候王建议,不给分配事情了,各回各大队,教书挣工分,接管贫下中农的教诲管理。害了一茬子人。
母亲先是当代课老师,后来又转成了民办,磕磕绊绊近二十年,才给落实了政策,转成了正式老师。那时,我已经考上了大专,两个弟弟也都上小学了。
由于母亲陆续在苗寨、横涧、小南关、北洗冀等地方的小学校里,当代课或民办西席,没韶光照顾我,我就从小一贯在姥爷姥姥家。听母亲讲,我的出生地就在西合营南场的六道巷,是租的一户姓孙人家的屋子。姥爷一贯对我很溺爱,从来没有喝斥过我,更舍不得修理我,姥姥也很喜好我,好吃的东西总是给我留着。
壶流落日
小时候,奶娘没有奶,姥姥每天喂我哄我。夜里尿炕了,姥爷都是把干被窝换给我,自己睡到湿处。有时出工到粮库学校医院大礼堂,也带上我,姥爷一边干活一边照看我,阁下的姥爷的徒弟们都说我是姥爷的小尾巴,走哪跟到哪。
母亲自己,或是托人来领我回村落里,我都不愿意回去,还得姥爷耐心地哄我,才随着母亲或熟人回去。为这,母亲还流过眼泪。
记得有一次,母亲托北洗冀学校的刘喜山老师领我回村落里,我正在南场小学的旧庙里玩,姥爷和徒弟们在修学校的坏桌子坏凳子,刘老师和姥爷劝了我好永劫光,才让我坐着刘老师的自行车往回走。刘老师当年也五十多了,很瘦但很精神,车子很旧,老吊链子。我们是绕着镇北边的壶流河大坝,走大路回的北洗冀村落,走到三渠,就遇上了雷阵雨,我们先是躲到了小桥下边避雨,雨还没全停,刘老师就呼唤我赶紧走,不一会,渠里的水就涨了起来。
母亲生二弟时,姥姥来村落里侍候母亲坐月子,我去接姥姥,和姥姥走得也是大坝,走走停停,歇歇再走,从上午挪到了下午。十多里地,我和姥姥走了四五个钟头,母亲都等急了。姥姥是小脚,当年年纪已经六十多了,真是太难为她了。姥姥手很巧,一把小剪子一张小红纸,要啥出啥,为所欲为,邻居家过年办喜事都请姥姥给剪喜庆的剪纸。
南场的人们吃水很困难,都是从东边的泉眼沟里去挑。六道巷最靠西边,到东沟路最远。每天下工后,姥爷都挑着两个水桶去担水,从南场的六道巷到沟里,交往返回足有四五里地,十分地辛劳。巷子里也有几口井,水却是苦的,不能吃。后来,在北边巷口通上了一个自来水管子,吃水才好了些。
西合营公社的小喇叭遍及的不错,每天早上六点多钟就开始广播了,在学大庆学大寨西合努克亲王等等的新闻中,姥爷姥姥就点着石油灯,开始张罗着做早饭了。吃了早饭,才七点多,姥爷就起身出门干活去了。冬天,外边还是黑乎乎的,天又很冷。
有一次,我随着姥爷去粮库玩,姥爷干着活,我在边上玩,二舅也在。安歇时,粮库的管理员让姥爷和二舅他们尝尝食堂的咸鸡蛋,给我也吃了一个,味道还真不孬。刚安歇完,就听人喊,失事了。姥爷和二舅赶紧往外跑,一看,阁下的一个库房不知怎么的,忽然就塌了一个大角,刚才还有说有笑的管理员不知怎么的被压在了下边,姥爷、二舅和人们赶紧上手,急急忙忙地将他从砖土中挖了出来,送到了二医院抢救,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客岁夜礼堂玩,常常去看里边收购的灰的黑的兔子。大礼堂是人们的习气叫法,正规的该当叫副食品公司,里边的各种副食品都堆积在很高很高的库房里。有收购进来的苹果梨桃猪羊鸡兔,也有从外边采购进来的柿饼海带食盐酱醋茶等。外边两个大池子里还有好多的半大乌龟。尤其是库房内的兔子,最怕人来,一有动静就自己乱跑,如伤弓之鸟,有的就每每自己撞到了墙上去世了,正所谓守株待兔,守库也是可以待兔子的。公司留下兔子的皮留着,肉就全体地现卖了。姥爷舅舅都和里边的人很熟,隔三岔五地买些兔子肉回去煮煮解馋。碰破的鸡蛋也时常处理,南场的人们常常去打听打听,买回一些。姥爷有时从镇南边的饭铺买上十几个大红糖馒头,买几斤破口鸡蛋,从食品公司刚刚煮熟的大锅里,买上半斤猪耳朵猪尾巴,回家喝上几盅小酒。姥姥有时也豪迈地呡上一小盅。喷鼻香喷鼻香的猪尾巴是我最爱吃的,姥爷用筷子头沾着喂我的酒却很苦。
该上学了,母亲接我回了村落。放假还是常去姥爷姥姥家。二弟三弟出生后,去镇上赶集,到姥爷姥姥家送东西拿东西就成了我的日常任务了。每次走时,姥爷都十分不放心,每次都送我到下堡到河滩,千叮万叮嘱,又不断打听行人中有没有北洗冀村落里的,让我和村落里的人结伴走。有几次,我就自己拐了弯,在半路的河沟稻田地里抓鱼去了。到半路的海子边沐浴玩水也常去。自然,回到家里免不了让母亲修理一番。
每到年前,除了背上姥爷姥姥给准备的山药蛋粉条和荞面饸饹,姥爷还领我去下堡,买好母亲叮嘱买的猪肉等等年货,再把我送到河边,定好拜年的日子,看着我过了河,姥爷才返回去。来回比我走的路还多。初三四,姥爷早就提前包好了饺子,早早地到河边等我了。正月里,在姥爷姥姥家一住十多天,大多是过了十五才回村落里。
家里的三间正房,也是姥爷带着大舅二舅一间一间地陆续盖起来的。玻璃都是姥爷量好了尺寸,从下堡划好,背着玻璃步辇儿过河送到我们家里安好,又自己返回去的。
上初中了,在村落里念了一学期,姥爷又给我联系好了西合营镇中,让我吃住在姥爷家,在姥爷家门口念完了初中。
初二时,姥姥不幸去逝了,才活了七十二。姥爷很失落落,感情很不好,但还是没有安歇,一贯和二舅一道出工。母亲怕姥爷忧郁坏了,就把姥爷接到了家里。姥爷对母亲包着素馅的油炸糕很喝采,还操持着将我们小房里放着的木料给做个立柜,却不料忽然就晕厥不醒,送到了医院就弗成了。那年我正上高一,姥爷才六十九岁。
献给姥爷姥姥
勤恳的善良的慈爱的姥爷姥姥永久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