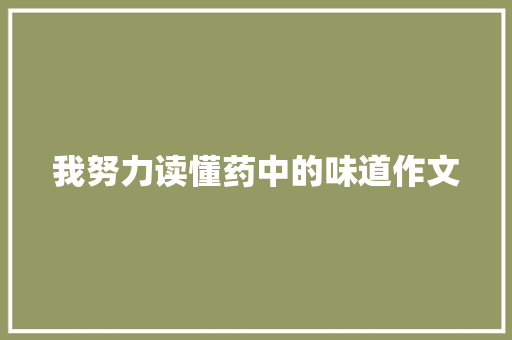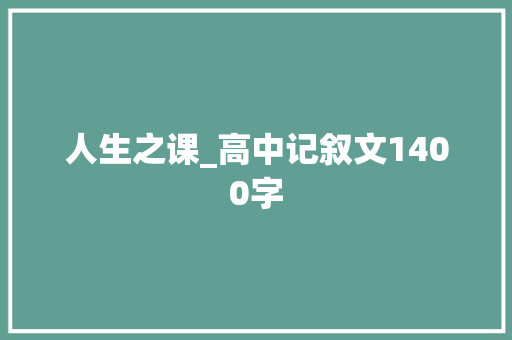要做一棵树
站成永恒

没有悲欢的姿势
一半在尘土里安详
一半在风里飞扬
一半洒落阴凉
一半沐浴阳光
————三毛
当窗外的雨簌簌得下个不停,雨珠顺过清嫰泛新的叶梢落到窗叶发出平仄不起的声响,与祖父在窗内的咳声连成了一片。我知道,又是一个春天来了。看着窗外朦胧的雨景,远处路灯忽明忽暗的橘色光线与温柔漆黑的夜相互缠绵交织在一起。灯下的樟树在雨风的舔舐下瑟瑟地颤抖着,亦如当年故乡家门口的那棵枣树。恍惚间,我似乎听见了窗外樟树沙沙的声响,又或是故乡枣树的喘息。祖父的身子大不如前了,成日里不断地咳嗽与气闷让他近乎无法下床正常走路,可他始终惦记着故乡,故乡里的那五亩地和家门口的那棵枣树。雨似乎更大了,窗外樟树枝叶的婆娑声与风雨扶叶的沙沙喑哑声逐渐的清晰起来,想是祖父也都听见了。祖父被咳声缠绕中思索了一宿。夜已阑珊,东方欲晓,祖父唤来父亲,嘱托他去故乡捎把泥土给他,就捎老家门口那棵枣树下的泥便是了。
那也是一个春雨潺潺的夜晚。家里的人焦急的等待着祖父回来,门楣上已经干涩枯绿的粽叶正沙沙摩挲着,缱绻徜徉出瑟瑟喑哑的声响,像极了雨声,又本是飘进来的雨花滴落在粽叶上的声音。
墙上摩挲过沙沙的声响,沾落的白灰汇聚成了一道流苏,悄无声息的而去。门是在那个时候开的,屋内明晃的灯光朝祖父的身上打去,一袭带雨的风尘尽数的在衣着上抖露了出来,祖父微微的冲我们一笑,眼角却是发红的。不经意间,眸中划过暗淡的伤。
髫年时的我从祖父与父亲的对话中才大抵的知晓。他是去了南边的田沿。我是知道的,那里有棵小枣树,是去年祖母还在的时候,同祖父还有我,三个人一起亲手的植的。
父亲去给祖父捎老家门口枣树根下的泥土时特意找了一个好天气。当他递给祖父那抔泥土时,祖父是带着连声的咳嗽接过的。他似乎早有准备,拿起床头的绢布将塑料袋中的泥土拿出,再裹住,然后搁在了自己的枕边。祖父的动作生硬虚弱却虔诚真挚,我是站在祖父旁边,亲眼看见他做完这些事的。
三月的暖意凝固在了我的指尖,看着那块云纹湖绣的绢布,我才记起这是祖母那块头巾的一部分。听见祖父又是一阵咳嗽,忽觉心酸,想来庚翼的《已向季春帖》中所说,“已向季春,感慕兼伤,情不自任,奈何奈何。”也便是这般滋味了吧。我上前轻柔的拍拍祖父的后背,希望他好些。祖父虚弱的躺在床上,摩挲着枕边用绢布包裹的泥土,眼睛却看着我。他蠕动着干涩发紫的嘴唇,轻轻地对我讲,又或是喃喃自语,“枣儿,枣儿,你阿娘跟我说,枣儿长大了,长大了……”
我的祖母就是在这样流云容容,惠风畅畅的春日里离去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油菜花开满了村边所有的田蔓延到了阡陌。整片整片黄碎的花在蜜蜂的嗡叫中摇曳出灼人的光,渲染出耀眼的明,踊腾出如袅的香。祖母是嗅着这样的味道而阖上眼眸的,我站在一角,胆怯的扯着父亲的衣袂,瞥见祖父跪倒在祖母面前痛声大哭。暮春的晚风泛起,吹白了祖父的发。忽然,我看见祖母紧闭的双眸上滑出了一只没有颜色的蝴蝶来,正当我想要说出来的时候,蝴蝶不见了!可是,我是真的看见了,我看见蝴蝶了。
那也是一个春风拂煦,暖意融融的白日。我同祖父将田沿的那棵枣树移植到了家门口。祖母已经走了一个年头了,这棵枣树与五亩田,是祖母留给祖父唯一的念想。我看着青绿的枣叶上缀着的亮珠不断地在空气里颤颤的抖动着。风拂了过来,嫩叶顿时摆动了开来,亮珠洒满了一地,被贪婪的泥土吞进了嘴中。
沙沙……
忽的,我听见祖母的声音了。她喊着枣儿枣儿。这是在唤我,还是在呼眼前的这棵枣树?我思忖着不敢告诉祖父,却为此得到了惩罚。我的唇上迸溅到了沁凉的水花,带着枣树的清香,味道直钻我的鼻腔。我感到我的心在狂跳,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那一刻,我屏住了呼吸,悄悄的把视线瞥到祖父的身上。
祖父正闭紧眼睛,手拿着枣树根下的一抔泥土默念着什么。难道刚才的声音祖父也听见了,难道祖父在和祖母说话吗?对,一定是这样的。这一瞬间,我感觉到浑身都乏力了,以至于只能大口大口的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从此以后,那棵枣树就在我家门口扎根生长,孟春仲夏,经秋历冬,枣树下是祖父日夜的陪伴与呢喃。日与月悄然的在春意阑珊中消沉,张沁《寄人》中的那句,“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也大抵是此番场景了吧?祖父靠在枣树下自言自语。即使他不说我也是知道的,他在陪祖母说话呢。而我,因为那次没有回应祖母的呼唤,得到了永生的惩罚。再也不能听见祖母的叫唤了。枣树下的泥土上残落着几缀清嫰的枣叶,有时晚风拂叶的声响会飘落到祖父的耳膜里,像一首冗长的清歌终于抵达了时光的尽头。祖父就这样,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对每一位路人微笑,笑容里绽放出岁月里的痕迹。
那也是一个春雨潺潺的夜晚。祖父在弥留之际,日夜摩挲着枕边的那抔泥土,嘴唇不断的嚅嗫着。窗外又传来了熟悉的雨声,风抖动着窗子吱呀作响,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上前,缓缓地搀扶起祖父,学着当年他给祖母喂药的样子,把汤药一勺一勺兜在他嘴边。
“阿爹啊,你莫担心哦,吃了药就好嘚。”
“莫了,莫了。阿爹活不过这个秋天的了。阿爹要去陪你阿娘了。”
祖父说完后,我忽然记起了一些小时候的事情来。譬如,临街的伯公来家里做客时,带给了祖父一张他年轻时与祖母一起在他家门口大枣树旁的合照。泛旧的黑白照上,扎着麻花辫的祖母头上正裹着一块云纹的头巾和寸头的祖父在枣树下温腆羞涩的笑着,正是那块云纹湖绣的。他们就是在伯公家那棵枣树下相识的。是当年伯公和伯婆一起做的媒。而这块云纹的头巾,是祖父送给祖母的信物。
祖母十八岁的时候就进了我们家的门。听叔公说,祖母挽着红袄,撩裙走了三里红妆路。一路上油菜花翻腾起金色的浪花,深绿的叶瓣,还有细小的露珠、流舞的蝴蝶、振翅的燕子,都像是绝美的刺绣镌刻在了祖母的红袄上,日光微醺,染醉了祖母的脸颊,泛起了一抹酡红。是杜樊川七绝里下来的佳人,“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刚进门的祖母就挽起了裤脚,卷起了衣袂陪祖父日复一日的耕耘着那五亩的田地。经春历冬,泥中尘封了一段岁月。岁月里,又裹挟着滴滴汗水,其中是苦涩的艰辛还或是炽热的幸福?时间煮雨,岁月如歌,田亩里开出花来,永不萎地。
祖父咳声随着春意阑珊渐渐更为严重,成日里都能听见他的咳声,可咳声已乏力不再强烈。那个春末,祖父的话多了很多。他说他吃不到今年枣儿结的枣了,他说他想祖母了……祖父依旧不断摩挲着枕边那块裹着泥土的绢布。我看着祖父,眼眶时常湿润,我知道祖父对祖母的那份爱,在日久弥生中已成了身体的一部分,那是抹不去也改不了的。就像是元好问的《摸鱼儿》中所言,“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绵绵的秋风里,枣树的叶瓣与果实相互的摇动示意,清甜的枣香被薄薄的晨露温柔的亲吻在叶尾。我坐在门槛上,望着祖父拿出长杆,那杆子的顶端绑着钩子,随着祖父的挥动。钩子勾住枣树粗壮的枝干,摇动中,那些枣子就好像春天的贵雨一般。嗒嗒的落下,唱起一首岁月的歌谣。
村里的老人走过,讨要着祖父几粒枣子吃,顺带感慨着祖母生前可是喜欢吃枣子了。的确,祖母是爱吃枣子的紧。其中缘由我是不得而知的。我只知道,自打我记事来,祖父从镇上回来,总不忘给祖母捎一份枣子。祖母吃着枣子,坐在门槛上,呲嘴扬唇咧笑着。
以至于祖母病危时,祖父便买了一株枣苗来,与我陪同祖母一起植在了南边的田沿。后来,我在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中读到那么一句,“庭有批把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忽觉一震,几番思量后,竟不能自已。
祖父还是走了。就如同他说的那般,他真的没有活到秋天,是菡萏已绽,木樨未见的夏末走的。临终的时候他嘱咐父亲,不要将他的骨灰放在陵园。他说,让他回家,他是要去陪祖母的。祖母在那头等了他这么多年,这会儿他终于可以去见她了。
今年清明的时候,和家里人一同去扫墓。来到故乡,田野上的春风依旧夹带着油菜花的馨香。家门口的晨光依旧亲吻着枣树的叶瓣。只是故乡老了,岁月的风将墙沿染成了斑驳的黄,时光的尘将屋檐晕成了残损的沙,故乡的人像摇落的枣子,一颗一颗的掉下,然后散落四方。他们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父亲在祖父与祖母的坟前植了一棵小枣树,并把祖父在弥留之际日夜摩挲的那抔泥土埋在了小枣树上。忽想到了庚信《枯树赋》中那句,“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金色的锡箔卷起枫叶般的火花,冲腾出一大股喧嚣的黑烟,我望过去,耳边适时听见了细碎的声响。那是祖母的声音,是的,是的。就和当年的声音是差不多的,这一次我没有在犹豫,扬声,“阿爸,阿爸,是阿娘,阿娘说话了。”
“错了,错了。是你阿爹,你阿爹的声音啊……”
是阿爹的声音吗?我的心不由的颤了颤,眼睛却瞥见一旁染着的锡箔散出的浓烟中朦胧的光泽,顿时呼吸急促了,心也跟着蜷缩,本以为那里会滑出蝴蝶来,可是,在我期待了许久后,等他寂寞的化为黑沫时,它依旧没有生出蝴蝶来。还能怎么办,我只能闭上眼睛,感觉脸颊上有温热的液体悄然滑落,落到了泥土上,再慢慢的渗进去。忽然之间,我好像听到了那些年深的岁月里,枣树拔节生长的声音。也听见,祖父在远方呼喊的声音。
“阿爹。”我猛然的睁开眼睛,鼻尖嗅到了一股清淡的枣香混杂着油菜香。
其实直到现在我还是无法弄明白关于阿爹和阿娘的很多事情。如果你硬是要让我说些来,嘘,我悄悄告诉你,其实我的阿娘是个傻子,以至于阿娘在生命的最后都没有认认真真的唤声我阿爹的名字。她是在文革的时候被打傻的,自打我记事以来,阿娘只会成天坐在家门口的门槛,傻笑着吃着阿爹买来的枣子。而我的家乡在江南的边陲小镇,那里的春天时常下着潺潺的细雨,空气里凝固着淡淡的清香。如果是晴天,兴许还可以看见,岁月更迭留下的记忆。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吹过
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言语
——舒婷
杭州市余杭实验中学高二(6)班陈鹏
以上就是关于且与春同作文的介绍,更多内容请关注美德网高二作文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