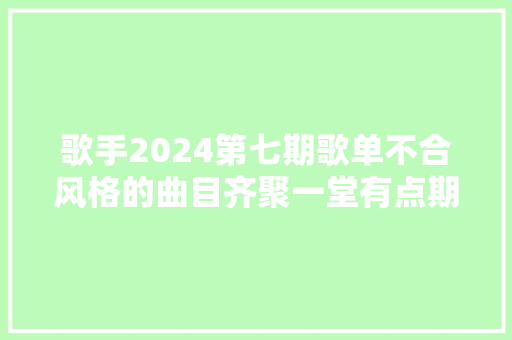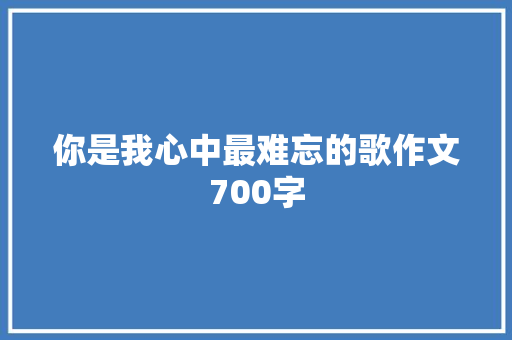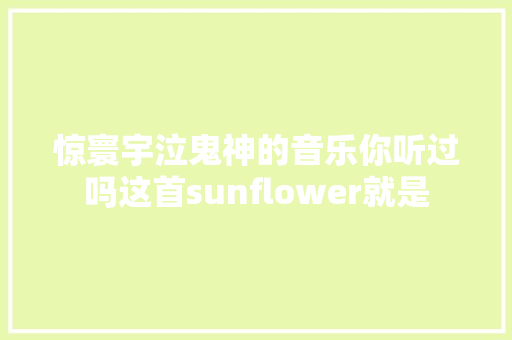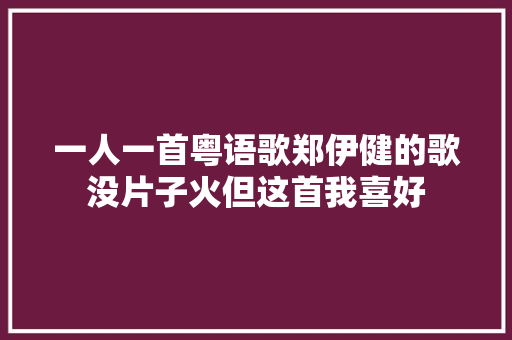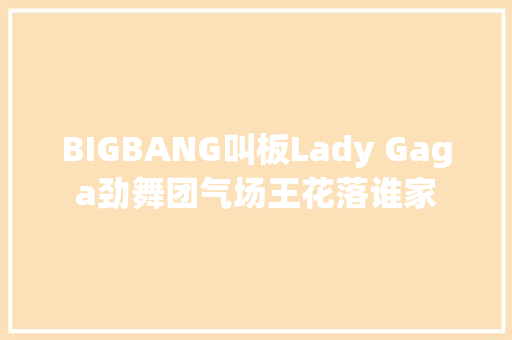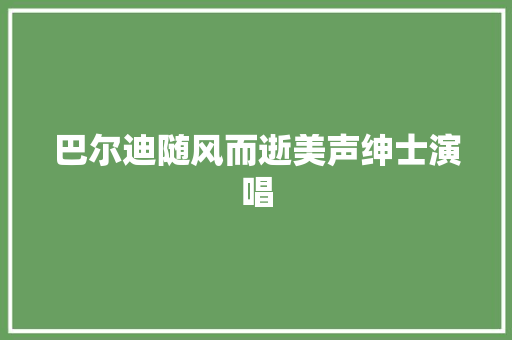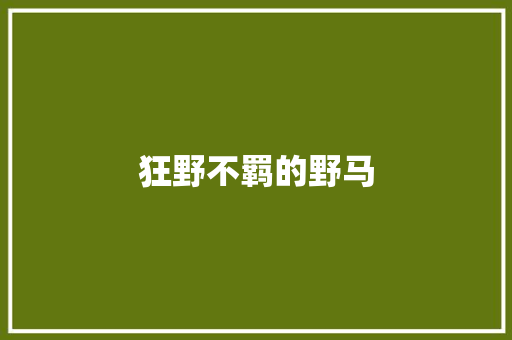最近大火的网剧《隐秘的角落》中,《小白船》这首童谣为夏日增长了一丝凉意。
本来承载着满满童年回顾的歌谣,摇身一变成了“人间阴乐”。反正阿信听到这首歌,是再也回不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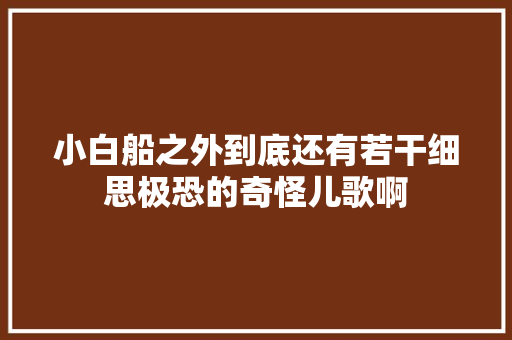
去世亡序曲《小白船》
实在,仔细想来,“毁童年”的童谣还有很多,有些歌词呀,真的是完备不能细想,比如:
拉钩为什么要吊颈?
两只老虎为什么没有耳朵和尾巴?
推理小说里为什么总是响起杀人童谣?
……
以是说,好好的童谣,为什么有的听起来这么胆怯?
《两只老虎》曾经成为了国歌?
《小白船》原来是韩国的一首安魂曲,相信很多人都已经被科普过了。
1924年,韩国作曲家尹克荣的姐夫去世,他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半月》(반달),既是为了记录失落去亲人的寂寥,同时也抒发了当时痛失落国土的痛楚。
但你可能想不到的是,《两只老虎》这首唱起来莫名其妙又朗朗上口的童谣,实在也是舶来品。
它最初的名字是《雅克兄弟》,在法国教会中流传,是一首敦促修士做晨祷的歌谣。
后来,它逐渐演化成了一首戏谑的催起床歌,在欧洲各国蜕变出许多许多版本,比如在德国叫做《马克兄弟》、在英国叫做《约翰兄弟》,但是歌词大意都没有啥变革:你在睡觉吗,XX兄弟?清晨的钟声响了,叮当咚~
放个英文版给大家看看吧:
Are you sleeping? Are you sleeping?
Brother John, Brother John?
Morning bells are ringing. Morning bells are ringing.
Ding, dang, dong. Ding, dang, dong.
那为啥到了中国,这首童谣就画风突变了呢?
这还要从北伐战役提及。当时的爱国人士,根据《雅克兄弟》的曲调重新填词,写成了《国民革命歌》。
1925年2月20日,在《中国军人》创刊号上刊登的《国民革命歌》词曲
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为了鼓舞士气动员民众,这首歌又新增了两段。
于是画风变成了这样:
随着革命不断发展,革命军所经之地民众争相传唱,这首歌曲迅速传遍全国,成为当时中国最盛行的歌曲,也成为了国民政府的暂代国歌。
而我们现在熟知的《两只老虎》的歌词,经由重新填词后从重庆走向全国:重庆兵营里的士兵都喜好唱《两只老虎》,由于蒋经国欣赏这歌词。
1948年出版的《蒋经国论》中就写道:1942年的一个欢迎会,末了的节目是台上台下齐唱“两只老虎”的童谣 。
为啥蒋经国这么偏爱一首童谣?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人生最宝贵的,是童年时期的纯洁诚挚、活泼天真。”
很多回顾录都记载,每当碰着重大问题,他就会唱这首歌勉励民气。
推理作品中为什么大量利用童谣?
暗戳戳地进行隐喻,真的是童谣爱好者的一大乐趣。
这就不能不提到推理故事里的各种“杀人预报”。
比如网综《明星大侦查》里的《胆怯童谣》,暗示了几个小朋友的出生和归宿:
图:《明星大侦查》综艺
柯南戏院版《迷宫的十字路口》中,皮球歌《丸竹夷》是一首帮助孩子记住京都地名的童谣,也是终极的破案线索:
图:《名侦查柯南》戏院版
当然,把“童谣x行刺”的故事发挥到极致的,还要数阿加莎·克里斯蒂。
她最有名的作品《无人生还》,将8个素不相识的人放在了同一个海岛上。一次次命案发生,都印证了别墅中的一首童谣《十个小黑人》:
《无人生还》剧照
在马普尔小姐系列的《黑麦奇案》中,凶手则反其道而行之,想要利用童谣误导侦查的调查方向。阿加莎的舞台剧作品《捕鼠器》,在狂风雪山庄中也涌现了一首童谣《三只瞎老鼠》。
而这三首童谣,都出自同一个——《鹅妈妈童谣》。
提及《鹅妈妈》,想必每个人耳边都会响起几段熟习的旋律。
比如“伦敦桥要倒塌了”(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比如由于小说《杀去世一只知更鸟》而声名大噪的“谁杀去世了知更鸟?”(Who killed CockRobin?)
再比如《爱丽丝漫游瑶池》中的“矮胖墩,坐墙头”(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鹅妈妈童谣》是一部英国民间童谣收录集。这些童谣大部分产生于18世纪,有些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
虽说是童谣,但是里面的很多内容,实在和我们一样平常以为的“童谣”相差甚远。
比如这首:
玛丽小姐真倔强,你的花园长得怎么样?
银色的铃铛、俏丽的贝壳,俊秀的女仆排排坐。
看上去很美好的场景,实在写的是都铎王朝期间的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她以严厉的宗教伤害而被称为“血腥玛丽”。
在这首童谣中,“花园”指的是被伤害的新教徒的墓地,“银铃铛”和“贝壳”是严刑工具的俚语,“少女”则是当时的一种斩首设备。
再比如游戏童谣《转圈圈》:
转圈圈,玫瑰圈,满口袋,花艳艳。
啊嚏!
啊嚏!
我们倒下一片。现在的英国孩子们会手拉手唱着歌转着圈,然后在歌谣结束时一起倒下。然而这首童谣最初的主题,实在是曾经肆虐欧洲的黑去世病。
“玫瑰圈”是黑去世病发后皮肤上涌现的圆的红疹;口袋的花是指当时把花束放在衣服里抵御疾病的习俗;“啊嚏”是受传染的病人末了阶段涌现的类似流感的症状;终极,病人们“倒下一片”。
像这样直指历史事宜和社会问题的童谣还有很多,在中国,哭诉孩子失落去母亲的《小白菜》、“娶了媳妇忘了娘”的《喜鹊尾巴长》一类的童谣也广为流传。
这些让民气有戚戚的童谣,都是对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小白菜》最早记载于荷兰籍传教士在清朝网络童谣结集而成的《童子歌图》
这些童谣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血淋淋的时期影象。也难怪,它们会被推理小说情有独钟了。
在信息不发达的过去,童谣算是一份宝贵的社会记录。而随着人们长久的传唱,这些童谣的原始意义,也逐渐被人们遗忘了,这实在也符合措辞的发展规律。
一点都不“儿童”的童谣,到底为什么存在?
看到这里,很多人就会问了:这些残酷的童谣,明明这么“少儿不宜”,怎么还会被传唱那么久?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散》中认为:“童年”是被建构出来的观点,在专属于儿童的读物广泛传播之前,儿童和成人共享文化语境。
也便是说,最初是没有“童谣”的观点的,成人说了什么,儿童就会接管什么。
在《童谣牛津大辞典》中,作者就肯定地说:
“鹅妈妈童谣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首先为孩子准备的,事实上,很多是成人的代码。”
那些广泛流传的童谣,很多都是由民谣或者民间故事演化而来的。它们在最初并不是专门讲给孩子听的,相反,它们是把成人的歌谣唱给了孩子听,由于只有成人才懂得其内在含义。
比如我们小时候定下约定时都会念叨的“拉钩吊颈”,在英文里也有对应的“Pinky Swear”,但实在它们都源于日本的童谣:
指きり
切手指(我们立下的是切掉了小手指般武断的誓言)
げんまん
(谁假如违背誓言)挨一万次拳头
嘘ついたら針千本飲ま~す
吞一千根针
指切った
手指已经割断了(誓言订立了)
中文中的“吊颈”,也有很多种理解,有人认为它对应了日文中挨拳头、吞针的残酷后果,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吊钱”的意思,拉钩就像把钱串起来一样说定了、不改了。
既然很多童谣是“成人的代码”,为什么很多童谣又因此孩子的口吻、用着美好的意向来映射现实呢?
一个缘故原由在于,“童言无忌”,人们常日不会对孩子的话负责,因此童谣中的隐喻可以让人光亮磊落地批驳时势。
而在另一方面,尤其在中国,儿童又总是会与通灵故事产生联系。不知从何而起的童谣,每每被附加某些“天启”的政治含义。
比如东汉末年的长安童谣“千里草,何青青。旬日卜,不得生”,就被认为是对董卓政权将被颠覆的预言。
“千里草、旬日卜”合起来便是“董卓”二字
在政治意味之外,这些饱含隐喻的歌谣,用童真的视角来处理极其残酷的社会问题,也暗含着诗歌的美学。
它们反响了成人作家的思想,表示的是作者对现实的关怀和反思,但是用孩子的口吻说出来,就别有一层意味。
就像米兰·昆德拉在其《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中写道:
“唯一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孩子提出的,只有最天真的问题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
不过,也不用太担心这些“胆怯童谣”会不会影响到孩子的生理发展,童谣的胆怯意味早就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步磨灭了。
而本日所创作出来的童谣,更多是承担了对孩子们的教诲意义,因此在创作过程中也应该更加谨严和严谨,符合孩子的发展规律。
毕竟,挖掘幽美童谣背后的残酷故事,是我们这些八卦的大人才爱干的事呀
参考文献:
[1]《<国民革命歌>:大革命期间的最强音》,廖利明,中国档案报
[2]《<两只老虎>竟然差点成了国歌?| 壹读精选》,那一座城
[3]《那一年,蒋经国教我们唱<两只老虎>》,马拉,重庆晨报
[4]《胆怯童谣,远不止一首<小白船>》,恺哥,新周刊
[5]《隐喻叙事与胆怯艺术———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鹅妈妈童谣》,赵跃,民俗研究
[6]《<小白船>怎么就成人间阴乐了》,网易上流
印刷术和电视如何改变成人和儿童的界线?尼尔·波兹曼“媒介批评三部曲”,带你看到技能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