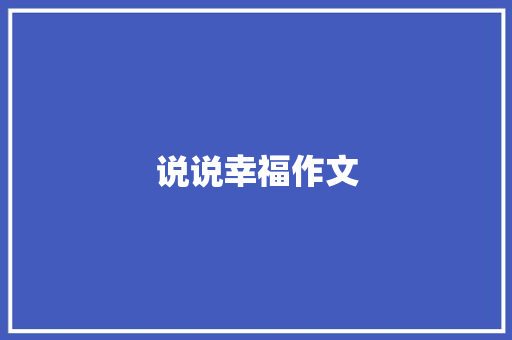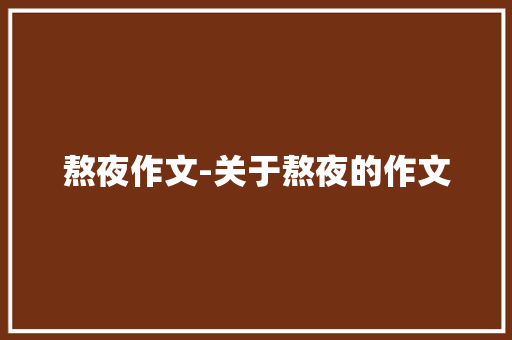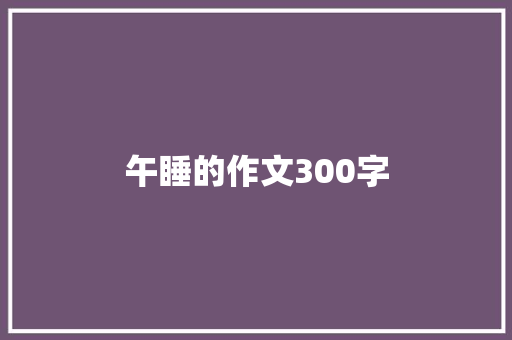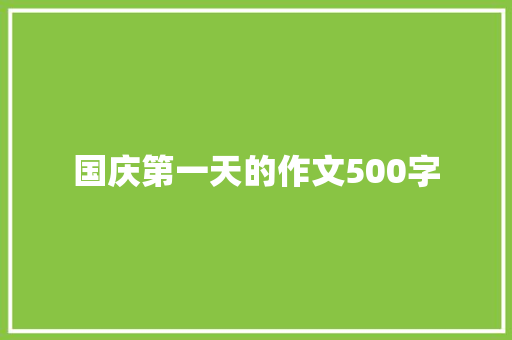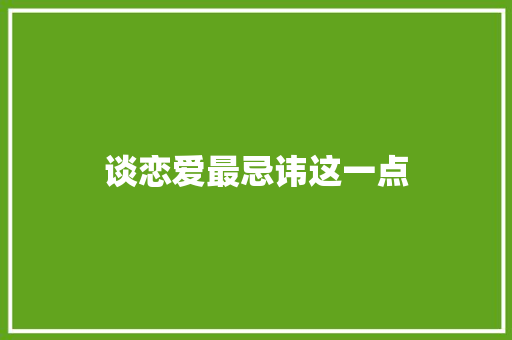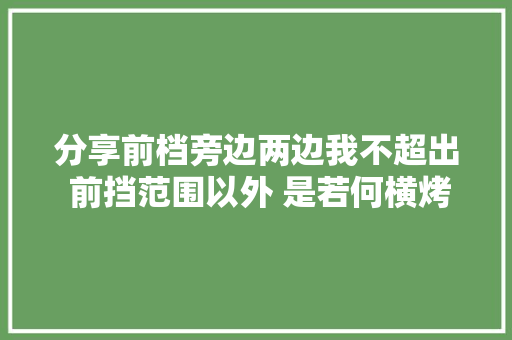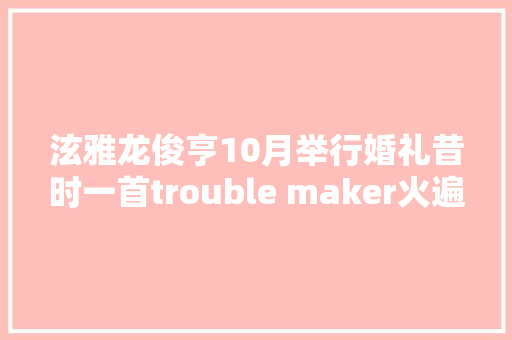采访整理:叶三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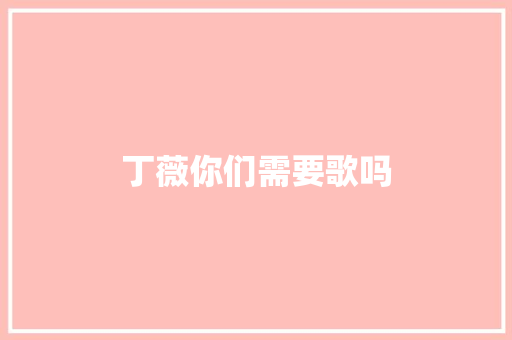
我的忧患意识是从初三开始的。
那时候,我是溘然对自己的专业产生了焦虑。我学的是二胡,这个专业并不是我选的,是我父亲给我选的。实在二胡拉到附中毕业足矣——附小附中就九年了,再加上考学之前那三年,我已经拉了十二年了。这十二年里曲子反复拉,《二泉映月》最少拉三遍,当然老师会说每一次会有不同的境界,但是……民乐界有点像民歌界,好坏明眼人可能看得出个一二,生手是看不出来的。而且二胡这个东西,拉个几年往后技能也就这样了,不像钢琴,弹李斯特和弹肖邦的还有个差异。以是,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大概是什么景象,四十多岁的时候是什么景象,我都能想象得到。
当时我以为,以我的性情想留校是不可能的——第一,不但不爱拍马屁还每天说坏话;第二,但凡须要一点潜规则什么切实其实定第一个喊出来。以是谁会重用我?我当时就看到了未来的景象,以为不能绑去世在二胡这棵树上,得想辙。
但我那个时候只是表示出对自己对未来的焦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招,由于我并没有什么选择。很幸运的是,高一开学之后学校就有了新的规定,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如果专业跟文化课达到一定的水准线之上,可以报考选修作曲专业。我高兴得要去世,就报了,也考上了,我自己还挺得意的。
这是我自己作出的第一个人生决定,之前都是我父亲替我决定。可以说,我的焦虑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这么看,我是个挺奇怪的人。一贯到当了歌手,实在大部分人就勾留在那个阶段了,高高兴兴唱歌。我是永久都会想,万一有不好的时候怎么办? 如果没有人须要你去唱歌,那个时候你能生存吗?我常常会问我自己。我想我至少得可以当个厨师、当个司机什么的。
虽然故意识地学了作曲, 但我真不是故意识地变成了一个专业词曲作者。
1996年出完《断翅的蝴蝶》,我跟“大地唱片”闹解约没闹成,我就自己把自己给冷藏了。
那时候,唱片公司既是公司又是我们的经纪人。我的唱片约到1997年,艺人约到1998年,在合约期间我决定啥都不干,但约没满我也没法签别的约。这就意味着,这两年我没有收入来源了,而我刚刚大学毕业来北京,一下就懵了。怎么养活自己,怎么交房租,怎么用饭?我就开始冒死写歌。
我开始给人打电话:“你们须要歌吗?”这在我的人生里,以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以前以为绝不能求人。那个时候开了第一个先例,我就开始给各种人打电话,而且说服自己:我也没求人,我只是见告他这个讯息“我这儿有歌”,我只是给自己创造一次让他们听的机会。这么着,1996年到1998年我写了很多很多歌,同时也给自己写了很多歌——怀着那种与唱片公司不能沟通的愤慨。
那两年作为一个词曲作者,我是不管数量还是质量都开始上去了,以是到1998年签BMG的时候,我的歌都准备好了,属于“来吧,让我赶紧干吧”。
那两年,可能焦虑的便是钱,由于那时候我居然买屋子了。实在也是被周围这几个人——孙楠、潘劲东他们带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银行分期付款这一回事,买那个屋子是先交七万,每月交七千,一共交七年,是开拓商搞的花样。结果阁下这几位说“多便宜啊我们买吧”,大家稀里糊涂跟在后面买,买完我就后悔了,每个月交七千块钱挺费劲的,还得装修。那时候我写歌就想,这首是马桶钱,这首是为了那个浴缸……但是我以为挺好玩,人实在是潜力是很大的, 人到触底之前都会有一个反弹的、自我保护的动作。
那时候我给很多人写歌。1997年,我签了刘德华的New Melody,1998年签了BMG。刚开始,一首词曲两千块钱,后来随着市场价和有名度上升,逐步变成四五千,又到八千或一万,但那也差不多便是顶峰了。这个行业的壮盛期间就在1998到2000年,后面就开始走下坡路。
2001年,我差一点上了春晚。总导演王冼平找到我,极力地想把我那首《冬天来了》弄到春晚上去。她说这是好作品,很想推举给全国公民,当然我也很乐意。为符合春晚的气氛,还给它改了个名字叫“春又来了”, 词也给改了。但是词决定不了音乐的实质,都已经改成那样了,大家还是以为这个歌太悲。末了到了年二十九的一场终审,还是没过。
那时候很多晚会也会找我,以为“你不是主流歌手吗?”由于我在大唱片公司,人家就会把我划为主流歌手,可正好是主流里的这些人听我的歌,以为“这个东西太不主流了,你是另类的”。但是,对付那些真正的地下摇滚音乐人来讲,我肯定是主流。以是我的问题是,我在盛行乐行业里面跟谁都不是一拨儿的,乃至从音乐的类型上来说也是,我跟大家都不太一样。
到这里,我人生的第二个焦虑是给办理了。但是我一贯都是一个有忧患意识的人,我从来不会说我对现状已经知足了。
我深知音乐这个行业是没有保障的。它是不以履历为优点的行业,也不以专业性为标准。尤其是当歌手,年纪大越大就越没有上风。制作人跟词曲作者稍好一点,但实际上也有很大的危急感。由于这始终是年轻人的行业,如果写出来的东西不再是年轻人所喜好的,不能为年轻人代言的话,你就要被淘汰了。盛行音乐的词从来没有什么规定说一定要怎么样,可能你很朴实,像小学生作文一样,也能打动人——现在很多歌词便是那个水平,但是跟普通人更靠近,以是大家喜好。既然没有标准,便是分分钟有可能会丢饭碗,不是受你掌握的。
2
我一贯认为我便是个搞音乐的,没有“艺人”这个观点。
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手,出道的时候没有助理没有扮装师,都是自己拎着包走的,自己有啥穿啥。《断翅的蝴蝶》MV的导演是李少红的丈夫曾念平,拍的时候他问我:“你没带衣服来?”我说“我就这条连衣裙”,而且我一个大学生也没什么衣服。他说弗成啊,还得来几件,“我让少红给你找几件”。以是那个MV里面好几件衣服是李少红的。
后来开始有时尚行业了,还有服装编辑,专门给你打理服装。曾有经纪公司卖力人跟我说,我以为你这个底子不错,你看你这个脸,颧骨要调一调,骨头削一削,就好看了。我说我不要改, 本来啥样就啥样,我父母给我生的样子,我改了他们不认识我了。
逐步地,我意识到盛行乐这个行业的各种不靠谱,就又开始焦虑,从2000年开始,我有了写影视配乐这个意识。
刚开始挺困难,我是个女歌手,发过专辑的,导演们大多数是男的,他们只要一听说你是女歌手就会有种不信赖感,“你一个女歌手怎么可能写我们这个戏呢?我们是男人戏噢”。他会疑惑我的能力,或多或少,影视界还是以男人为主导的,以是女性在里面想要得到一点公正的机会也不是太随意马虎。
我从小就有个毛病是老哀求公正,有的时候会愤愤不平,在街上跟人理论什么的,现在逐步想,的确这天下上没有公正,以是大家才求公正。
2002年,有一部电影找我,他们想用《冬天来了》这首歌。那部电影叫《天下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改编自张洁的小说,是马晓颖(后改名马俪文)的处女作。我去跟导演聊,她说,你是学作曲的?我说对啊。“要不你把配乐也给写了吧?”我说,真的吗?我可没写过。她说对啊,我也是第一次拍电影——就这样,算是第一次考试测验,稀里糊涂的。当时我只有感想熏染,没什么履历也没有什么技法,肯定好多都是不对的,但是音乐便是这样,没什么可不可笑,你就听,你以为动听就动听,你以为好听就好听。那个电影还不错,算是考试测验了一把,让我知道做电影音乐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以为我得接着学东西,必须要磨炼磨炼,多练到一些本事才能做的长久。我就开始研讨电脑,自学,跟编曲的朋友们请教。当时我有个本子,有了问题就想,本日给谁打电话?——我给XX打,问完这个问题,赶紧记到本子上。一下子又涌现一个问题,弗成,不能再给XX打了,看看XX在不在给他打一个……就这样轮着打电话,三四个音乐人朋友,最多一天给人家打一个电话,别烦着人家。就这样张三问一句李四问一句,吃百家饭那样的,摸索着把电脑程序这块儿搞定了,然后就可以自己编一些小样。
2004年我出专辑的时候,实在已经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编的,已经开始有了这方面的技能。之后真正开始影视剧配乐工作,差不多是一年一部。所幸,我还有一个差错林朝阳,他是男性,又有非常好的音乐教诲背景,单单我一个人,后来也没有问题,但一开始会比较难。2008年,林朝阳(盐哥)跟我迅速地变成一个组合,就很有说服力了。
2008到2011年这段韶光,跟我们互助的几位导演都不是请大牌明星的那种,可以平衡好制作的关系,大家互助得很愉快。差不多从2008《人间正道是沧桑》开播到2014年,配乐变成了我的奇迹主线, 那六年过得很辛劳,也很稳定。到2015年,配乐作品是一年4部旁边。
这两年影视剧更热,尤其是电视剧,但反而乐意在音乐上费钱的少,越是热钱多越是想赚快钱,投资完备失落调,演员身上花掉90%的钱,10%用来制作,那还做什么音乐?弄点罐头音乐得了,已经没有钱了。以是这两年的配乐作品我们选择得更为谨慎。
我认为写配乐很练人,是很好的事情。它是一种作品,但它的来源、目的都不是我的,是要为导演、为全体电影做事的,而且电影已经拍成什么样,我掌握不了。可能对付很多人来说,做音乐最空想的状态也便是这样了——在这个时期,有一份稳定的事情,收入还不错。但是,我以为一个搞艺术的人必须要有自己的作品,纵然写这么多配乐,它毕竟是集体创作的一部分。
3
2005年,我在湖南经视“明星学院”节目第一次当了评委。2006年,易骅 请我去超级女生广州赛区当评委,我纠结了一下。当时那个节目太火了,我以为娱乐性太强,跟我的身份不符,也以为跟歌迷心目中我的形象不吻合,彷佛有一点不太搭。后来盐哥劝我,该当从积极面去想,一个这么火的节目,每周直播,你会有大量的韶光在电视上揭橥你对付音乐的意见,这有什么不好?我以为有道理。
事实证明,那几年的娱乐节目, 评委这部分还是挺看重专业性的。当时广州赛区的评委是我、袁惟仁和王东。我既是歌手又是制作人词曲作者,袁惟仁也是词曲作者制作人,王东是电台DJ,大家成为了朋友,跟导演易骅合营得也特殊好。
那几年,每星期跟打仗一样,真挺故意思的。那时候是真正的直播,而且还有实时投票。脑筋一刻一直地在想,一下子说什么,怎么组织措辞。我们在广告韶光内快速地商量,还要跟票选做一些抗争,有时候票选人不是我们想要的人,怎么办?这轮先把韩真真送上去,不要让她被票选弄下来,下一轮把尚雯捷送上去,由于她是票选很低的,刘力扬不用送,她票选很高……搞这些挺故意思。那几年我以为做评委还有好处,便是会打仗到各式各样的人,听到各式各样的歌——我也不怎么去卡拉OK,盛行什么歌我做几次评委就都知道了 。
现在的选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是直播,是录播,找评委看重的只是你的有名度能给节目带来话题性就可以。现在的选秀比赛有剧本有编剧,有人设 。我之前做过一次节目,导演说你作为这个节目里的女评委,我们希望你感性一点,“你能不能动个情,哭一下?”我说感激,能不能把我当男的呢,我泪点比男的还高,真的很难哭的。
我干不出这事。我不愿意改变自己,为了成功什么都干这种事情我干不出来。
我现在很少看这些节目,除非朋友圈转得沸沸扬扬觉得不看就没话题了。说实在话,也差不多,歌还是那些歌,我最不愿意看的便是唱来唱去还是那些歌,都是百度前一百名。可能也就这几年轻微多加了几首李志赵雷等民谣歌手的作品。
我以为李志挺好的,他在音乐上有追求。而且他把歌迷调教得那么好。
认识李志也挺有趣的。2015年11月,他在工体演出,我想去理解一下给他做调音器材的团队,就去看了一下。之前一首他的歌我都没听过。之后我发单曲《流浪者之歌》,朋友转来转去,李志就托人联系我,请我当那年他跨年演唱会的高朋。
我以为李老师有一种人格魅力,他很知道怎么跟歌迷相处,这一点我到现在都没学会。我一站在台上总是不好意思,唱歌的时候没有问题,一旦说咱们聊点什么我就不知所措。我只有跟我熟习的人才能聊得很自然,歌迷你说熟吗,也挺熟,实际上又不认识,我就会在自己的尴尬症里面永久很尴尬,以为该说话但是说多了以为不对,不说话以为不礼貌。我说到底在音乐学院象牙塔里终年夜的,练就了一身清高的本领,音乐学院的教诲是上台便是好好演出乐器,没有跟不雅观众互换这一回事,弹完琴不雅观众以为好鼓掌你就鞠个躬,这事就结束了。但是李老师在台上,跟他的歌迷就像跟自己家兄弟一样。
我参加过那么多年选秀,看过很多群体性歌迷的形象,太知道粉丝怎么聚拢,聚拢往后什么状态,从玉米到后面的各种,都能看出来这些歌迷的状态,但是李志的歌迷跟这些选秀艺人的歌迷状态完备不一样。他们不举灯牌也不尖叫,跟军队一样齐刷刷的,而且很故意思, 他们不是一样平常的那种偶像崇拜,他们跟作品的联系性很强,我以为李志如果开演唱会,他从头到尾不唱,歌迷都可以唱完,这点真的很牛。
我实在始终还是勾留在根深蒂固的音乐学院的教诲中,认为音乐是用来欣赏的, 从来没打算让人参与,现在正好这个时期,大家以为一定要能参与的音乐才是好的歌,我不太理解这件事。
我想要得到的最高境界,是像Queen乐队那样的大合唱。像《波希米亚狂想曲》这样的歌如果都能大合唱,我认为不是歌大略,而是歌迷练了好多遍,实在我的歌如果练好多遍也可以,只不过不可能像有一些民谣那么大略,唱两三遍看着词就会,我的旋律写法跟他们不太一样。
我的很多审美意识勾留在上个世纪,习气了这种办法。像平克弗洛伊德那样的状态我以为是最最空想的,但是现在很难有这个气氛有人合营——但在那个年代,大家是合营的。那时候大家不认为我一定要能唱你的歌你才是好歌手。像迈克尔杰克逊很多歌怎么随着唱?最多感想熏染一下,可能一两首可以唱,绝不是每首歌。那个年代的歌都很难唱,那个时候我们崇尚某种专业性和精神性的东西,认为高过于我们的是好的,但是现在这个时期,彷佛大家认为你跟我是不相上下, 诙谐亲切的状态彷佛才是更好的。
在上个世纪,哲学性的东西大概大家是须要的。现在大家以为我已经很累了,你别来说教了行吗, 听音乐不便是消遣嘛,你干嘛搞那么多花样,烦不烦?现在人没有耐心,所有的东西都很快速,歌听起来随意马虎,关掉也随意马虎,不像从前,听个磁带想听到哪首歌,还得倒倒带子的。事情便是这样,得来随意马虎扔掉也随意马虎。这些征象我能看得清楚,但还是固执,不想因此改变自己。
我最近一次焦虑,该当便是没发专辑这几年里。我不知道这个专辑还要不要发,发了还有没故意义……到真的发了,一下子心情惬意,一通百通。
至于人生存划,我以为可能不会有什么新内容了。我没有很大的野心,还是希望能保持自己的创作力,再去做几张故意思的专辑,就这样——由于我以为,实在年纪越大,这部分越要小心。我虽然是搞音乐的,但我把自己分成了好几个角色去判断,我认为歌手是歌手,作者是作者,制作人是制作人,配乐是配乐,每一样我都希望能达到这个行业里最专业和最好的标准,不因此多取胜,而是你真的在每一个你从事的职业范畴里边都是最好的,得往那个方向去奔。
实在我有很多面,能写很多不同的东西,也能唱不同的东西,常常大家想把我定性成某个面的时候,我又转了个身。今年我出这张《松绑》的时候,好多人听完说丁薇你变了,我说我没有。这张唱片的风格从很早开始就有延续性,我早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实验了,熟习我的唱片全貌的人再去听我现在这张唱片,不会以为很奇怪。但是很多人对我的印象还是《女孩儿与四重奏》,或者《再见我爱你》。
可能在音乐上我太喜好玩花样了,这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是不好的。我并不抵触商业,谁跟钱都没仇,但我也没有赚很多的希望,只要够花就行。相对来说,我比较幸运的是没有转业,或者必须干别的事情来养活自己——我还在音乐这个行业里,能一贯做音乐很愉快。
—— 完 ——
题图拍照:黄京
本月的值班主编是谢丁,有事请与他联系:xieding@jiemian.com。来不及看投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