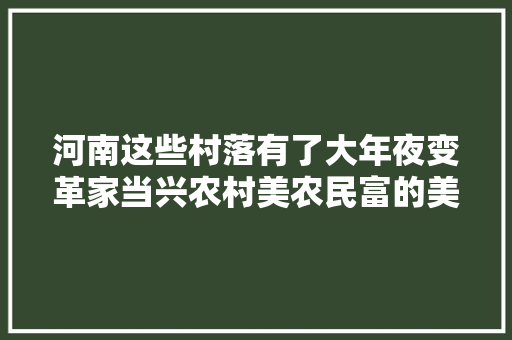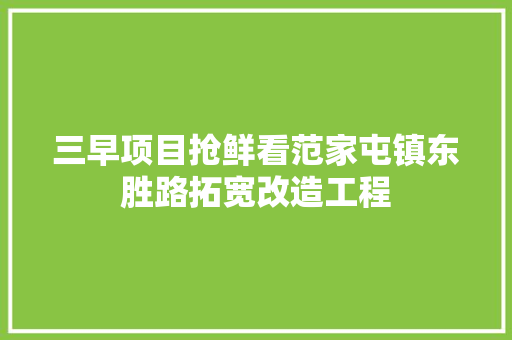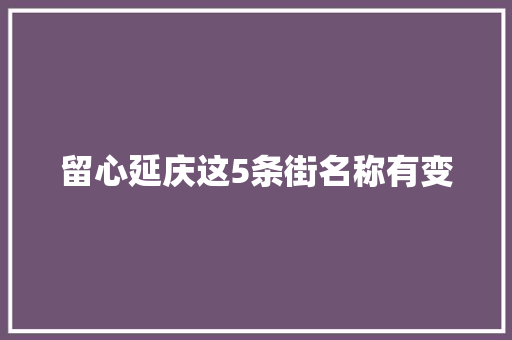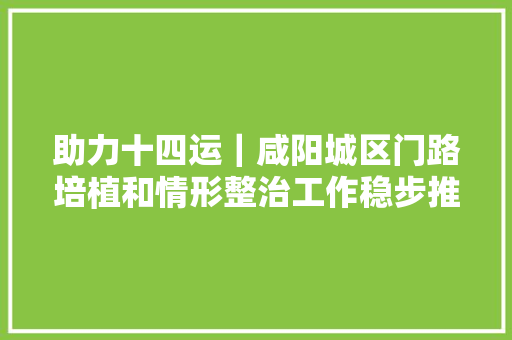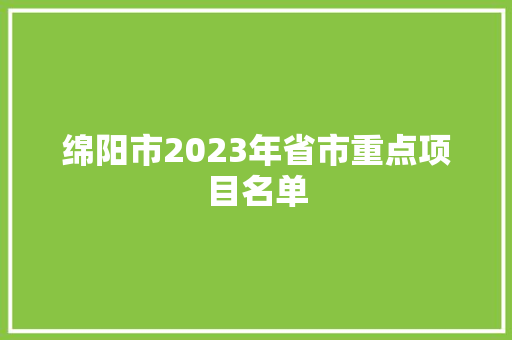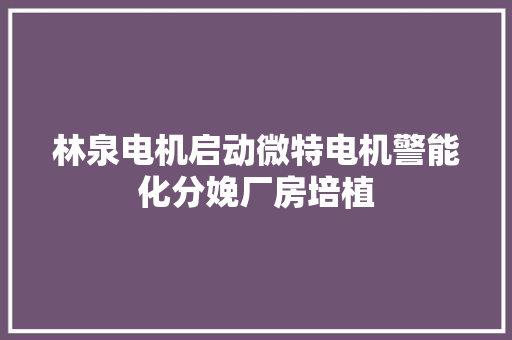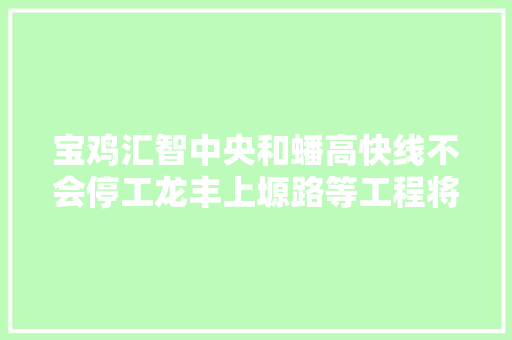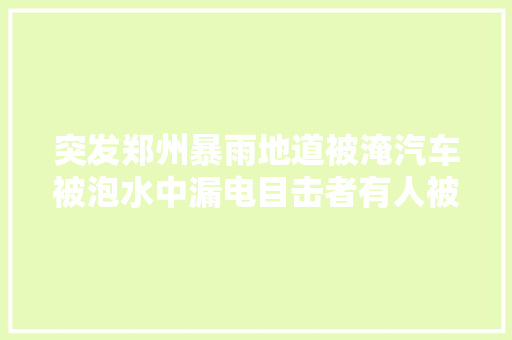6月23日,实地探访了延庆赛区生态修复情形。据北京市重大项目办表露,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生态修复事情将于本月尾全面完成,下一步将进入美化和精修阶段。这也是北京冬奥会培植周期最长的一项工程,在过去的6年内,他们共完成了214万平方米的生态修复。
延庆冬奥村落与山地新闻中央背靠青山。新京报 王贵彬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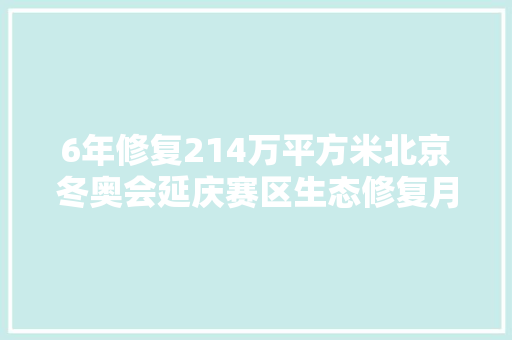
延庆赛区生态修复事情本月尾全面完成
从市区出发,沿着京礼高速一起向西北行驶,驶出海陀收费站后,顺着山坡向上望去便能看到已经落成的冬奥延庆赛区。未来,这里将举行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等赛事的比拼。
伴随着场馆和干系配套举动步伐相继落成,在海陀山谷内,一场为期六年的生态修复工程也附近尾声。专家和培植者的共同目标是——将因场馆和根本举动步伐培植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如今,七条覆满绿色植被的雪道从山顶倾泻而下,与周边林草融为一体;海拔2198米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央出发平台周边、高山草甸,花草树木依旧茂盛;延庆冬奥村落与山地新闻中央背靠青山,点点野花点缀在绿茵如毯的山坡上。
突出“绿色办奥”,把培植奥运场馆同促进生态文明培植相结合,努力让运动场馆和市政配套举动步伐同小海陀山的自然景不雅观和谐相融……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副主任于德泉见告,这些都是延庆赛区场馆培植事情的主要原则。
延庆赛区培植条件艰巨,生态修复事情的难度不亚于新建场馆工程。该项事情于2015年开始,至今历时6年,成为北京冬奥会培植周期最长的一项工程。
市重大办表露的信息显示,延庆赛区以七条雪道和市政道路周边的边坡为紧张修复区域,共计完成修复面积214万平方米。按照操持,生态修复事情将于本月尾全面完成。
滑雪赛道的结束区,目前已基本实现植被覆盖。新京报 王贵彬 摄
动“第一锹土”前,先给动植物定制“保护方案”
生态修复有一个原则,便是一定要用原生或本地的乡土植物,以确保坚持当地生态资源的稳定性。为保护海陀山的自然生态,2016年,在动“第一锹土”之前,干系林业、水土、生态专家先期开展了“生态环境本底调查”,这是决定冬奥延庆赛区能否实现生态修复的关键。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张志翔便是个中一员。2016年,北京林业大学120多人的团队正式进驻保护区进行摸底调查。“在培植前,小海陀上山险些没有可供攀登的路,到处都是茂密的植被,为了尽可能充分地网络动植物样本情形,我徒步爬上小海陀山顶好几次。”张志翔见告,当时他们每次都要绕道河北,从小海陀山坡度稍缓的另一端登顶。
在张志翔看来,生态环境本底调查是极其主要且具有前瞻性的事情,基于网络到的数据,他们制订了详细的保护方案,辅导施工方科学培植。
工程培植开始前,培植单位对赛区内受到扰动的植物进行了“定制”的保护方案。对付生态环境好、受施工扰动小的植物进行原地保护,使之成为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付施工过程中无法避让的树木,培植者制订了详细的“移民方案”。
2017年4月,延庆区张山营镇上板泉村落8号地作为迁地保护基地,迎来了第一批“植物移民”,同时还移植了762棵树木至新建筑的冬奥森林公园。
截至目前,赛区内原地保护树木共计313株,迁地移植乔木24272株,建成迁地保护基地近300亩,成活率约99%;近地移植灌草11027株。同时,依据前期本底调查所记录的“台账”,共栽种5.75万株乔木、30.4万株灌木,进行了214万平米草灌播种。
对付赛区内的动物,他们结合施工培植形成的自然空间,开展动物通道培植和栖息地重修。在设计中充分考虑动物的活动特点,利用涵洞作为动物通道,利用施工废石、湿地重修爬行类动物栖息地。
从空中俯瞰滑雪赛道。新京报 王贵彬 摄
“全手工”回收8.1万立方米表土,现已全部回用
在延庆赛区的自然生态修复中,土壤也是一项关键成分。
“土壤是地球的外衣,而山区表土更是历经千年形成的宝贵资源,对付生态环境的稳定有很主要的浸染。”北控京奥培植有限公司景不雅观工程师赵瑞勇见告,土壤中蕴含丰富的种子库,不仅可以快速恢复原有植被,还能避免外来生物的入侵。
赵瑞勇说,为了快速规复延庆赛区的自然植被,他们对施工过程中剥离的表土进行了“全手工”回收。历时一年,延庆赛区共计剥离表土8.1万立方米,这些表土现已伴随生态修复事情全部回用,成为海陀山快速恢复原有生态的关键成分。
延庆赛区内修复区域总体海拔高、坡度大,最大坡度超过70度,新覆盖的土壤在雨季坡道固定较为困难。赵瑞勇先容,为此,他们提出了“随建随修”的生态修复策略,依据园地条件,因时制宜。
对付坡度较缓的地方,采取传统的修复方法;对付45度以上土石或岩质边坡,选择喷播的形式,将土壤、肥料、有机质、黏合剂和种子按适当比例稠浊后,按一定的厚度用机器喷射至须要修复的坡面,随后还要再覆上一层植物纤维毯,减少土壤流失落,担保植被成长。
亚高山草甸间,各种野花自然成长。新京报 王贵彬 摄
海拔两千米以上的亚高山草甸实现“原地回迁”
从半山腰的游客集散中央乘坐缆车一起向上,一片片灌木丛便开始涌如今面前。“这些都是亚高山灌丛植被,开着淡赤色花朵的便是红丁喷鼻香。”张志翔指着缆车下方的灌木丛说。
而靠近海拔2000米时,地面上的植物会逐渐变得稀少且矮小,灌木丛开始逐渐被更加低矮的草丛取代。
“小海陀山顶海拔有2198米,现在看到的都属于亚高山草甸的植被。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固化水土,可一旦被毁坏,规复难度极大,因此能避让的地方就一定不要毁坏。”张志翔见告,亚高山草甸是赛区内主要的一栽种被类型,内含多栽种物种群,紧张分布在山顶平台、比赛出发区和技能雪道周边等高海拔地区。他们在前期踏勘时就解释了这一情形,培植单位尊重了他们的建议。
理解到,为保护草甸生态系统,施工中受到扰动的草甸被整体移出,等到培植事情完成后再让其回归,可以说是进行了“原地回迁”。但从草甸被剥离到重新回铺,中间有6个月的间隔,这期间还须要战胜寒冬时节的七八级大风和-30℃的极度景象,如何担保草甸顺利越冬存活,成难堪题。
经由严谨的剖析论证,“草甸搬家”的方案终于确定,每块草皮的大小和厚度都有讲究。所取草皮的厚度要大于根系深度,这样可以避免切割根系,担保回铺后的存活和成长效果。随后,将这些草皮堆叠起来,其高度不高于1.5米,并用腐殖土填塞缝隙,存放在无草甸植被的阴坡平缓袒露地表,草皮浇水封冻,用加厚无纺布覆盖。同时,选取得当规格的草皮进行装袋,周围用装有腐殖土的吨袋压实,围在草皮的周围,预防冻害。
一只蜜蜂在采撷花蜜。新京报 王贵彬 摄
2019年4月,经由一个冬季的磨练,掀开无纺布后,培植者们创造被包裹起来的草甸长出了新苗,他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2019年4月中旬到5月,3500平方米暂时“搬家”的草甸得以顺利回铺。
如今再来到山顶出发区,绿色的草甸已经与原有植被融为一体,胭脂花、蒲公英在风中摇荡,蜜蜂穿梭其间。
新京报 裴剑飞 拍照 王贵彬
编辑 白爽 校正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