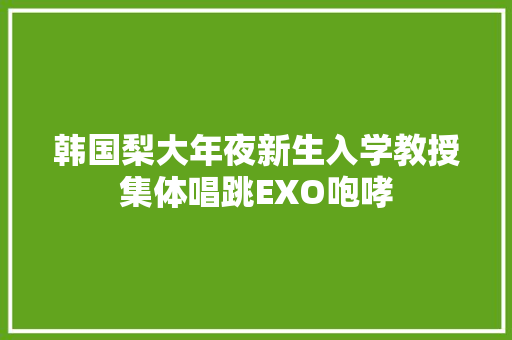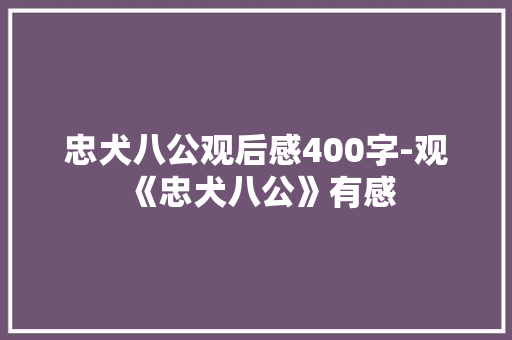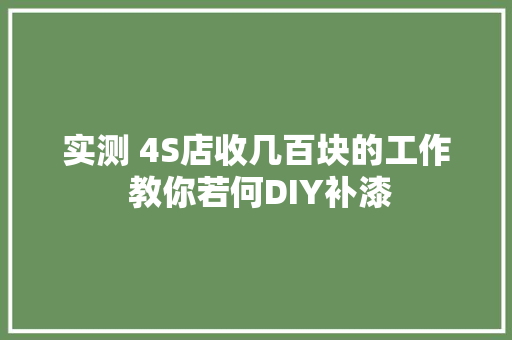在中国文明的原野上不雅观“器”探“道”
陈少明教授在讲座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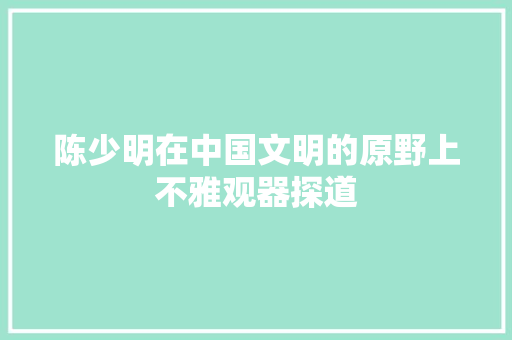
宿世界午三时,“标识性观点”系列讲座第三讲“道器”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主讲人为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哲学系陈少明教授,讲座由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哲学系主任张伟教授主持。
张伟教授首先回顾了“标识性观点”系列讲座的前两场讲座,即徐俊忠教授的“公民”和刘志伟教授的“食货”。对付将进行的“道器”讲座,张伟教授提醒不能忘却副标题——理解中国文明的视角。“道器”说是范例的具有中国标识性意义的思想观点,是中国的“形上学”传统中的基本观点范畴。在陈少明教授倡导的“做中国哲学”的理念下,对付“道器”等中国哲学核心范畴的探索,是考试测验跳脱西方理论框架,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努力,同时也为更好地阐明经典的天下和理解中国文明的叙事供应了新视角和新履历。陈少明教授长期致力于思考和探索“做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引领着我们在文明的原野上探“道”不雅观“器”。
张伟教授主持
器的天下
《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但我们的哲学传统中,更多的是“原道”,很少“说器”,陈少明教授认为“道器匹配”更是进入古典文化天下的思想正道。问道莫若先不雅观器。
陈少明教授首先以《易·系辞》和《礼记·礼运》篇为例,揭示了古典文献记载的有关从“不雅观物取象”到“不雅观象制器”的事理,借《易》卦象功能的阐释,为我们概括描述了器的发明史。从“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到“神农氏作”,再到“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即从渔牧、佃猎到农耕及早期工商时期各种器物的生产和运用。器的时期贯穿了旧石器、新石器、青铜时期和铁器时期。《礼记》中器与礼的结合更涉及了与“养生送死”“事鬼上帝”有关的人类生活的饮食、衣饰、居屋和祭拜。可以说器是人类力量(物质与精神)的见证,器这种古代社会生活的创造物关联着人类的文明。
不雅观器
陈少明教授认为器为有形之物,是人为达到特定的目的而制作或利用的物品,它的制作与利用,覆盖着物质、社会和精神(宗教与艺术)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可分为五个层次:自然物(器物的资源或“物欲”的工具)、日用物(生产与生活用品)、象征物(礼器、艺术品与文物)、功能物(从象征物中派生,如货币、笔墨)、人物(君子之“道”,超然器外,隐身器中)。这里既席卷了实用物,也包含了用以表达不雅观念与社会行为的象征物。
象征物的代价不在于材料特性,而是被授予的某种非物理的精神意义。礼器是其大宗,如象征古代权力的九鼎;此外还有一些象征物与一样平常礼器功能不同,如货币与笔墨;而更分外的器,不是物,而是人。同一类型器物的用场是变革的,以鼎为例,它经历了从生活到宗教再到权力象征的转手,成为了礼器,用以树立威信,掩护秩序。作为功能物的笔墨和货币,两者对材料的选择都有一定的哀求,笔墨附着的材料,须要得当的质地,货币则须要相对稀缺的物品。但二者的发展表明,材料只是临时的载具,意义在于其符号代价。
拟人为器,是从孔子就开始的说法。《论语·八佾》中孔子批评“管仲之器小哉!
”《公冶长》中把子贡比喻为有类于“瑚琏”一类的礼器,《为政》中又言“君子不器”。役夫言器,每每以礼的态度来看评价工具所起的浸染和所处的位置。而人的成器即成才,则是与社会、文化干系联的。在儒家的框架中,器象征着秩序,“成器”则须要修身与修心,心身即道器。
即器言道
道原指道路,是连接此处与目的地的路子,是实现想法的手段,“有道”须要符合规矩与秩序。随着“道”意的泛化,“道”也从器物(路)走到了不雅观念,从形下走到了形上,以是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以道不雅观器,器为有形之体;以器不雅观道,道为无形之物。有形与无形涉及到了可见与不可见,也就关联了“形下”与“形上”。孔颖达言:“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行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以上者谓道,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孔颖达的表述,很好地阐释了道、气与形下、形上的关系。
陈少明教授以鼎的功能的变迁为例,通过“鼎”从作为炊具的器到敬神的祭器,乃至化身为王权象征的重器之剖析,揭示道从现到隐,即从可见、可不雅观到可解的构造变革。陈少明教授又以《左传》宣公三年所记的“楚子问鼎”之事,来解释鼎与王权的盛衰关系,并将“壮盛”与“鼎革”的词源纳入到“鼎”的物变阐明中。鼎的功能从实用用具转移到礼制象征是由于“在德而不在鼎”,“铸鼎象物”是为了“使民知神、奸。”(《左传》宣公三年)鼎形与纹饰的选择和设计就涉及到了艺术与器的某种浸染或功能的共存。在象征的思维办法中,一旦分开了原初的利用背景,图案或纹饰就会成为艺术形式,事实上,青铜器在后来也的确发展成了艺术。
毛公鼎,西周晚期青铜器,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
清道光23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虽然道器相即,但道不即是器。鼎除了用以仪式性的展示外,对付其所蕴含的不能直不雅观的代价或意义,就须要通过措辞笔墨的标示来进行传达,即起“名”。如毛公鼎中,就通过鼎内部的笔墨铭刻其功绩。即器言道便是从器的利用中理解其浸染或意义及其变迁,但道也有离器独立的趋势。道器不二,是由于“道”是“器”的目的;而道器二分,是由于“道”与“器”存在无形与有形的差异,剖析、描述离器言道的趋势有助于把握“道”逐渐不雅观念化的轨迹。
《春秋》之道:救世与救器
孔子说:“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在孔子的心目中,有道无道是依据利用礼器的权力秩序是否正常来判断的,而清代阮元在《商周铜器说》中对孔子“器名不雅观”的阐明也正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阮元认为鼎的转移存在赐、赂与取三种路子,而这也正是礼崩乐坏的表现。
当象征名分的器变成了可以争夺的工具后,人们已经见“器”不见“道”。而失落道之器,实在只是废器乃至乱器。孔子作《春秋》,便是基于救道的激情亲切。实在道废不是由于器亡,而是支配政治权力的礼器秩序的混乱与损失。以守护礼义为义务的孔子,编修经典,便是试图通过历史履历的评述,规复道的本来面孔。
道家与儒家的救道计策不同,同样面对礼崩乐坏、丧德失落道的局势,老子开出的药方是“以无为本”。老子认为,秩序的混乱是在于人们对权势与财富的贪婪,沉迷太深,故器乱而道蔽。在道器错乱的局势中,当务之急不是徒劳的整顿器用的秩序,而是把道拯救出来,才是长治久安的正途。救道便是要摆脱器的纠缠,在思想长进步道的位阶,给道重新定位。老子的道,是离器、无形、非名之道。
孔、老两种不同的救道方略,都因此退为进。老子是“见周之衰,遂退”;孔子则是知“时之不用,道之弗成”,才退而修《春秋》。孔子知其不可,但积极编修经典,仍旧关怀世道民气;老子则不得已,为了过关西去,留下那五千言,是看破民气世道。一个是经世之道,一个是玄思之道,在中国文化中,分别造诣了史学与哲学。
器的复位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非常关注道器构造的实践意义,他强调“天下惟器”(《船山全书》)。这种道器论,不但是对理气论的冷落,其器本道末的想法,实际上颠覆了重道轻器的不雅观点。章学诚后来的“六经皆器”说(《文史通义·原道中》),方向与王夫之相同。这种道随器变的呼声,是那个时期的空谷足音。在近当代梁启超、陈独秀、梁漱溟都曾讲到变革要从器物、制度和文化三个层次入手。船山哲学得到的回响,正是器、道共变的时期特色的写照。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中华文明如何做到固本开新,开新且有良心?从历史的永劫段看,这是一道可能要负责作答的考题。
机器,还是物种?
在传统中,器物的支配是从自然的利用发展到不雅观念的赋义;在当代,不雅观念的力量已经可以从物质利用图变为征象的制造。在日渐到来的虚拟天下,人工智能技能的发展已经从授予器物功能,在人操纵下完成人的哀求,到独立完成并逾额完成人的哀求,乃至自动给自己设定哀求。这种智能之道,与人之道(心灵)终极是支配-被支配的关系,还是演化为并存的关系?简言之,机器是工具还是对手?这是一个等待解答的问题。
Q&A
所有的反思都是为了前瞻,对文明中根源性观点的回顾,也从来不是为了在夕阳中“沉沦”。塞万提斯说:“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韶光反抗,把遗闻往事保藏下来。它是往昔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道器”从历史的长河中经由,也从陈少明教授一个多小时的讲座中显身,等待着“后来人”的发问……
提问环节
器物从实用走向象征,是否又会由从象征走向“无意义”?器物的天下是否便是“工具”“功用”的天下?在历史的长河中,道与器的关联是否始终紧密?同学们的问题层出不穷,陈少明教授也逐一给出了回应。在他看来,“器”是我们理解天下的开始,更是我们生活的开端。作为文明的象征,任何器的制作都带着创作者或隐或显的目的,文明的积累是从具象(器)而来,添加抽象的理解与定义(道)。
吴重庆教授由此发问,在传统的敬拜中,祭品的选择是非常严明的,如君王祭社稷,牛羊豕三牲齐备为“太牢”。这些选取的畜生本身接管过人类的驯化,作为祭品,它们的身上彷佛也携带着“人的目的”。如此一来,我们是否可以将祭品也视为“器”?
对此,陈少明教授表示,在祭礼的过程中,祭品固然是不可或缺的。然而“食货”分开便已经充分解释,“食”与“货”终归是有差异的。由于食品是花费性的,而器却是可重复利用的。“祭品”中虽然包含着人的目的,但这一目的却要通过“器”来完成,因此,“器”成为了“目的”的实然承接者,以是祭品主要,却并非器。
曹家齐教授则提出了三个主要问题,首先,人既是自然的繁衍物,也是教诲的“产品”,受过教诲的人,是否可以看作是器?其次,道器和体用的关系如何?它们究竟是一套道理的不同表述,还是两个不同的道理系统。末了,曹教授将道器的问题引向了更为伟大的视域,如果说,文化便是一种生存构造,即人面对他所处自然环境形成的具有持久性的意识和行为习气。那么当我要去区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时,究竟是从器的角度出发,还是从道的层面回答?
陈少明教授回应说,如何确定区分中西文化的视角,是一个留待无数学人思考的“大问题”,以是也不妨将答案之钟,留至未来敲响。而对付前两个问题,首先从制造和被授予意义的角度来说,人不能称之为器。虽然从形式上来说,人也在接管着“教诲”的塑造,但是人始终保有着“心”的能动性。
以器喻人,既是看到了“人的发展”与“器的制作”在形式构造上的相似性,也是反响着人对付自身“有用”的期待。然而这究竟只能是一种比喻,且必须是有限度的比喻,我们不能把人当作工具、机器去授予它意义,乃至无限度地定义塑造他,如此,则人不为人。至于道器和体用的关系,体用指向的是实体与功能,它和“道器”这一观点确实存在一部分意义重叠,但彷佛并不能完备等同。
随后,诸位教授又就本次讲座进行了“无程式”的自由互换,肆意抛撒着思想的火种。吴重庆教授别出心裁地从“器”字的字形上展开了思考,他说器有四口,个中为犬。犬这一动物象征了什么?它是否具有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文明属性?
对此,陈伟武教授表示,人驯化犬的历史是极为悠久的,故而以犬作为字义构建的媒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毫无疑问,人和动物的关系是繁芜的,无数的谜团还萦绕在“人禽”之间……
曹家齐教授(上)和陈伟武教授(下)提问
显然,对“道器”观点的反思,牵引出了中华文明中诸多根源性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期,又为不同的你我深情思虑,而你我也终将在思虑中看到“未来走到我们中间,只为能在它发生之前良久,就先行改变我们”……
讲座合照
(笔墨整理:谢佩霖、何擎宇;拍照:施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