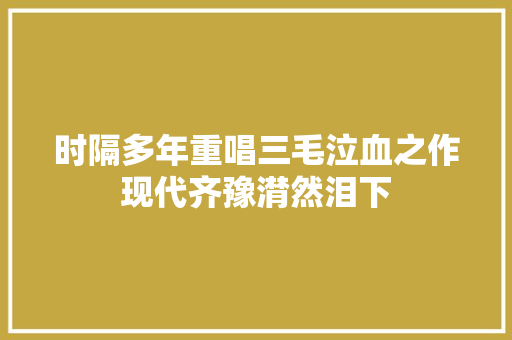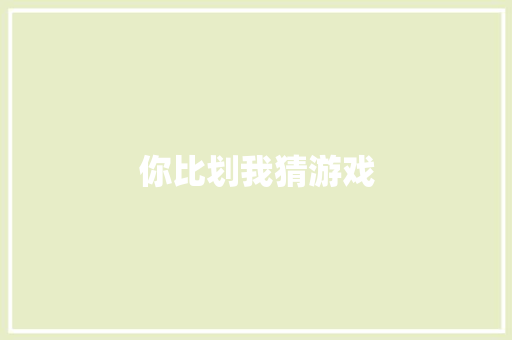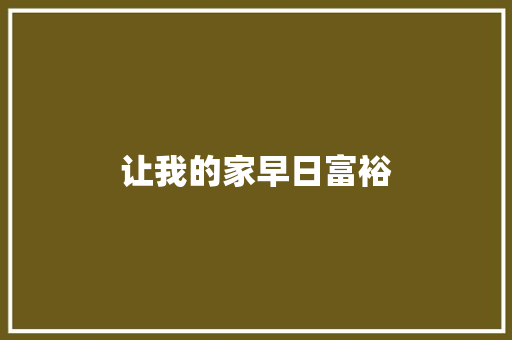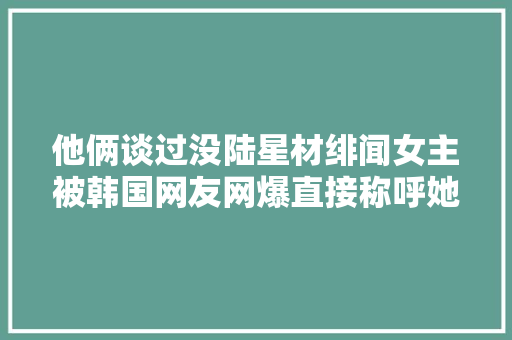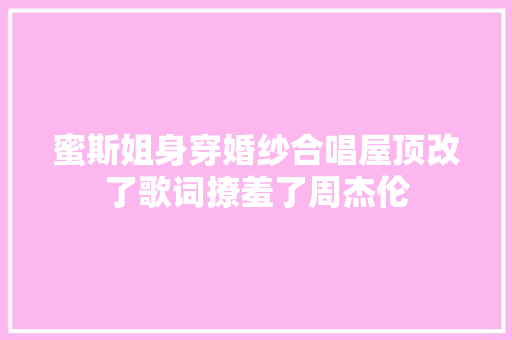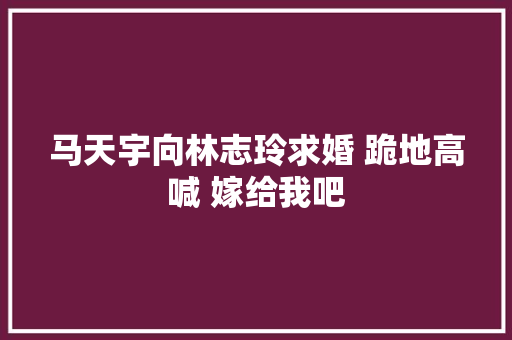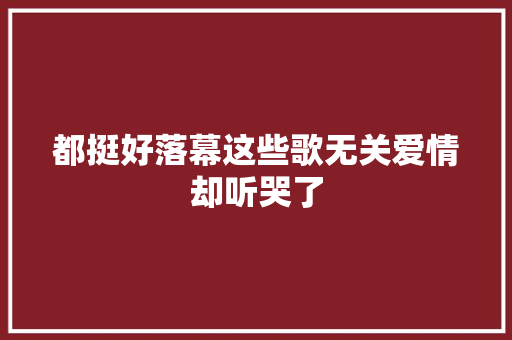《乘风破浪的姐姐》风起云涌地开播着,一韶光,仿佛所有的聚光灯都在“姐姐”们身上: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努力、各有各的个性……这统统终极都会在舞台上达到沸点。
舞台,一个多么具有魅惑力的词,万人运动场,所有灯光打在脸上,所有目光等待着,定是要有非凡的自傲,才足以撑起这统统。这时的歌声彷佛都属于舞台,歌手们争相上综艺,只为能让自己的音乐多一点曝光。这时的“姐姐”亦仿佛被提前预设好,等待不雅观众的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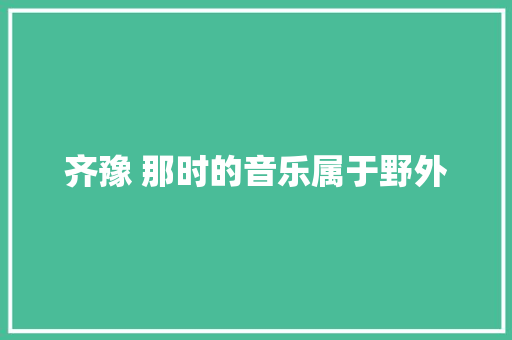
属于舞台的音乐层层累叠,耳畔不禁飘来悠扬的旋律,它们来自野外,呼唤远方。亦不禁想起一个诚挚唱歌的姐姐——齐豫。
姐姐齐豫,她的歌声彷佛三十年都没变过一样,不急不缓,淡淡飘在空中。像远方的云朵,像空想,可追、可不雅观、可叹;又或是一只手,轻轻拍着你的肩膀,不说多余的安慰。而她的样子,衣着层层叠叠、披披挂挂,头发蓬松,爱笑,还是姐姐给我们最初的样子容貌。
很多人都说齐豫唱歌是在云端,她是仙女,是天使。但生活中的她却一贯在“低处”,对空想与生活依然保持着谦卑,对他人始终给予最大的同理心,对自己始终在自省复苏。就像她说的一样,“空想不是用来追逐的,而是要来成为的。要成为一颗丰满的、茂密的、给予人风凉和氧气的橄榄树。”
郁热的夏,就随着这棵橄榄树回到那时的音乐,那时的野外,那时的远方吧。
1979年,一曲《橄榄树》横空出世,飘遍了大江南北,还在台大读人类学的齐豫迅速为人们熟知。而这首曲子等待它的演唱者,等了整整六年。
《橄榄树》的创作者是李泰祥,台湾音乐界难得的天才,音乐圈难得的伯乐。创作《橄榄树》时,李泰祥还不满三十岁,当时的台湾音乐大多都不是原创,翻唱国外的歌曲。带着要曲稿身的歌的义务感,加上自己古典音乐的专业出身,李泰祥做了很多的考试测验,横跨古典乐、当代乐、实验电子、盛行歌曲、电影配乐、戏院配乐,将当代诗唱着歌里、跨界与文学家互助,他认为我们民族的音乐该是有人文性的。他想到了三毛,写了《橄榄树》、《一条日光的大道》……
音乐人李泰祥
那个年代,台湾还没有对外开放,不可以出境旅行。当时三毛的书受欢迎的很大缘故原由也便是:她去往了天下上不同的地方,她像是大家的眼睛,看到了万千天下。
三毛原来写的《橄榄树》是她对西班牙的情绪,以是原版词里,都是西班牙的痕迹,比如“为了小毛驴/为了西班牙的姑娘/为了西班牙的大眼睛。”李泰祥拿到歌词,不太满意,勉强谱了曲却没有揭橥。过了几年,民谣杨祖珺把中间一段歌词改写为“为了天空飞行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三毛对这样的改作也不满意,曾经公开说:“如果流浪只是为了看天空飞行的小鸟和大草原,那就不必去流浪也罢。”
对付三毛的“不满意”,李泰祥反而以为那是一种轻松,他以为自己常常被传统所束缚,生活上有许多框架,处处以为碍手碍脚,多么希望自己能自由清闲地写与创作,以是《橄榄树》可以代表个人生命完全自由与追求完美空想,可以打开胸襟,不再拘泥于某些传统上。
而彼时的齐豫,二十岁刚出头,是个还在上大学的姑娘。她参加了歌唱比赛,幸运的被李泰祥听到。李泰祥以为这歌声惊为天人,以为齐豫像活在这天下上的星星,并且她的光亮能一贯存在。于是,在李泰祥的带领下,初生牛犊的齐豫唱下了这首难度极高的《橄榄树》。没想到的是,这首歌火了,歌里唱的远方,是没有出门的人神往的空想,是出门的人念想的家乡,大家都渴望流浪远方,流浪……
齐豫被李泰祥的《橄榄树》领进了音乐的大门,但她并没有焦急进入演艺圈。
最初唱歌,齐豫完备是无意识的,她的父亲不许她唱,由于她是台大高材生,“戏子”的不雅观念在父亲的脑海里无法拔除。齐豫也没有太反抗,乖乖去美国读书。而在美国读书的日子让她清楚的创造,“我是一个唱歌的人,我想唱歌。毕业论文,我的题目是《校园民歌》。那个时候,我自己下了决心:要回台湾去唱歌。”就这么一唱,就唱到老了。
前年在《歌手》的节目中,齐豫又唱起李泰祥写的《一条日光的大道》,齐豫还是那个心怀美好,念着“雨季不再来”的女孩;唱起《不要告别》和《告别》,亦是永久感念她的老师李泰祥,由于老师让她在年轻时就知道——音乐也可以成为艺术,飘向很远的地方。
李泰祥对齐豫的意义,不仅仅是帮她写下《欢颜》、《走在雨中》、《答案》等等无数经典的老师,而是带着她找到空想的灯塔。
齐豫这个姐姐,从来叫三毛都是“三毛姐姐”。她与三毛的缘分,可不止于《橄榄树》。从她在学生时期看三毛写的书开始,到她们互助音乐专辑《反应》,再到现在提起齐豫的名字就想到三毛,她们的缘分一贯都在。
三毛曾说:“在台湾,只有3个女人适宜穿波西米亚风格的大花裙,这三个女人便是三毛、潘越云和齐豫。”也在那个时候,齐豫在三毛的影响下,穿着了波西米亚风格的大花裙,那是自由的、不失落自我的。
现在已经年过花甲的齐豫,还是坚持波西米亚这样随性的风格。她的演出服装几十年来都是她亲手预备,她常常拎着菜篮子去同一家店铺买布,老板对她很熟习,她们拉拉家常。买到布,自己想颜色怎么搭配,又该配什么样的胸针。
三毛、齐豫、潘越云
当年,齐豫与潘越云两人敲开了三毛姐姐家的门,要和她互助一张专辑《反应》。当时的三毛才失落去爱人荷西不久,而这样的爱情让齐豫和潘越云两个妹妹有了更多的想象。她们想象的的三毛是比较撒哈拉风情的,像北方人,会骑着骆驼去流浪,大大咧咧的。结果看到的三毛,创造是小桥流水的觉得,讲话细声细气、很柔柔、感性。
齐豫和潘越云两人常常去三毛的家里,创造三毛的家里全是书,连厨房都是书,乃至每天要坚持看八个小时的书。而两个小妹妹的到来,打乱了三毛的生活。她们一起做的专辑《反应》实在更像是三毛的自传,里面布满了她的亲情、爱情、思考、困惑。三毛每写完一首词,就给两个小妹妹听着讲故事,讲得缓慢、有节奏,讲到落泪、不能言语。而两个小妹妹并不能体会到她的痛楚,只想齐心专心挖掘三毛姐姐的故事,只想齐心专心帮助三毛姐姐走出阴霾。
三毛、齐豫、潘越云
专辑里《现代》、《孀》等无不是三毛姐姐的血泪,这实在对三毛来说是痛楚不堪的,她也坦言到,“反应是一种恫吓,它一直息地深入民气,要的不过是一个证明。”
后来齐豫回顾这张专辑时,陷入深深的自责,她感慨着,“(三毛)她一定要经由很多的消化、重新揭开痛楚之后,才能写出那些词,大概她不想再连续了,但是我们在那样的状况之下还在哀求,我以为我们是有一点不谅解的。”
二十多年后,在飞往秘鲁的航班上,当齐豫飞过三毛也曾飞过的天空,仿佛溘然受到某种感召,一气呵成地写下《未曾告别》的歌词:
当年的哀求是对比样错
反应的恫吓是否还在闪烁
无知无明的 走进了你的生活
乱了一方好不容易平息的滂沱
三十年后,当齐豫与潘越云重新唱起了《反应》,满是感念。想必三毛姐姐未曾责怪过她们,由于在她心里,她们是她的好朋友:一个是天使齐豫,一个是埃及艳后潘越云。
而两个小妹妹以为那首预示三毛姐姐走出阴霾的《梦田》,早就成为每个人心中的梦田,种桃种李种东风。
把齐豫叫姐姐,莫过于她是乐坛“小哥”齐秦的亲姐姐。由于父亲齐济感念生他的济水,济水流过的地皮都成了儿女的名字。两姐弟,姐姐是乐坛的仙女,弟弟是乐坛的“浪子”,就像弟弟给姐姐写的歌《飞鸟与鱼》一样,一个在云端,一个在海里。
姐姐齐豫从小便是一个自卑的人,她有些内向,也不睬解撒娇。弟弟齐秦反而会和父母撒娇,终年夜了还会给姐姐撒娇。家里常常空空荡荡没有人声,只能见到茶几上压着20块台币。姐姐就带着弟弟去巷口买两碗两块钱的阳春面。弟弟后来接管采访说,“从那之后,我就常常在等齐豫。无论我多么尴尬,多么绝望,只要我等齐豫,她一定会涌现,让我有无比的安全感。”
儿时的齐豫与齐秦
有一段韶光,父母去国外了,大哥齐鲁去昔日本求学,姐姐齐豫彻底成为弟弟唯一留在身边的亲人。弟弟不听话,已经开始混帮派,吸烟饮酒逃学斗殴,进了感化院。姐姐就周六从台北坐车到台中,再到彰化,再到田中,末了上山到弟弟所在的感化院。除了考试,3年没有间断。
这时的姐姐由于唱歌得到了自傲,她想弟弟也能重新自傲起来。姐姐去参加了歌唱比赛,得到了8000块的奖金,对付一个学生来说,这是一笔“巨款”,她拿着这笔“巨款”给弟弟买了把吉他,一把很好的吉他。
弟弟没有辜负姐姐的期许,一唱,就唱出了一片天空。弟弟后来在无数次的采访和自传里也感念姐姐的照顾,他以为身上有根细细的线,多年来一贯被姐姐攥在手里,才没有“断绝”在那个禁闭压抑的高墙之内。
当然,弟弟也送了姐姐音乐上的礼物。
姐姐的歌曲常常被大家说“曲高和寡”,苦恼有时,幸福有时。弟弟就自告奋勇给姐姐制作音乐,《玄月的高跟鞋》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而在微凉的玄月。《飞鸟与鱼》中没有时令、颜色、眼泪,只有嗟叹、干净的“Always together forever apart”。弟弟还是依赖姐姐,大大小小的节目,常常找姐姐来“救火”。
姐姐与弟弟在音乐上一起飞行着,真好。
姐姐齐豫今年63岁了,人们都说她的歌里有暮色感,低低地飘落人间。但她还是当年姐姐的样子容貌,平凡、沉着着。
2年前,姐姐参加了《歌手》,第一场唱好朋友潘越云的歌《最爱》,她面带从容,咬字缓缓的。不同几年前杨宗纬的唱的苦情凄凉,齐豫细说的是一段往事,这段往事她释怀了,这段往事让她发展为自己,以是“以前忘却见告你,最爱的是你。现在想起来,最爱的是你。”姐姐爱这样的自己。
姐姐的婚姻实在比较坎坷,她的两段婚姻都没有得到善果。但姐姐很少在"大众年夜众面条件起这些事情,即便提起来也都是戴德的,都是淡淡的笑颜。她现在的生活很是沉着,沉着便是最大的幸福。
一大早起来,洒扫庭除,自己擦地,擦桌子。买菜,做饭,不外食。她爱这些小事,这都是一个人的本分。做好自己的本分,便是在修行。本分事,做得适可而止,便是圆满。
对付唱歌这件事,姐姐齐豫始终感激,始终自傲。她说,“我逐渐从一把乐器,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多难,多不好听的歌,我都不挑剔,不抱怨。由于我有了灵魂,歌被我唱出来,会完备不一样。”
的确如此,她唱佛经,摒弃感情的起伏,险些让人觉得不到呼吸,用长音去唱,唱得饱满,安宁,均匀;她唱《女人花》,不是美人迟暮的是自怜与空无,而是如梅、如莲的空静与平和;她唱《城里的月光》,不是许美静似的清冷中有温暖,而是如真实的月光一样,洒在每个人的心房;她唱《Vincent》,是最温顺仰望梵高星空的人……
她的人生,正好好。有音乐,正好好。
记得,有一位听众听完齐豫现场演唱后,写道:「听齐豫唱歌像淋了一场上一个秋日的雨,寒冷,沧桑,我打开窗,张望出去,是回不了头的日子和人们啊。」
回不了头的日子,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猜想是有李泰祥看到“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时的哲思;是三毛从沙漠里走来,又向沙漠中走去;是齐秦等着姐姐买那碗阳春面;是齐豫那棵属于野外的橄榄树。
“我一开始便是一棵树,让途经的人靠一靠,我用歌声见告你,你看,那便是永恒的光明。”姐姐齐豫曾这样说到。她也做到了,她的音乐诚挚而发,几十年过去了,依然可以安慰着我们的光阴。
反不雅观现在的盛行乐坛,鲜少有音乐人要去做一颗树了。大多音乐都在迎合流量的时期,热热闹闹,但末了什么也没留下。音乐早经不起岁月的考验了,更何谈音乐带来的远方与空想。
这亦是姐姐在这个时期的宝贵,由于她早便是那棵橄榄树了,既是家乡,又是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