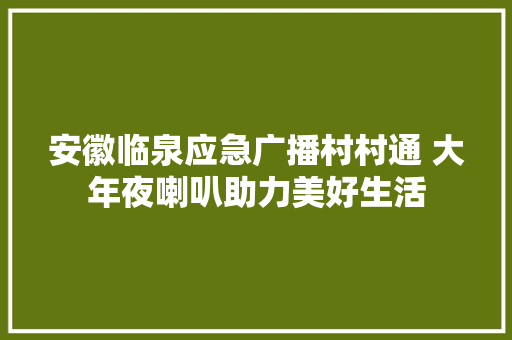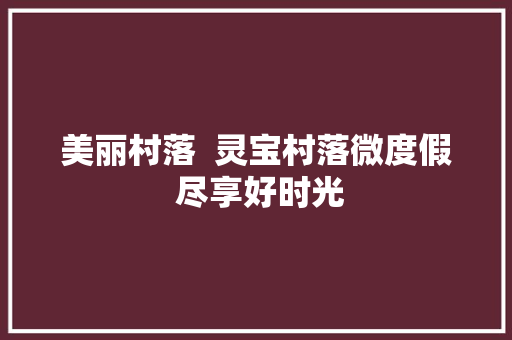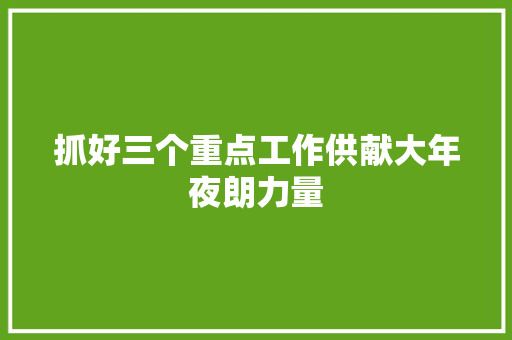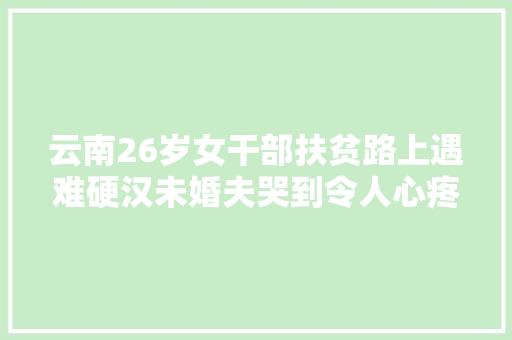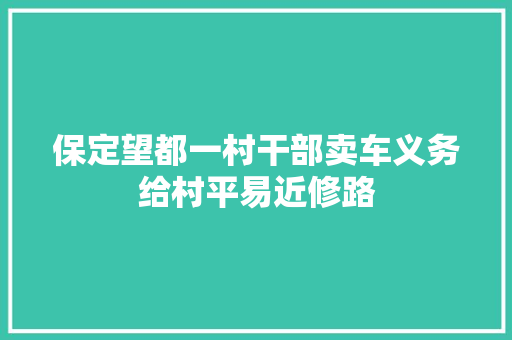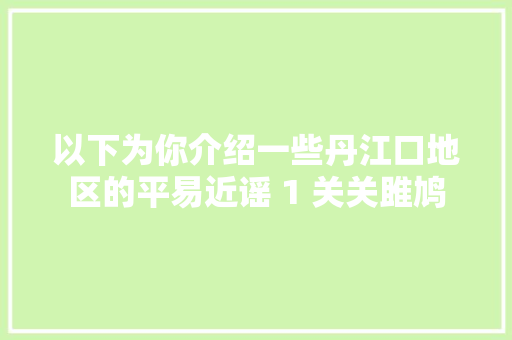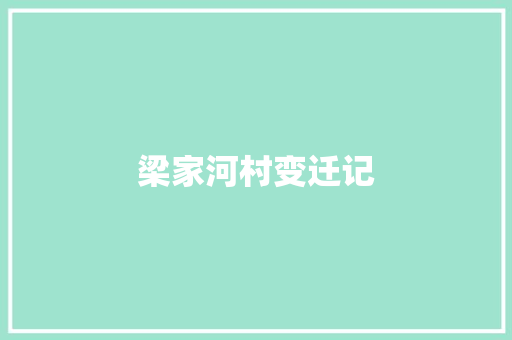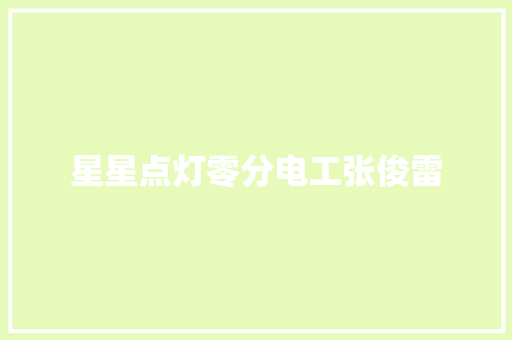文:乔玉璞
洋车子便是自行车,俺老家那一带就不说自行车,偏说洋车子。洋车子是用来骑的,不是用来扛的。良久以前我还真得的扛过洋车子,俺们村落也多人扛过洋车子。个中缘故给你逐步道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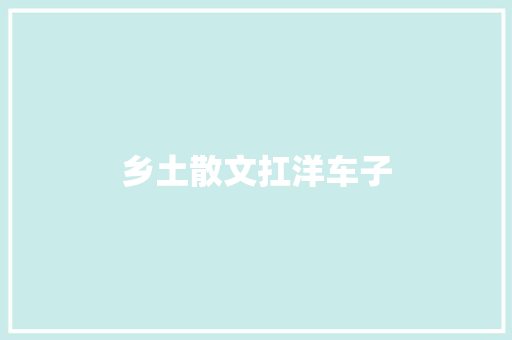
在上个世纪90年以前,我们赵店村落既不通油漆路(柏油路),也不通水泥路,如果出行阳谷、聊城、济南等地儿,非得去阿城镇不可,由于我村落由阿城镇走上油漆路最近!
我村落在阿城镇的西南方向,有8里路,与阿城镇是地邻,即耕地相接,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河沟为界,这条沟将这8里路平分为两段。靠我村落这段4里是淤土路,靠阿城镇那端4里是沙土路。晴天,沙土路路面平整,也好走,淤土路这端虽疙瘩凹凸、磕磕绊绊,也勉强能走。雨天或雨雪刚过,这两个4里种则路况迥异,沙地皮的一段仍平整硬实,可以通畅,淤地皮的一段则泥泞不堪,要多难走有多难走。我村落的路是出了名的难走,沙地皮儿的姑娘都不愿嫁我村落,便是这路给闹的。
沙土路,不粘(nián)且渗水快;淤土路,很粘,渗水慢。二者土质不同。
我村落这真个4里路,若是雨天或雨雪刚过,有好多“洋景”可看。
——步辇儿的人鞋底一定会被粘(zhān)住,与鞋邦“分家”。若心疼鞋子,可连同袜子一起脱下,赤脚挽腿前行;若踩到路面“发亮”的硬地儿,脚底板下如流油般打滑,摇扭捏晃,打几个趔趄,乃至“哧溜”一下子滑出几步,摔个跟头儿。
——汽车,特殊是小轿车开到这地儿,只见轮子“哧哧”空转,光打滑不走路。司机急得头上冒热气,那种开车得意的神气自会荡然无存。
——自行车到了这儿,起初还能推着走,推不几步,前后轮盖瓦里塞满了泥,越推泥塞得越紧,直至前后轮一转不转,只能推着“哧哧”地滑行,还会“犁”出一道深深的沟痕。再急也得生法走,于是在树上披下一段树枝儿,将泥儿戳了又戳,推不了几步,泥又塞满了,还是推不转圈儿,推车人连急带累衣服溻(tā)透,气喘吁吁,筋疲力尽,只好望车兴叹。这个时候,真是体力大比拼。粗壮有力的青壮年干脆扛起来,让车子骑人,但扛不多远,也得放下歇歇。那个时候多是有大梁的28大轮金鹿牌洋车子,有四五十斤沉,飞鸽、永久、凤凰牌的小轮车子稍轻点儿,也得40多斤,连磨带压,肩膀上会现出通红通红的血痕。这个时候有人会嘟嘟囔囔、骂骂咧咧“这是啥熊路唉”“这是他娘的啥路唉”,实属“绝望”、无耐。我曾见过不知是小媳妇,还是大姑娘,挺俊秀的,穿着也时尚,洁白的袜子,红红的凉鞋,崭新的洋车子,老天爷也不会由于这眷顾于她,她的车子还是推不动,而且她的凉鞋粘在泥里,脚丫踩在泥里,袜子上满是泥巴,只有哭的份儿。又能乞助于谁呢,路人们都困于烂泥之中,各顾各都顾不了。只有一个办法,待雨过天晴,路面稍干,再前行吧。
在这个4里路程上,我也领教过扛洋车子的滋味,也像以上扛洋车子的一样狼狈,一样尴尬,一样“丢人现眼”,但每次我都能“去世扛”“硬扛”,“全程”通过。这使我终生难忘。
我村落上的人祖祖辈辈都来回在这段路上,早已接管了它的“泥泞”,都能坦然面对。雨天或雨雪刚刚过后,没有急事不出行,窝在家里,待路面干(gān)好再出行;有事非要出行的,则要借助工具,活人总不能叫尿憋去世。
履带拖沓机可以出行,可谁家有这般“家什”?没这,就利用现有的工具。套上牛,让牛拉着地排车,可坐几个人也可装至少两辆洋车子;也可套上牛,让牛拉着拖犁子的拖车,在上面放上几条长条木板,将洋车子放在上面,人也坐上面,即可通畅了。牛蹄子抓地,不用担心滑倒。最笨的法,也是较费力的法,则是将洋车子绑在长长的扁担上,穿上长雨靴,两人抬着,小心翼翼、“四指儿四指儿”挪动。80年代,村落上很多家有了小型四轮拖沓机,可用于农业生产,可当交通工具,小车斗里能拉好多人,也可带上几辆洋车子,拖沓机头上也能坐两个人,拖沓机在这泥路上也左摇右摆、颤颤微微,走得也不大胆,磨练的是驾驶技能,这倒让没拖沓机的人家好生倾慕。无论用啥工具出行,目的只有一个,能胜利通过这难走的4里地,将人、洋车子弄到阿城地盘,踏上沙土路向外出行就ok了。
这难走的4里路,雨天或雨雪刚刚过后出行很难,晴天路干了也好不到哪儿去。一道道由洋车子、地排车轮子压出的沟痕,远看就像火车站上的条条道轨;一个个由牲口和人踩出的深深的蹄印、脚印里,竟然成了赖蛤蟆和田鸡的窝巢。为使这段儿路好走点儿,待雨过天晴路干,村落里时常安排人使牛拉着耙(bà),将车辙梗子、牲口的蹄窝、人的脚印耙碎,再用耢(lào)耢平,路就好走多了。但自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小四轮拖沓机成了致富工具,这段路从此便“万劫不复”了。好多人开着那宝贝儿似的小四轮,贩卖豆子、石头、沙子,特殊地“恨载(zà)(尽可能多拉)”,能拉上万斤,阴天下雨根本挡不住他们出行,挣钱心切,将我村落这4里路,“犁”出了道道弯弯曲曲、长蛇般蜿蜒绵长、足有尺余深的沟壑。至此,就无法用牛拉耙、拉耢所能平整,但这却给皮孩子们供应了好玩地儿,他们上学放学偏要在这深沟里比赛骑技,骑不几米就撂个子,腿上磕得青一块,紫一块,却笑得前仰后合。村落民们见此,却是哭笑不得,拖沓机如此“不法”,也无人干涉干与,总不能不让人家挣钱致富吧。也只能从心底里发出“这样的路何时变坦途”的叫嚣!
愿望着,愿望着,这一天会一步一步到来,也只会逐步到来。
上世纪90年代初,镇上修了一条由阿城至颜营村落的防汛油漆路,我村落在颜营村落的西北,恰好有一条2里长的土路与这条公路垂直相接,这意味着我村落踏上油漆路前所经由的淤泥路由4里缩减到2里。村落民们已感知足,难走的路少走一点儿是一点儿。
上世纪90年代末,阿城—张秋(阿张)的油漆路修通,且在我村落北通过,距我村落不敷100米。意即我村落外出还剩不敷100米的淤泥路,这自会增强我村落整修这不敷100米和村落内大街小巷同属淤泥路的信心,曾经“不法”的小四轮拖沓机从外地运来柏油路重修而废弃的沥青块,整整铺了一层,顺利实现了我村落与阿张公路的“链接”。虽仍坑坑洼洼,但人车勉强通畅,下再大的雨雪统统地不怕了。
光阴穿越,时期发展,统统会逐步变好。2016年,乘着“全省履行村落村落通,打通末了一公里工程”的东风,通向阿张公路的这不敷100米的路和全村落的大街小巷统统铺上了一拃(zhǎ)多厚的水泥路,我村落实现了建村落以来(村落上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建村落)由淤泥路,隔着油漆路直接到水泥路升级换代式的顶级超过。与我村落境遇相同的还有与我村落地邻的史塘、袁庄、上闸、下闸、颜营、刘什庄等村落。这些村落村落内也都铺上油漆路或水泥路,且与阿张公路相连。至此,让人发愁的淤泥路没了,用废旧沥青块铺就的路没了,“洋车子骑人”的年代没了,那些沙地上的姑娘也乐意嫁到我村落来了。村落上路修睦了,大小汽车也多了,可远行游四方,可买卖达三江。村落民们个个神气十足、扬眉吐气,小日子红红火火。这统统都得益于党和政府的惠农政策!
作者简介:乔玉璞,山东省阳谷县作家协会会员,公开拓表教诲专业论文30余篇,主编校本培训教材4部,与他人互助出版论著5部,现喜好散文写作。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若侵权联系删除。欢迎文友原创作品投稿,投稿邮箱609618366@qq.com,本号收录乡土、乡情、乡愁类稿件。随稿请附作者名,带图片最好,请标注是否原创。乡愁文学公众年夜众号已开通,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xiangchouwenxue,关注我们。